盐与刀:阿合马之死和“汉法”的两张面孔
你说一个外来人,如何才能坐稳中原的江山?是把大胡子拉成小辫,还是一窝蜂全学汉人读经念诗?隔三岔五总有人琢磨这个问题,但真要摆上桌子,没那么简单。生活里事事都有明面的一套——讲义气、讲道德,老话说得好听——可真有哪样铁板一块、天经地义的“汉法”吗?咱们寻思寻思,八成没那么美好。
有人说,跟着儒家念“仁义道德”,天下太平。头一回听,谁不心动?可日子过久点,你会发现,这玩意儿就像老酒楼后院挂的匾,能登门面,但吃饱饭可不靠它。那帮从草原上滚进来的人物,打了一辈子仗,命都是蹦着玩儿的,全靠刀头舔血的本事混成大头目。他们更懂,没有规矩能让世人只凭良心做事;道德是好东西,可是真给你一把权,谁能真一辈子忘了自家利益?
这些年头,人嘴里讲着“义”,实际算盘全在算“利”。也难怪,站得越高,吃得越多,总得给自己找个“大义”包装包装,这样抢起来心里踏实点。可是拆开看,大义都是拿来说的,润藏里面的“利”才是动力。利益线,才是拖着历史车轮往前跑的绳子。
你瞧中国的老路数,早早就玩起了“大一统”,中央收税收粮、集权收心,全靠一套必须精打细算的财政本事。那些书上少提的“法家”,把账本和奖励、惩罚摆明面——谁种多少,罚多少,吃喝全明码标价,别扯虚的。这样才能维持一国庞大的财政机器。当然,这种管法不一定人人喜欢,可要真收拾得起一个巨大地盘,老实说,还就是管用。
要问“汉法”灵魂在哪?其实是“儒表法里”。拿个钵装着佛水,心里揣着算盘。“儒家道德”是表面功夫,底子里却少不得法家干活。两条线藏在一起,外人拍胸脯说明白的,其实都还差些火候。
这两条线里的“义利之争”,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回,咱们老百姓可能都听过些道道——汉昭帝年间的“盐铁会议”。台上文人唇枪舌剑,说得“纯义不谈利”,可人物账算到最后,主事的桑弘羊还是把盐铁专卖给留了下来。嘴巴会响不如腰包吃紧,这戏码后来一代代重演。
转眼到元朝,蒙古人打下这片地盘头些年,进了城也还是带着草原子弟的心气。最早那会儿,打进金国,城破就屠,财宝、女人,抢完了就扔下跑,谁稀罕留屁股头管田种地。但好景不长——手头金子挥霍得快。蒙古贵族眼红,可拿华北平原真当牧场?亏得有个耶律楚材,还不是给窝阔台大谈仁义,而是把账单摊桌子:你要想年年有钱,不怕粮断饷缺,就得用汉人的那一套收税法。
于是,从“烧抢”变成了坐地收钱,等大车的粮食和银子一摞,谁还怀疑“汉法”不好使?这就是把坐寇的本事学到家,比流寇高明多了。站住了脚,甜头上来了,才算是两个世界的交汇——蒙古汗王和刚刚被动员到朝廷的儒士们,一段假象蜜月期。
可你说,这个蜜月期能长久?那哪儿的事。皇帝宫廷里的账,哪有那么好糊弄。大蒙古国“开矿收税”全靠汉人文士献策,撅起袖子来一通折腾,前几年怪得几车黄金银子,等地方豪强学乖了,土地人口假账越做越大,那点钱眼看又不顶用了。
其实每到这个节骨眼,全天下的“当道者”都碰一鼻子灰。钱不够花,看谁能再出主意。历史的筛子总会把能找钱的人拎出来。等到忽必烈坐上大位,这筛子筛下来,可不是个一般人物,叫阿合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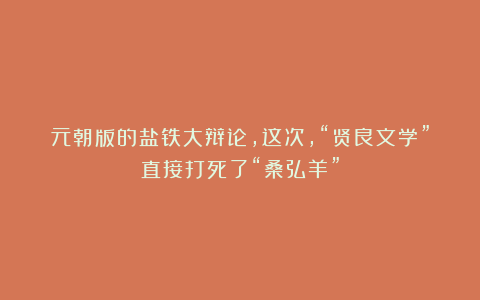
谁是阿合马?有什么来头?这位跟着察必皇后进宫,本是她爹的奴隶,大老远从中亚游来的“回回人”。嘴皮子溜,脑子清楚,对盐铁粮税那是门儿清。忽必烈瞅中了他,让他管中书省财政,说白了——把帝国的烂账全摊给他。
咱说句老实话,阿合马是真有一套。他一上来,先拿盐动刀子。老路玩得溜,国家专卖,除了官方盐,其它全是私盐。这年头地方政权枝蔓满地,农民私下买私盐。走私打压吧,代价大,政府精力有限,阿合马玩了个新花样:不管你吃不吃官盐,一律摊派税,反正你跑不了,最后基本都摊到有钱人和免税的和尚道士头上。
盐之外,他瞄上了铁。大开河南铁矿,产出的铁做成农具,一面卖农具一面收回粮食。不只铁,还琢磨着桓州开银矿,连锡都是顺带进账。
但最让地主和土豪们炸锅的来了:阿合马彻查土地人口,多少年没人敢摸的烂账,被他挨个捋出来。往年那帮地主、和尚、道士啥的,靠特权躲税的好日子到头了。现在都得老实交钱,免税特权一刀切。
你以为官员能逃得掉吗?元初官员没定数给俸禄,靠捞空子过日子,被他改成了“国家发工资”,想打秋风的路断了,官场上鱼龙混杂,也算治了治乱。
这一套拳脚下来,财政收入哗哗地涨,可敢得罪的人可是一大帮。咱老话说得好,动人钱袋跟杀人父母一样。地方豪强本来垄断了土地、人口和暴利行业,阿合马现在是刀刀切他们肉。你想,谁肯干?
这些地方豪强,一多半其实就是老文士、老地主,过去打着为国家操持、为百姓谋福的旗号,底下可都是产业大户。有了制衡之心,这回可真闹翻了——弹劾的、污蔑的、上书的,没完没了。骂阿合马无德、贪赃枉法,说他逼贫害富。想想当年桑弘羊,算计天下人的钱粮,也是这些贤良文学出头骂,把嘴皮子磨烂。
忽必烈怎么对付?耍滑头,一边虚心受批,一边继续重用阿合马。天底下,真金白银才是王道,至于弹劾他啥品行,那跟账上进了多少银子比,根本不算什么。
可话说回来,杠到最后,“理想派”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有力的代言人——太子真金。此人自小就是按照儒家养大的,信义为本,看不惯阿合马这等“坏人得势”。可惜说破了天,也只是说说,忽必烈还是看重能帮自己填财政窟窿的人。
真正的转折,像戏台子上一声锣响,突如其来。至元十九年春天,宫里突然惊动八方——一个叫王著的千户,配合着高和尚,率八十多人扮成太子的仪仗杀进京城中书省,把阿合马一铜锤砸死。整个计划之诡谲、过程之荒诞,听得人脑门直冒汗。
怎么做到的?这王著本地头蛇,利用骑兵、僧侣特权,动静搞得跟真的太子进京似的。没几个人敢拦。铜锤加大势,门前一叫,阿合马被撞蒙了——死得真不体面。后来王著当场被瓮中捉鳖,死得也惨,说到底,他俩不过是地方豪强和被砍特权的和尚的缩影。
这场闹剧,皇帝大发雷霆,该杀的杀,该剁的剁。但你要说“只关正义”,那可就天真了:王著其实不过是“既得利益”(说白了就是被阿合马砍过肉的人)反扑的一颗棋子。现实里,地方和中央,就是这水火不容的关系。
更讽刺的是,忽必烈自此对儒士光环生了嫌隙;往日一腔热情的汉化大潮也就此偃旗息鼓。而真金太子,理想越高,轮廓越悲——郁闷而终。
再绕回那个最早的问题:什么才是“汉法”?每一代外来皇帝都在磕磕绊绊地试错。手里揣着真金白银才有资格讲“仁义道德”,讲多了变成笑话,最终人心隔肚皮,皇权也好,地方也好,没几个人真想着乌托邦。
而阿合马,活着是权臣,死去成了反面样本,手腕铁血、心肠自私,却又不得不说:他的那点办法,的确让国库鼓了鼓。可惜,无论是铁血、为公、为私,或许都只是权力游戏里的短暂一程。利益荡漾,旧友新敌来来往往,等到下一场财富大潮,谁又能分清“义”与“利”的边界?
有些人,看起来风光无限,死得却像一场临时上演的话剧;有些账,算一辈子也算不明白。历史走到这里,真真假假,似乎总要蒙上一层灰。你说,这“汉法”,究竟是活人的规矩,还是亡者的墓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