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那些水里浮沉的人间事
谁能想到,一大片水,能把人的命运搅合得这么糟心?几十年前的昆明人,每年都得提心吊胆——水太多,怕老天爷发疯,水灾一来柴米油盐都成了难题;水太少呢,又怕断了生活的脉气,连下雨也盼着不带风。哪里像现在,偶尔逛湖,只觉风景宜人,可你要是真听进滇池的“人话”,那才是滋味。
这水,讲起来是家乡的青山绿水,转身又成了工业废水的生死场。说起来,谁家不是靠着它喝水种田的?可有人一句话:“生产为主!”结果呢,往里倒的污水一年赛一年,生活污水、工厂废弃物,恨不得湖里全是人类的“长尾”。滇池沉,鱼儿沉,昆明城也跟着揪心。到了九十年代,湖里能见度连半米都不到——老昆明人有把湖水捧起来做茶的记忆,后来只能摇头叹气。
但这事,拐弯抹角地也不是一朝一夕。滇池啊,真不是今天才遭这罪。翻起本地的家谱和故事,那些上世纪老照片都还算新鲜玩意,明清时候的灾祸才扎心呢。一场洪水席卷过来,村民睡前都得瞧瞧水面,生怕天亮被江水卷走。洪武年间的滇池水患,十里八乡喊天呼地;吴三桂那会儿,也不怎么管水情,反正自个享乐第一,百姓下泪没人看。
到了民国,水灾还是年年见面。每逢暴雨,昆明就像被勒紧了腰带——街头巷尾全是泥水。不是没人动手解难,五十年代,种田人和城里人都上山下河,在滇池上游修水库、建泵站。几十个工程,谁家男人都搭了把手,往回说起来,反而像是儿时的考验。大家期望洪水能被这些大坝拦住,日子有盼头,可天意总不由人。
但滇池的命,恍惚间又换了模样。水涝渐远,水干又来。你要说以前水是气势汹汹的汉子,到后来倒像个消瘦的孤女。库容从唐宋的十八点五亿,一路掉到十三亿出头。连补水都成了大工程,牛栏江搬水进滇池,大家像养病中的亲人一样紧张,每一滴都不敢浪费,好比守着家里最后一坛陈酒。
记得有一阵子,湖边的草た扎扎实实,九成湖面都绿得耀眼。等到围湖造田的热潮起来,二十平方公里说没就没,“新田”没种出啥好果,反倒叫滇池又伤了一回。种田人的苦,做工程的人更苦。填出来的地,每年亏钱,甚至办农场都不见效,说起来,谁那时候不为土地和水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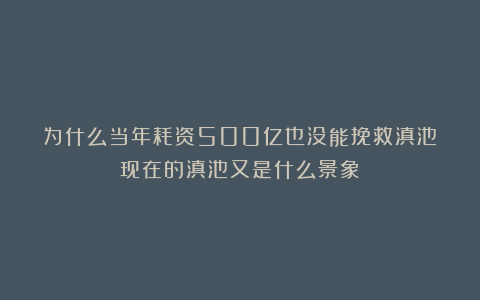
后来治理滇池,500亿砸下去,只为能多看到一抹蓝、闻一口清新空气。有的人觉得钱投了没回头,湖面上的变化没那么快,但水体的修复和人心一样,慢慢磨才见成效。泵站一座又一座,农田的灌溉线爬满滇池边,昆明的水产品,八成来自这湖。有人嘴上喊“母亲河”,有些人只是习惯了家常便饭——早晨的鲫鱼汤,夜晚的虾米粥,这口吃喝其实都系在湖里。
在滇池边,旅游的发展也上了点台面。翠湖、西山、海埂,公园修了又修,每年来看湖的人都念着,“真挺美”。可湖边的老人都知道,这美景来之不易。水质治理,既不是一锤子买卖,投钱得等回报,治污要守几年、十几年。哪怕蓝藻还时不时抬头——那玩意儿,像是湖水里酱油抹锅,苦得发涩,久了连空气都捂得发闷。治理蓝藻,多少科学家都挠头,钱花出去了,头发掉了一把一把,湖面才慢慢透亮一寸。
蓝藻的麻烦,细听就是个死循环。有年夏天,岸边的鱼像下暴雨一样浮起——湖面上一层油腻的绿色,谁看了不叹气?有人说,湖面是呼吸的肺,蓝藻一堵,水里的鱼虾得活活闷死。岛民抱怨:“政府能不能给咱清干净?”可专业的人知道,一清不干净,再来一波更猛的生长。母亲湖跟人在一起,治病不能心急,得慢慢调理才是。
偶尔下午,我也会打伞去湖边走走。翠湖的水没了当年的天青色,可有几丝新绿,倒也叫人放心。沿岸的花园,修修补补,变得热闹。治理队还在琢磨着下一步,城市生活的节奏仿佛都和这湖连着。我们常说,要为环境做点什么,可人在湖边,未必真的懂“保护”是怎么一回事。投钱是一回事,日复一日的细活才是长情。
滇池的命,和昆明这座城的故事拧成了一缕缠绵。有年水灾时,老屋里的炕头堆满了衣服,大人们在岸边喊破了嗓子。如今,湖水慢慢恢复,岸上的人也不急着跳脚,孩子们在水边捉螺蛳,老人拄着拐杖,盯着波光发呆。环境那些事儿,不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数据,更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水边留下的痕迹和故事。
说到底,滇池能不能重回最初的样子?谁也不敢拍胸口。水里浮沉过多少人的命运,这湖还在慢慢转好。也许还有很多难题没解,也许再过些年,水会更清,鱼会更多。只是每次踏到湖边,总想到那些曾为滇池操心的身影——他们的焦虑、期盼、失望和坚持。湖水总是流淌着人间的苦乐,我们是路过的看客,也是参与其中的人。
也不知道下一代的孩子,会不会还能在这湖边奔跑,笑着捧一把湖水喝下。你说这样的希望,是不是也值得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