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2025年第4期封面
苏新平 《侧躺的男人》局部 2023年 布面油彩 200×160cm
探索与建树
本期探索与建树专题刊载4篇学术论文,现将论文全文或提要发布如下。
苏新平
[美]阿克巴·阿巴斯
近些年来,苏新平创作了一批发人深省和引人注目的作品,在形式上和风格上比大多数同时代艺术家的实验性更强。在这些实验背后,有个问题在其艺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反复出现,这就是关于“什么是艺术”的疑问,每次都仿如初次提出一样迫切。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例如描绘内蒙古牧民与牛、马和羊的普通生活场景的系列石版画,看似简单直接,不带感情,但这些写实的图像亦往往伴随着“何为艺术”的严格追问,如影随形。对这个问题的探寻,苏新平从未停止过。这种对艺术的论述,本质上是他与自我的对话,并非与他人的辩论。爱尔兰诗人和政治家W.B.叶芝曾说过:“我们与他人争论,从中得出修辞;与自己争论,从中则得出诗歌。”在苏新平身上,与他人辩论产生了理论和解释,艺术作品则来自他与自我的争论。对他来说,艺术从来不只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一种生活方式。
一、石版画:抽象的影子
让我们尝试找出他早期的石版画《赶牛的妇女》和《赶集》有何特别之处。由此,我们会心生疑问,这些作品中人和动物的写实描绘,是否是内蒙古村落的生活写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内涵远非如此。首先,让我们先探讨记忆的问题。我们发现的不是一个直接的图像,而是对记忆中某个失落图像的追寻,这跟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伟大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有点相似。此外,记忆与其说是将经验回归到一个安全舒适的过去,不如说是对过去经验的回归,而过去的经验尚未被完全理解,仍然令人费解。尽管画面人物形象质朴,他们却表现得不知所措,以至开始散发出一点诡异,既熟悉又陌生。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写实主义是如何被抽象所染的,就像美国艺术家惠斯勒构思其母亲肖像时用灰色和黑色进行抽象的画面编排。第三,在苏新平的作品中,影子在走向抽象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石版画《影子之三》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试图触摸自己的影子,仿佛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影子之一》中,画面左侧的女人正在看着右边的一个(她的)影子。在这些石版画中,我们不仅发现了现实主义,还发现了记忆、抽象与影子如何在画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下一刻,现实主义框架开始分裂,记忆让位于梦境。《躺着的男人和远去的白马》被视为苏新平的代表作之一,画中人马相背,画面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让躺着的男人与远去的白马各行其道、渐行渐远。假若画面架构得以保留完整,则轮到影像自身分裂,如1995年的《作品系列》所见,逻辑屈从于梦境和无意识的非逻辑,现实主义被超现实主义所覆盖,而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其内在必然性的发展,不受外部影响,亦相当独立于作为艺术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本身。
《寂静的小镇之二》和《寂静的小镇之七》是苏新平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品。《寂静的小镇之二》展现了一日将尽时一个空荡荡的小镇。这里无人在场,两间石头平房投下的影子,我们在两者之间看见一道光被一根柱子的黑影分解。我们只看得见影子,却看不到柱子。请注意,天空是黑暗的,这使得光本身有点怪诞。这幅画给人一种神秘模糊的感觉,让人想起乔治·德·基里科的名画《一条街的忧郁与神秘》里空荡荡的广场。像基里科一样,苏新平作品中的符号是神秘和难以解读的,它们或许指向童年记忆里已然遗失的片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寂静的小镇之七》,主导画面的平房和骑马人实际处于画面以外。我们看到其黑色的剪影映衬在一座光亮小丘之上,就像在梦里一样。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梦境是通向无意识的捷径。
于此,石版画的世界呈现出由爱因斯坦、波尔和海森堡引入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奇异而反直觉的特性:不确定性、测不准,以及精确与不可靠性的矛盾组合。苏新平对艺术的看法近于量子理论——我们向他人解释艺术作品时应该清晰,但创作艺术作品时则必须精确,而对精确性的重视意味着对清晰度的牺牲——是以苏新平令人费解地指出,他的艺术是准确和模糊的。波尔有句名言:“任何不被量子理论震惊的人,都未曾真正理解它。”也许,我们对苏新平的石版画的理解,应该从意识到它们有多令人震惊开始。
二、摩登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果断地向全球世界秩序开放。在此期间,苏新平得以出国,包括在纽约度过了六个月。他参观了小型艺术画廊和著名博物馆,如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直接吸收了一些其他的艺术传统。回国后,苏新平的创作似乎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广度。空间背景不再是原来的小村庄,而变成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世人”如今是披上中山装或西装的城市居民,不再穿着传统服装;风格上,不再聚焦于黑白石版画,而是大型的彩色布面油画,以及反映城市生活的套色石版画。抽象、超现实主义和灰暗的色调,已经被一种表现主义所取代,在某些方面近似于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的创作。
然而,这些题材和媒介上的转换,并不能证明他关注点的改变;“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转移,仍然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些风格和内容的转换,不过是以新的方式提出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亦是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变化的一种回应方式。不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前卫艺术,苏新平总是将自己的艺术置于一个可接受的角度。从某个角度来看,他的艺术是在寻找一种精确的自我表达形式,即使其所表达的自我无法被辨认,就像《我》这样的自画像一样。
以《欲望之海》系列为例,其形式为石版画和布面油画。这些作品描绘了一些正在俯冲、坠落或奔跑的人物形象,以此回应现实社会中的变化,产生了令人困惑的欲望之海。这些人物似乎每日在忙碌奔波,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忙碌什么,没有目标地大步前行,不知去往何处。这看起来似是玩世现实主义,实际上却与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角度。苏新平画笔下的人物更多是困惑而非玩世,是迷乱而非知晓,他们都被自己所不理解的力量驱使。与玩世现实主义者岳敏君、方力钧或张晓刚等人不同——后者利用戏仿及荒诞手法,在意识形态上批判社会现实,而在苏新平的图像中,很少出现直接批评社会的表现。相反,他专注于描绘那些发人深省的充满矛盾的社交手势,而他则跟着他的人物角色追随着那些并不属于他们自身的欲望。
其中一个社交手势是干杯的动作,苏新平以一系列同名作品对其予以探讨。干杯是庆祝或纪念的社会仪式,但当我们一路追随这系列的发展,那些庆祝或纪念的内容便逐渐模糊起来,甚或从画面中消失。在早期作品如《干杯2号》《干杯5号》中,我们仍然看到穿着西装或中山装的男人在一片红色背景衬托下举杯,脸上挂着微笑。在后续的《干杯28号》《干杯29号》等作品中,一些人的面孔被涂黑,而女人们亦加入了这个群体。接下来是衣服与场合感被双双剥离。在《干杯55号》和《干杯56号》中,我们看到的是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这意味着没有“着装要求”来表明画中是什么场合。没有笑容,也没有眼神交流,只有半合的眼睑和张开的嘴巴,一直不变的是干杯的动作。苏新平密切地关注着“干杯”这一普通的动作,如何在仿佛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在这个系列中,“干杯”既指庆祝时酒杯空空如也,也可能象征着其他更模糊的东西,就像干杯这一传统行为一样,我们一直喝着,却不知道为什么。
《干杯》系列的尾声是一幅尺寸为240厘米×540厘米的大型油画,以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命名。在达·芬奇的壁画中,我们看见耶稣与十二使徒共席的一幕,而耶稣刚刚揭露了其中一个使徒即将背叛他。对于耶稣的宣告,使徒们对宣告的反应表现在他们的手势、面部表情上。在苏新平的画作中,我们看到中心人物张开双臂,似乎在宣告什么,这貌似苏新平穿着中山装的自画像。他的两侧各有六个上身赤裸的人物,每人手中都握着酒杯,以不同的手势、动作和表情回应着当下的宣告。然而,这些动作已经变得如此自动化和无意识,以至再无背叛可言。
1936年,查理·卓别林拍摄了一部伟大的喜剧电影《摩登时代》,讲述了工业社会及其非人化的影响。查理是一名工厂工人,他就像自动机械一样不断将螺丝帽拧紧,直至最后精神崩溃。苏新平创造的人物角色则属于一个高科技模控论和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后者生产出属于自身的自动机械形式,凡此均阐析于《欲望之海》和《干杯》之中。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版本的“摩登时代”。
三、一堆破碎的图像
2006年前后,在《欲望之海》和《干杯》之后,苏新平似乎将注意力转向了自然环境。通过制作一系列非比寻常的名为《风景》的油画,他“回到粗糙的地面”(维特根斯坦语),随之是几年后的《荒原》系列。先细看《风景》,在这件长幅作品中,我们看到在荒原的背景中,左边有个在自行车上努力保持平衡的男人,右边则有一些女人和光着上身的男人在干杯。不过,这些人物的形象在自然风景里显得格格不入、不适其所,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与传统山水画有着截然不同含义的景观。在传统山水画里,山与水、高与低、自然与人类诸对立面和谐共存,风景或山水就是这种和谐本身的展现。在苏新平的作品中,人类与自然世界只是在各自的差异中共存。图像之间彼此不和谐,每一个元素都有不同的风格,就像听一首自由爵士乐,每样乐器都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听起来或许一片混沌,但“混沌”亦可能是另一种秩序。在苏新平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图像的存在缺乏一个能够赋予其价值的综合体系,就如自由爵士乐的构成方式。秩序并非预先设定,而是有待发现的。故此,在1922年出版的《荒原》长诗里,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T.S.艾略特所称的“一堆破碎的图像”——用以指向传统的破碎——对苏新平来说,可谓无须痛惜。在2007年,破碎的图像就成了苏新平艺术创作的元素。《风景》所探索的并非末日以后的情景,而是尚未认识的事物秩序。
几年后,《风景》系列由《荒原》系列接续。后者并没有明确描绘一个废墟般的世界,亦没有刻画生态灾劫后的余波。相反,这些铜版画和纸上铅笔画的关键,在于它们将空间构想成碎片的概念。当风景被分割成方块再予以重组时,它就变得逼真又抽象、有形又无形、清晰又模糊。这种不协调源于一个事实:荒原跟未知且异常的空间混在一起。正如苏新平所解释的一样,他在纸上用铅笔涂涂画画,“记录了碎片化的生活方式,造成无数的碎片图像。它们汇集起来又构成意想不到的视觉景观。看似是偶然得来的结果,其实拼合的过程也引发了艺术家思想观念的植入”。(苏新平绘、黄立平主编:《苏新平:虚构的真实》,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风景》和《荒原》就是由一堆破碎图像构建而成的一场意想不到的视觉景观。
四、想象力的饥渴
创作《风景》和《荒原》的同时,苏新平还创作了《八个东西》和《灰色》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也有着属于自身的理论关注。什么是一个“东西”?它既不是某个东西(某物),亦不是没有东西(无物)。当一样物体变得无法确切具体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东西”。乍看之下,《八个东西》好像放大了苏新平其他画作里的树干;再看一下,我们就发觉它们不易确定,甚或不可界定。这些作品来自一种笔笔相生,以至“有无相生”的绘画实践。绘画可以无限时地延续,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正如苏新平所言:“我的绘画永远处于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停下笔来使之成为完整的作品,同时它又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可以继续画下去。”(苏新平绘、黄立平主编:《苏新平:虚构的真实》,第85页)因此,绘画中止时,并不意味着作品臻于完整。在我们面前的是个难解的谜题:完整的不完整性。重复亦是过程的一部分,这种重复并非普通意义下再现或复制已经完成的东西,而是特殊意义下对于不完整的延续。
与《八个东西》系列密切相关的是《灰色》系列,后者是一组布面油画,将自己表现为不具体、不明确的图像。我们通过初步观察能够作出的最明确解释,是它们都是由各种颜色化成的斑渍:黑、灰、白、红。仔细看,我们可以将这些斑渍想象成一座山脉,或烟囱冒起的烟雾,或轮廓不清的人形。就此而言,这些画面也算是一种罗夏墨迹测验。在这些心理测试中心理治疗师最感兴趣的是病人在图像当中看到了什么,并通过分析来确定病人是否患有如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障碍。苏新平的《灰色》亦令观众在图像内容和自以为看到的内容之间摇摆不定——并非为了确定观众的精神异常与否,而是为了展示日常感知里奇怪的不确定性。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擦笔纸堆》,一个用擦拭画笔的废纸制成的装置。这是个名副其实由废物制成的作品。苏新平以擦笔纸建造了一座金字塔装置,直达大型展览空间的天花板。不同于建筑师贝聿铭以昂贵玻璃及金属设计出卢浮宫博物馆主入口的著名金字塔,苏新平的金字塔是由毫无价值的废纸做成的,除了作为“艺术品”以外,似乎不具有任何目的。它亦不同于古埃及金字塔以沉重巨石制成,后者据称是法老的坟墓。然而,大约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道德寓言《拉塞拉斯》里如此谈论金字塔:“对于金字塔,从未有任何理由足以解释所付出的庞大制作成本和劳动……它的兴建似乎纯粹为了满足想象力的饥渴,后者不断捕食生命,且必须一直通过某种付出来平息。”对苏新平来说,用来平息想象力饥渴所付出的正是艺术,无论是石版画、油画还是擦笔纸。
五、行走的男人,远去的马
以下略记北京798艺术区内东京画廊的苏新平展览,并以此结束本文。展览以画廊总监田畑幸人一段简短的文字陈述开始,他提到自己为何珍视苏新平的作品:“(它们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他在追问事物的本质,追问人为何物。”随后我们看到各种作品。尽管展览标题指向苏新平最著名的石版画,但展览本身并不是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品回顾展。相反,他将过去40年间发展出来的不同风格作品都置放在同一个展览空间内,新作品轻易融入具象与抽象风格之间。画作《回头之马》里,一匹小马歇息于一匹大马背上,而远处还有另一匹小马;画作《背影》则展示了一个穿着暗淡西装的男人,在蓝色、白色、红色和橙色的背景衬托下背对着我们;而其他更抽象的油画令我们想起《八个东西》和《灰色》。结果是一种时间的压缩和并置,而非一个回顾展的线性叙事。
新作品中有两件尤为突出。首先是指向《回头之马》的一件雕塑,三匹不同大小的白马层层叠起,一匹站在另一匹背上。在俄罗斯套娃或中国套盒中,较小的部件会嵌套在较大的部件里;而苏新平的雕塑就像此二者的反转——当中不再存在部件之间的套合,只以重复的形式去把玩不同的尺度。尽管方法有异,但我们在三者身上都发现,重复的手法标记了作品的不完整。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是一组草图。在一条通往楼梯的狭窄通道的墙面上,我们看到一系列手稿的展示:一个双腿交叉着站立的男人,三匹大小不同的马依次叠放,一个全身红色的男人像马戏团杂技人一样在马背上平衡站着,还有其他身形偏长、带有棱角的人摆着各种姿势。草稿无须完整,而这令苏新平得以“撇开语法”来创作,为他的绘画赋予了一种卡通幽默的性格。这让我们想起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记、信件和笔记本的黑色墨水速写,当文字停止时,图画就出现了。直至近来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些图画为何如此迷人:因为它们并非从书写中诞生,而是来自其自身。同样,苏新平这些草稿亦不是为之后作品准备的习作,它们本身就是作品。
画廊总监田畑幸人指出,如今“只追求表面的轻薄的艺术充斥着整个艺术界,令人厌倦”。苏新平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过一个在超市买鞋的故事,试将前者关于肤浅艺术的讲法跟这个故事比照一下。超市没有一双鞋真的适合自己,因为制鞋史的发展遵循着自己的逻辑,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回到光脚的时代:“在没有任何’鞋’的概念的前提下,佛才出现。”对苏新平来说,只有在没有任何艺术概念的时候,艺术才会心有灵犀般显现。
【美】阿克巴·阿巴斯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远方4号》2018年 布面油彩 73×1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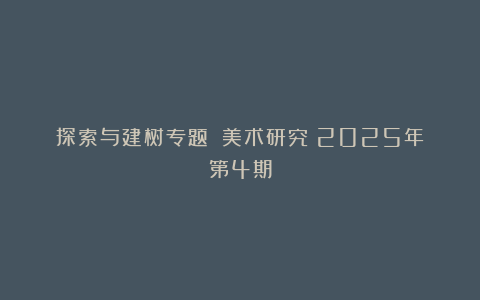
《空间6号》2020年 布面油彩 65×82cm
《行走的人2号》 2023年 布面油彩 300×200cm
《站立的男人2号》 2023年 布面油彩 260×200cm
《墙边的男人》 2023年 布面油彩 300×150cm
《讲道者2号》 2023年 布面油彩 200×160cm
《自画像》 2024年 布面油彩 65×53cm
《背影》 2024年 布面油彩 81×65.5cm
从私园,到公园:
摄影视域下中国古典园林公共化转型与视觉重构
周岚
内容提要:本文以摄影媒介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古典园林从传统私密空间向现代公共空间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视觉重构与文化意义变迁。研究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首先,聚焦摄影对园林空间属性的重构,揭示其如何将作为精神修行载体的私密园林转化为公共文化展演的剧场,通过影像传播消解园林的封闭性,赋予其大众观赏与意义再生产的功能;其次,分析摄影对园林记忆形态的重构,指出摄影将原本依托个体情感体验的园林记忆转化为集体共享的文化记忆,形成跨时空的文化认同纽带;最后,探讨摄影媒介引发的园林话语革命,论证摄影通过解构传统园林封闭的象征符号系统,将其转化为开放的视觉文本,在公共传播中衍生出多元解读路径,重塑园林文化的现代阐释体系。摄影不仅纪录了中国古典园林公共化转型,更是推动其视觉文化范式革新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既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性语境下的适应性转化,也揭示了媒介技术介入对文化遗产空间属性、记忆传承与话语建构的深层影响。
周岚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瑞典 ] 喜龙仁《苏州狮子林水塘和假山》 1920年代
周岚《从私园,到公园》 北京颐和园 2024年 艺术微喷 66×99cm
周岚《从私园,到公园》 北京宋庆龄故居 2024年 艺术微喷 66×99cm
周岚 《从私园,到公园》 天津人民公园 2024年 艺术微喷 66×99cm
周岚《从私园,到公园》 天津人民公园 2024年 艺术微喷 66×99cm
周岚《从私园,到公园》 广东余荫山房 2024年 艺术微喷 66×99cm
生活陶艺——面向大众的“新器物”
齐彪 吕品昌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在西方现代陶艺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陶艺崛起,“生活陶艺”即是继此之后的一个新概念。生活陶艺与传统意义上的生活陶瓷的一字之差,不仅说明了其出身来源,更体现了其被赋予的新的内容与涵义。它是在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艺术观念之下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亦即,它是从人们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在新时代、新观念和新审美需求之下,面向大众的“新器物”。
齐彪
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吕品昌(通讯作者)
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动人的雕塑——国家美展雕塑的情感叙事
焦兴涛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中国现代雕塑中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如何开启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叙事。雕塑家们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巧妙地融入了多层次的情感表达,不仅传达了时代思潮,还呈现了家国情怀和人性的柔情。通过细腻丰富的情感刻画,展现了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与张力。
焦兴涛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开渠 《农工之家》 1942年
潘鹤 《艰苦岁月》 1956年 高约100cm
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龙绪理作品《非洲 母亲》 1965年
四川美术学院 《收租院》( 局部 ) 1965年
孙闯《摇》1982年 高40公分
曹国昌 《儿子》 1984年 高46cm
刘威 《当年十八》 1991年 高30cm
霍波洋 《赵一曼》 1998年 高 11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