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谋老师《南街烟火味》读书札记
张慧谋老师在《南街烟火味》开篇便道:“印象里,小城南街是最长的一条老街。”
这句朴素的陈述,恰似一扇缓缓推开的木门,引领我们走进一条被岁月浸染的街巷。南街之老,非因岁月本身,而是因“一代代人把它走老的”——这轻轻一点,便道出了街道与人间烟火最本质的关联:街因人行而活,人因街存而聚。读罢全文,最动人处莫过于作者对南街日常的细腻描摹。
清晨清冷,“偶尔从街心走来一个乡下进城收尿人,冷不防叫一声:’有尿卖无?’街上才觉得有了点人气”。
这般市井画面,令人想起宋代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意境,只不过这里的叫卖声更加质朴,更接地气。古今街巷的烟火气,原来一脉相承。
张慧谋老师笔下南街的饮食图景尤为鲜活。鱼行里“鱼虾、蟹鳝、乌贼、章鱼、贝类,大海鱼,小海鱼,应有尽有”;菜市中“菜叶的绿,萝卜的白,黄芽白的嫰黄,芽兰豆的青翠,蒜叶的修长”。这些描写不着华丽辞藻,却让市集的热闹与色彩跃然纸上。不禁想起杜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饮食之美,或是苏轼“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时令之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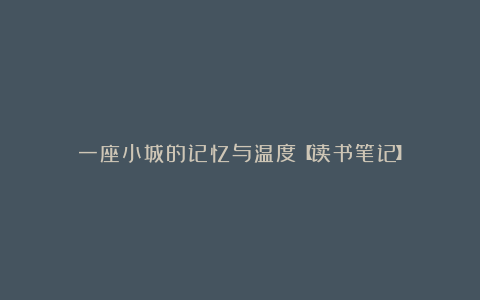
中国文人向来善于从寻常饮食中品出生活真味,张慧谋老师承续的正是这般传统。街巷与饮食,在中国文学中从来不只是背景,更是情感的载体。汪曾祺写故乡高邮的街市,梁实秋忆北京胡同小吃,皆是以味觉记忆勾连地域文化。张慧谋老师亦如此,他写跟随父亲买菜的场景:“一路上,我手脚都冻得发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冬天真冷。”寥寥数语,父子亲情、岁月流转尽在其中。
南街的可贵,更在于它保存着小城的历史脉络。潘屋巷祠堂那副“荆树有花兄弟睦,砚田无税子孙耕”的对联,黎屋祠堂的断壁残垣,临水宫六百多年的香火——这些不仅是建筑遗存,更是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张慧谋老师感叹:“一块身上刻着年号的老城墙砖尚且都能留了下来,而那些有眉有目有名有姓活生生的人…早已随风飘散。”这声叹息,与唐代刘禹锡“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苍茫感何其相似。
历史无情,总将具体的人事湮没,只留下零星的物证供后人凭吊。然而南街终究是幸运的。尽管“全变了”,但“小城南街的烟火味还在”。这种烟火味,不仅是鱼行菜市的交易热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证明。作者注意到,虽然正规市场冷清了,但小巷和正南街反而热闹起来,“街道两边路面,摆着菜蔬、鱼肉、鸡鸭、番薯、芋头等摊档,应有尽有”。这种自发形成的市集生态,恰是街巷生命力的体现。
张慧谋老师的南街行走,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寻根。他寻找的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座小城的历史纵深。从明朝洪武年的临水宫,到清朝形成的鱼行,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书店,时间在南街叠加沉积,形成独特的文化地层。这种寻找令人想起木心所言:“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南街的烟火味,正是这种“慢”的生活节奏的体现,在日益同质化的城市发展中显得尤为珍贵。纵观全文,最打动人的是作者那种平静而深情的注视。他没有大声疾呼保护老街,只是细细描摹所见所忆;他不作怀旧悲叹,只是如实记录变迁。这种克制反而更具力量,让读者自行体会南街价值。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热闹是热闹,就是苦了行人,来往的摩托车有时扎堆,停在街心,交通实在不便。但是,恰恰这样,才能更加体现南街的人间烟火味。”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解——真正的烟火气往往伴随着些许混乱与不便,过分规整的秩序反而会扼杀街巷活力。
南街的故事,其实是中国无数老街巷的共同命运。在疾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如何保留这些街巷的烟火味,如何让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张慧谋老师的文章提醒我们:街巷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其中流淌的生活之河;不仅在于保存过去,更在于滋养现在。合上文章,仿佛还能闻到南街的鱼腥味、蔬菜的泥土味、打铁铺的铁锈味,这些气味混合成一种叫做“故乡”的味道。
张慧谋老师用他质朴的文字,为我们保存了一条街的体温,也让我们想起属于自己的那条老街。或许每条老街最终都难逃消逝的命运,但只要还有人记得、书写,那条街就永远活在人间烟火中。
乙巳年闰六月廿九夜,整理于三楼“曲尺巷”
图片来自张慧谋老师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