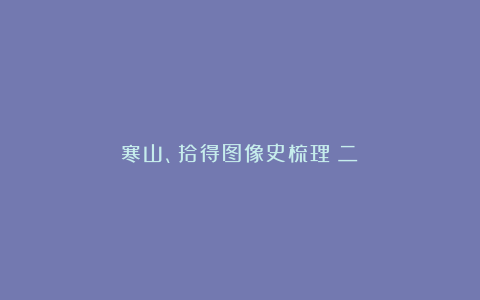寒山·拾得-和合二仙无疑是中古至近古中国人创造的一大宗视觉图像材料,这些材料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被规模化复制并在不知不觉中演化,不仅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态,而且当代的研究更进一步思考图像积极地向社会反馈着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意义。在图像作品的形制和形式层面讨论从(可能)北宋开始至近现代、和合二仙由寒山拾得演化而来的图像历史,不仅在纯粹图像的形式意志自身的发展逻辑层面,且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的多领域变迁。凡是图像的转向都是系统性的运动,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机缘的湊合。这一转向系统的子项条件大致分为外在的经济条件、社会心理、文化宗教、受众对象、展示场景和内部的图像形式意志、视觉性等方面。本部分试图补上对影响寒山拾得图像演变关键阶段即南宋至明代的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描述,并以此为依据继续探讨明代以后该图像演化过程中显隐两个层面的历史。
一、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民间神祗体系的形成以及官方的敕封和对淫祀的干预
论者普遍将中国社会早期的现代性出现认定在明代,如英国牛津大学的柯律格教授,这种议论的核心意见是将明代尤其是江南农桑业以及手工业经济的繁荣导致城市化的雏形产生以及离开永久居住地农村的都市平民阶层出现。而本人更愿意将此关捩前推到南宋,将这个时间节点看作前现代中国母体孕育出与都市商业化文化进程及其文化消费相适应的、具备一定现代性特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唐代尤其是唐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仍是属于自然经济,即多数人居住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奢侈品、食盐、茶叶等物品的长途贩运只是一种补充。至宋代初建前后,中国经济的重心移向南方既成事实,又一百多年后宋朝廷迁往杭州,当时大杭州地区的人口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万左右(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政权在地理上的南北迁移,更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中世纪转折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这一转折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几乎所有的领域,而因经济活动的活跃度和规模的急剧扩大导致宗教方面的变迁、尤其是民间神祗体系的形成,成为实际社会转折的一项重要内容。
南方城市人口的激增在南方形成了以杭州地区、环太湖地区、福建泉州地区、南昌与景德镇等地为枢纽的城市商圈;两季稻作的成熟引进使得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基本足以供给,有些地区因此有盈余的土地得以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水果、桑叶、药材等经济作物;堤坝、水闸、水车、深耕等农业、水利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江南地区密集的河网使货物交换的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可以方便实现、成本费用远低于畜力、人力的车载担荷;造船业的发达使沿海航运也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沿海外贸港口官方和民间的对外贸易异常繁荣……经济的繁荣带来社会财富积累,民间识字的人群迅速扩大。据统计,在科举取士人数并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到13世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由11世纪7.9万增加到了40万人,这群人中最终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或科考落第的有文化人群参与到社会活动的各领域之中,也包括经商和手工业生产等活动,反过来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人才。
科举、航运、经商、手工业直接和间接带来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内部竞争程度的加剧。对陌生领域的不断探寻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有望彻底改变守着出生之地生活一辈子的人生境况,但身世和经营的不可预测性风险也在增强。与此相适应,原本固守一方的地域性民间信仰诸神因为人员流通的频繁、活动范围的扩大,地方性神祗随着商旅和仕途扩散,在其中逐步拔擢产生出全国性的神祗;原本主要职司自然和生死的神灵也出现范围更广的灵力,如掌管文运、财运、婚姻、子嗣等专职的神仙。在12、13世纪的中国已初步形成覆盖全国性的诸神体系。万回、志公、魁星与文昌帝君、招宝七郎、布袋和尚、济公、刘海、八仙以及寒山、拾得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前后出现并被确立地位。
随着受教育人群的扩大,寺庙、道观里也出现了较有文化素养的僧人、道士,他们成为精通各家经文的博学有识之士,他们借助诵读经文的力量为官家沟通天人、护国佑君;也为地方设坛司礼、求雨降瑞;为民众扶乩作法、祈福消灾;同时利用掌握的宗教知识对传统宗教进行普适化、世俗化的改造,使宗教更加深入民心。如通过强化玄奘法师翻译的《心经》和《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影响力和《华严经》中善财童子参访的场景,配置出观音与文殊、普贤并列的菩萨崇拜体系,在宋代形成“ 三大士 ”(地藏王菩萨和三大士平列要到明清时完成)的组合。
大量地方性的神祗以及迅猛出现的全国性的各类职司的神灵、仙道,致宋、元、明时期民间信仰神祗体系的过于庞杂,淫祀泛滥,越级祭祀、非官方认可的神明祭祀等行为大行其道。《礼记》将“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这一概念成为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一直注重规范祭祀行为,强调祭祀需符合身份等级和礼制要求,因而“淫祀””客观上干扰了官方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
地方神升级为全国神需要有一个认识以及固化的过程,专业的宗教机构为了凸显自己的禅林、道观地位需要推出具有自家烙印的全国影响的偶像,官方有鲜明的控制宗教体系、规范崇祀制度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在北宋晚期开始直至清代中期这五、六百年间,在民间信仰领域一直存在着民间、宗教界、官方互相博弈的情况,如诸神体系中个别地方神升格为全国神、庞杂的诸神体系被不断删选、叠代和简化、民间形成影响力共识的寺庙、道观以及诸神不断获得官方认证和敕封的现象。寒山、拾得和丰干三贤晚唐时期还属于天台地区的隐逸传说,代表着一种洒脱、退隐的出世态度,还属于禅宗思想体系的文本传播;至北宋可能已经出现不修边幅、乱头粗服而与自然的观念相协合的图像,寒山拾得的传说和诗歌里有佛家的哲理机锋,也糅合了道家的出世玄谈,甚至包含传统儒家的经典痕迹,这些观念对于在文人圈争取更大的传播面有价值;我们并不清楚南宋时图像里寒山、拾得的贫子造型是原典文本首创还是这种颠倒淋漓的邋遢仙态为当时禅画里神仙们的观念化造型,其目的或许为了在民间传播增强其亲和力,但这样的同质化造型无疑对于突出各自的个性会受影响。随着南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流通的增加,在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于和合利市、吉庆美满的祈求日益强烈。此时的寒山、拾得和同时期万回、布袋和尚、济公等神祗除了形象之外在神格上也产生了同质化的情况,这体现了代表各地方寺院、道观、官府、民意为争取各自的神祗地位而进行的激烈博弈和内卷。在此过程中因为所谓的灵验以及好评渐获社会的认可、赢得广泛的民意,统治集团会在此民间遴选基础上颁布敕封,使之纳入朝廷的神祗体系。如后文会提到的刘海在元朝元世祖时被封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再加封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小几十年间由“真君”而臻“帝君”,不可谓不荣耀,或许是表彰他远离谋反之臣的明悟见识。
由于神祗和崇祀的寺庙道观是合二为一的,朝廷通过对神祗的爵位、封号的赐予,使祀庙甚至整座山林都得以封荫沾光,因而各地的祀庙和信众包括地方官员都有相当大的积极性参与其中。将一些在民间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神祗通过朝廷敕封、官僚机构负责修缮和主祭,使各类神祗各领封赏,从而虚拟纳入到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体现无所不覆的君临神界的皇权力量。
但是由于对神的封赐体现了多方的利益交集,因而地方各种势力都会很热衷此项工作,甚至官方派出考察神迹及应验力的官僚也可能涉及其中,在此过程中各方结成了某种非正式的利益联盟。但这样的局面是朝廷所不愿意看见的,因此朝廷在宋代中期(1075年以后)在一段大力赐封、建立诸神体系以后,12世纪末期朝廷对民间冒出来的一些新的、未经审验的神祗和建祠奉祀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即对所谓的“淫祀”的打击。不管是赐封也好、打压也好,其实都是朝廷对意识形态和地方势力的控制手段。朝廷对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构建与控制的工作从来不曾停止,如寒山、拾得从晚唐开始的诗坛影响建立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被封为和合二仙,经历了一番长期的多方互动的过程,因而我们在考察民间信仰神的演化现象以及图像演变的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一过程和经济发展导致民间信仰的细分以及朝廷的封神措施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对应关联;同时也不应忽视一些广有影响力的大神竞争某些爵位和封号中处于下风后在地方上影响力的不绝如缕现象。
宋时,杭城盛行腊月祀万回哥哥。万回,是和合之神,据说祀之可使人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三)”。万回一直是民间传说里的神人,其实,万回的这种和合神性在唐代就已经萌芽存在。唐代敦煌文书 P.3490《愿文》载有一段发愿文,如下:“弟子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当州左马部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李神好,奉为国界安宁,人民乐业。府主使君长延宝位,次为己躬吉庆,障不侵,合家康宁,所求得遂。敬绘万回大师,愿垂悲圣力,救护苍生,一心供养。”那时万回已经有人为求平安吉庆而请人绘像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唐代的万回形象什么样子,只知道南宋的时候其像蓬头笑面,身著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看似无厘头的言语和举止往往能应验,因而民间将他当做吉祥的“和合仙人”奉祀。宋代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李小官谎称要买花去供奉和合利市哥哥:“你不知,我买来供奉和合利市哥哥的”。到了宋代,万回除了有了“和合”之名以外,还有了“利市”的涵义。“和合”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合”统指如意圆满,狭义的和合指男女配对的幸福美满。说明在宋代的时候,万回不但具备能让离人虽万里亦能回还的团圆神通以外,又具有了“垂悲圣力,救护苍生”、更兼助人招财利市、婚姻好合等职司。明代通俗文本《万法归宗》卷二 “和合秘法”中“和合咒”云:“……专管人间和合事。和合来时利市来……男女相逢心相爱,管谋买卖大招财……吾奉万回歌歌张圣僧律令勅。”几乎已经是民间的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仙。
图二十 元、明代尚流传的万回像 左手擎鼓,右手所执棒已失
但唐宋元明之间有可能成为“和合”之神的“候选”者其实还有好几位,在“和合二仙”正式命名还没有固化到寒山、拾得头上的时候,万回之外,至少还有布袋和尚、海蟾子等人,其中布袋和尚还差点和万回搭成了和合对偶神组合。《宋高僧传》最早记载契此生平,书中对布袋和尚的描述就是’形裁腲脮,蹙额皤腹……“长得矬而肥,愁眉苦脸,大腹便便。这是《宋高僧传》成书也即北宋初年时布袋和尚的官方认可形象。
图二十一 北宋崔白画苏轼题《布袋和尚真仪图》(愁弥勒)拓片
到了金代元光癸未年(1223)也即南宋嘉定十六年,有一幅《布袋和尚图》,在这个画面上,他不再一脸愁苦,而是笑逐颜开了。据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到金代元光二年(1223)之间,布袋弥勒的情绪形象发生了重大的逆转,这一逆转的关键时期大概会在南宋年间。这一转变是宋代佛教进一步融入市井生活、寺院经济与民间信仰结合、形成“庶民化佛教”与“佛教庶民化”的双向互动的结果,和佛教从早期的苦难救赎,逐渐发展为大众提供精神慰藉的平民宗教的发展步调相一致。
图二十二 南宋梁楷和法常的《布袋和尚图》,已经完全转化为嬉笑的面相
布袋弥勒原本是一个引导大家放下的神灵,他的布袋,就是他的负担与所执,宽心忍辱、心无挂碍,才是核心。据明代田汝成叙述,宋代岳珂曾经赞布袋弥勒像::“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言简意赅。但是,本来禅意的叙述,被市井的意念解读成了布袋的神奇魔幻,布袋自此渐被投射了更多的世俗欲望,放下的布袋被满满地扛起,幻想里面装满了富贵财货与名利欲望。明代开国时奉洪武帝命住国清寺的昙噩禅师撰写过《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文中叙述布袋弥勒用布袋罩住木材,让岳林寺的师父在寺院井中取木材,取之不竭直至大殿建成。这种神迹,在市井小民眼中,就跟要啥有啥的聚宝盆别无二致。这样的神通正是如意和合、招财利市的最好的形象隐喻。
前面提到过写过《四睡图》赞的南宋禅宗曹洞宗僧人如净禅师曾有《源山主求赞顶相》云:“有时随搂搜,若万回老子欢喜;有时放歇蹶,若布袋和尚颠狂”。这里,如净禅师把万回老子与布袋和尚并列,呈现了南宋时代僧俗两界对万回、布袋并列关联的习俗。不管后来世俗有没有最终选定布袋(弥勒)、万回成为和合二神,本文开头所引的团形《四睡图》和朱见深的《一团和气图》已确实将南宋时候形成的笑弥勒形象植入这一构图的中心,也不管他是丰干也好、慧远也好。
图二十二 南宋成对花钱(正面)肩鞋履、提口袋的布袋和尚和执鼓与捶的万回
图二十三 南宋花钱(背面) 布袋和尚后铸“招财利市弥勒佛”和万回背面“香花敬重万回哥”
上图转引公众号“乐艺会”《花钱中万回为何与弥勒并列:老赵闲聊僧伽艺术图像系列8》,该文对于南宋布袋和尚与万回两神的盛祀以及花钱上成对出现的现象罗列和考证颇详,足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昙噩禅师作为来自台州的临济宗元叟行端禅师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寒山、拾得的铁杆粉丝(在现在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元人佚名《四睡图》上是重要的题赞人之一,题诗洋溢着玄妙的禅意——可详见本“木图时代”公众号《元代佚名<四睡图>考略与索隐》一文),他在为布袋和尚作传的时候则一反为《四睡图》题赞的态度,大肆渲染着和尚不可思议的神迹。昙噩是禅林中享极崇高声誉的禅师,他一定深知颇具小说体的文字对于民间信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可见这个时候的昙噩还没意识到布袋和尚这样的招财利市的神通和神格和当时寒山、拾得构成竞争的关系,因此可以认定作为未来的和合对偶神,在元末明初似乎还和俗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秉持脱俗的气质与禅机,不慕名利、承担着警醒世俗的职责。
图二十四 南宋寒山、拾得警语花钱 正面为两人的组合图像,背面为“触来勿争竞,事过心清凉” 。图转引公众号“乐艺会”《花钱中万回为何与弥勒并列:老赵闲聊僧伽艺术图像系列8》
图二十五 元代因陀罗《寒山拾得图》局部 国立东京博物馆藏 两人嬉笑组合仍是典型禅画意境,但从诞生之日起一直不离手的经卷(或诗稿)与扫帚母题的消失是不是透露即将开始的图像寓意的某种变化。
似乎丰干脱离寒山、拾得“单干”后曾经也有过和布袋和尚短暂组合的苗头。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曾经论述过在大众求对偶集体心理的影响下,丰干较难永久楔入寒山、拾得这对越来越牢固的骈联组合(上图元代因陀罗画的跋语“试问丰干何处去,无言无语笑呵呵”颇能说明问题)。但这种落单的孤寂并不适合临时的凑合,因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丰干、布袋和尚组合只是短暂的,很难得到僧俗两界的认同并赢得大量拥趸。
图二十六 传南宋李确画,偃溪广闻赞《丰干布袋图》轴,纸本墨笔,日本京都妙心寺藏
除此两位之外,刘海、铁拐李、张仙等也曾经有过竞此和合二神岗位的简历。
图二十七 明代宫廷画家刘俊《海蟾子》 绢本设色,藏河北省博物馆
传刘海,五代时人,本名刘操,字昭远,又字宗成、玄(或元)英,居燕山一带,先为辽国进士,后官至后梁燕王刘守光的丞相。据说一日有道士至,在其面前垒卵叠钱警示,刘海觉醒,次日即解印、着道士服、佯狂出燕国,随道士而去,因此免受刘守光谋反祸。刘海出家后,取道号“海蟾子”,称为刘海蟾元朝元世祖封刘海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再加封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后来,民间因这名字附会上了刘海戏蟾的传说,刘海遂成为能给人间带来钱财、子嗣的吉祥神。刘海的形象是中国中古至今神祗里最接近寒山、拾得形象的,在后来的图像里很多工匠也常常有意无意将他与两位混淆。
图二十八 明 商喜《四仙拱寿》 台北故宫藏
由于本文以专门叙述寒山、拾得的神格演化的图像史为务,关于其他更多宋、元、明时代原本有望竞得“和合”封号的神祗退出竞争或另辟神境的历史本文不作过多叙述。
三、寒山、拾得成为和合二仙的隐喻和符号化
隐喻原本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是一个语辞对另一个描述某一事物的语辞的替代。替代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描述更加感性、更加畅达,因而“隐喻”的喻体往往具有形象和习见的特征;其次,由于隐喻使用范域的不同,其应用有对喻体形象的玩味和借助喻体以方便明理的目标区别。
1、诗之象与易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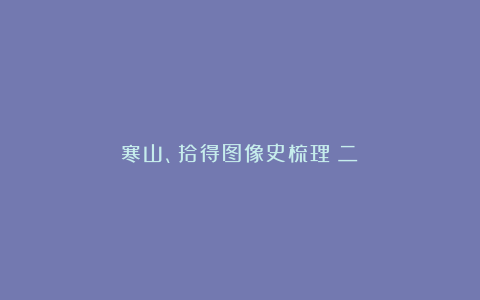
钱锺书《管锥编·二乾》:“《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爲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着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另成章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
钱先生在这里拈出了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易之象”与“诗之象”。所谓’易之象”是指一切提出观点、论说道理的文字,为了是道理说的更加明白、易懂,需要打多个比方,举例不少形象来佐证。但这些比方和形象只是辅助,只要接受者明白了事理,这些比方和形象就可以忽略,或者说只要能够将道理说明,不一定非要执着于一定的比方或形象(sign),换其他的也一样可以。所谓“诗之象”则不同,诗里的形象本身就是诗人自己因此感动的对象,他将之叙述或描绘,以期打动读者。形象就是诗歌本身,换了形象那就成了另一首诗了。这里的“诗”可以是涵盖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可以是绘画、音乐、雕塑等,那么所谓的“象”(icon) 就是诗歌里语言文字描写的意境、绘画里绘制的形色表象、音乐里的音符旋律、雕塑里的实体外形。钱先生这里使用的 sign和icon是语言学、符号学里的概念, 前者指“符号”,后者指“表象”;符号用来指代,表象足以玩味。
我们并不认为寒山、拾得和丰干的故事在一开始就被当作禅意观念的表达载体(sign),我们更愿意认为是宋代画家从寒山拾得的故事里读出了寒山的洒脱与诗意、拾得的不拘于形的透彻以及丰干对他俩行为的睿智鉴识。寒山、拾得的形象不惟契合禅宗的思想,更因其独特的形貌个性,塑造了两位迥异于普通僧众的特立独行的觉悟者形象(icon)。从这个视角看闾丘胤《寒山诗集序》文本,就是一篇充满意趣和禅味的值得读者传诵体会的小说。但地方、寺院、民间对寒山、拾得存在着神祗升级以及世俗化转向的需求,原典故事对于故事本身的传播固然有价值,但大众过于执着于故事本身的奇诡,尤其在禅家看来容易落入舍本求末的窠臼。因而也只有将艺术形象“诗之象”顺利转化为宗教符号的“易之象”、防止众生“之囿於一喻而生執着也。”( 钱锺书《管锥编·二乾》),就是说如果大众将寒山、拾得的故事当作艺术作品玩赏容易执着于表面的故事“能指”而忽略了该故事所要传达的意旨“所指”,宗教只希望将寒山拾得的故事当做禅理寄宿的表象和符号,而不希望大众沉湎其中不可自拔。在禅宗看来,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经书语言并非真正的实在,能指并非所指。禅宗因而认为“迷人从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人的手指指示了月亮,就像故事指示了禅义。如果一味执着于故事本身则容易忘了对禅理的探求,就像把手指当做月体一样地落入谬误。
2、寒山、拾得的符号化阶段
将“诗之象”向“易之象”转化的第一步是必须做到“祛线性”。任何故事都在时间上展开,尤其是语言文本。当人们沉浸在线性的语言叙述的时候,故事本身叙述和场景描写具有魅惑性,只有摆脱这种魅惑,才能将“寒山、拾得”从形象的陷阱中解脱出来。这一“袪线性”的第一步是“图像化”——利用图像的共时性特征,消除故事的历时性魅惑。有关北宋的三隐或寒山拾得的绘画并没有可靠的传世品,但早期的作品一定和文本之间一定存在着较为忠实的关系,图六南宋马远的《丰干、寒山、拾得》对屏、图十一传为刘松年的《寒山图》当是那个阶段的图像。
图像化的目的是为了将形象从线性的叙事理剥离,避免大众对线性叙事的沉湎,但图像化的弊端顷刻显现:图像本身具备色彩和造型,这种表象的“魅惑感”同样容易使人沉沦不可自拔。所以 将“诗之象”向“易之象”转化的第二阶段会有现成的两种解决祛表象魅惑的办法——
钱锺书《管锥编·二乾》:“游词足以埋理,绮文足以夺义,韩非所爲叹秦女之媵,楚珠之椟也(《外储说》左上)。王弼之惇惇告说,盖非获已。《大智度论》卷九五《释七喻品>言,诸佛以种种语言、名字、譬喻爲说,钝根处处生着。不能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以权爲实,假喻也而认作真质……古之哲人有鉴于词之足以害意也,或乃以言破言,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辄反其语以破之……妙悟胜义不至爲一喻一象之所专攘而僭夺。”就是说为了防止单一的形象导致读者或观者执迷不悟,古之哲人常常用不同的、多个的形象来揭示同一个道理,使不同的形象形成互相抵消之势,从而完成直抵原旨的目的。早期的佛画形象往往人物形象高古、场景幽奇,每令观者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为表象迷惑。如能将同类的图像以联屏的办法成堂张挂,则不同的形象互相抵消,森然万象皆空,唯现慈悲一殿。传为贯休创作的《罗汉图》以及南宋年间传向日本的宁波佛画都是此类案例。至于寒山、拾得图像也不乏与丰干并置(图六)、寒山与拾得分屏(图九)的现象,甚至设想还有与其他禅林图像共同悬挂于同一空间的可能。
《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正因为图像表面的色彩、形象存在着表象魅惑的风险,为了避免心为形所役,应减低图像的色彩和形似迷惑,纯水墨的、不求形似的简笔写意风格作品应运而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宝绘堂记》)简淡的风格、变形的形相,体现了一种脱略表象、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直观简约主义思想。这样的绘画风格符合佛家不执着于文字、形相的禅理,因而被称作“禅画”。而在禅画中,丰干和寒山、拾得题材正是图像的大宗。
图二十九 传为五代 石恪《二祖调心图》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传为五代石恪的《二祖调心图》显然不具备五代人物画的特征,而与南宋梁楷、法常一路的简笔大写意意趣异常接近,其中伏在虎上的僧人不管是伏虎罗汉(论者认为支颐沉睡者左手原本为掣龙姿态)也好、丰干(又有论者认为这两图是拼合而成,伏虎僧人图边上可能是寒山、拾得,裁切了,后与另图合裱)也好,在马远的基础上图像已经完全呈现出抽象化的表意趋势;法常的三隐图像也在原先相对写实(见图四)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写意的倾向(见图五),而与禅界交往甚密的参禅画家梁楷则在形相抽象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见图五)。
这类禅画作品开始很可能主要流传在梵刹禅林以及部分文人中间(且为来华日本僧侣所喜爱被大量携带回国,而在国内社会上则流传不多),并且完成了在禅林内部将丰干和寒山、拾得形象剥离原典、形成抽象化的符号进程。但要将当地或本寺的神祗获得朝廷的赐封才能具备更大的社会传播影响力,并为在地官府、寺庙带来实在的好处,也为当地的信众带来更加踏实的护佑感,显然光在禅林间传播的抽象化的写意简笔画无法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甚至可能被主流画界认为粗陋不雅,因而个人认为这一阶段的寒山、拾得的符号化之路属于禅界精英层面的功课,对于神祗的大众化、世俗化之路来说甚至可以认为是入了歧途;而且在大众间,寒山拾得故事受原典生动的文本以及小众的诗歌内容牵累,其形象更多显示为“icon”,在向世俗福瑞隐喻“sign”转向方面尤其是在民间大受崇祀的“和合”神的占位竞争中比万回慢了一拍。
地方神祗得到朝廷认证的重要途径是验证其神迹的灵力可征,这一验证方法除了官府、祠方的努力以外,民众的笃信与口碑将起到极重要的作用。创造为公众所喜闻乐见的符号化、多媒材、多场景的图像将成为同一时期或稍后一段时期亟需调整的传播策略。
3、从“四睡图”到“一团和气”的图像演化
在北宋晚期和整个南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表现城镇乡里人物和风情的风俗画。“这些数量可观的作品反映了宋代绘画中的“公众转向”,把再现对象从宫廷和贵族扩展到街坊和村野。”(巫鸿《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这一原因已在前面说明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众对通俗文艺作品的需求增大以及民间在日益广泛、多元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生活状态中对世俗幸福的渴望。
当丰干和寒山、拾得已经由文本转化为图像,图像便脱略了文本的线性叙事而置换成图绘场景法,从而完成了初步的符号化转型;转型的第二步在禅林间运用了同类图像多屏联挂、以图像互相抵消的办法避免观者执着于原典、其次采用禅画的形式以杜绝形色的夺人眼球。禅林间的精英化路数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于是一种人虎共睡的寓意化场景、即《四睡图》题材出现以及将该题材形式进行装饰化、即《四睡图》形制的团块形构图获得了大众社会的普遍认同。
四睡图以前的三隐题材绘画图像大都以分屏的形制出现,虽然看起来图像有抽离场景的摆拍嫌疑,但细读《寒山子诗集序》发现其实图像表现的都是序言原典里的叙事瞬间。南宋至元代三僧题诗的《四睡图》图像其最大的转化是人兽四者相聚成一团酣睡的图像出现,这在《寒山子诗集序》和传说里都找不到对应的叙事,这就是一个没有上下文的虚张的寓意场景,也就是说天台三隐的故事至此已经脱离了原典的叙事而转换成纯粹的禅宗意象表达,成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乾》里标示的典型的济河之舟、示月之指的“易之象”了。有明确的证据“四睡”图像在南宋已经出现,有关四睡题材的图赞出现在许多禅师语录中——
如《如净和尚语录》卷下赞佛祖中有赞《四睡图》:“拾得寒山,老虎丰干。睡到驴年,也太无端。咦,蓦地起来开活眼,许多妖怪自相瞒。”如净和尚是南宋时期的僧人,隆兴元年(1163年)出生,俗姓俞,号长翁,明州人,嘉定三年(1210年),受请住持建康清凉寺。之后又历住台州净土寺、临安净慈寺、明州瑞岩寺。宝庆元年(1225年),奉敕住天童山景德寺,世称“天童如净”,是南宋禅宗曹洞宗的传人,发展了禅宗的“默照禅”,日本名僧道元来华师事如净,得曹洞宗旨而归,归国后创立宗派奉如净为始祖。
图三十 元代佚名《四睡图》局部
在我《元代佚名<四睡图>考略与发微》中提到的法常(牧溪)的师尊《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五有《丰干寒拾虎四睡》图赞:“善者未必善,恶者未必恶。彼此不忘怀,如何睡得着。恶者难为善,善者难为恶。老虎既忘机,如何睡不着。”这种惊世骇俗的人虎共睡图像无疑博得了无数惊异的眼光;由于并无上下文的线性关联,因而不存在引发大众对“能指”的执着,在佛家丛林仍不妨碍做到禅机的阐发。
将原典里丰干骑虎传闻的叙述文本改成三人一虎和谐共眠的图像无疑是天才的创造,这一图像题材无疑是禅林传播策略的“公众转向”。以上宋僧提到的《四睡图》都已看不到了,不清楚那些画法是简笔写意的禅画还是其他如明州佛画周季常、林庭珪们那样的设色明艳的工笔绢本画,目前存世的以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元代佚名《四睡图》为最早存世图像。
以《四睡图》作品产生标志着原本天台三隐题材由禅画对游戏人生、脱略一切羁绊的生命外在潇洒形态(icon)的羡慕和玩味转向向内观照、求之乎心的理赜表达。画面的生气渐失,拍手、大笑演化成了垂首酣睡,直至固化成为一团和气的符号化图像。
明代中期成化皇帝朱见深创作的“一团和气图”为大众所习见,正如皇帝朱见深自己题字所说的,是表现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虎溪三笑”、儒释道三家融合、天下一团和气的愿望。
历来都把“一团和气”图像形式的原创归于成化皇帝,尤其觉得这种三教合一、圆融无间的观念和这种构图形式结合颇具创意,但直至看到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院所藏的《四睡图》(见图十八)后,瞬间觉得很可能是成化皇帝只是借用了当时现成的“四睡图”圆团构图来传达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已,至于是朱见深自己动笔还是御用画师代绘制已不重要。托普卡帕宫的收藏记录清楚表明,这幅画是15世纪(几乎和成化皇帝同时代)传入大不里士(当时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最大城市、始建于3世纪,历史上多次成为王朝首都,古代为四方往来通衢)的中国作品。三人一虎加一鸟形成团块,去掉了自然山水背景(以一鸟为自然界象征),比元代佚名的《四睡图》和日本默庵灵渊等作品中三人一虎成团的构图更加收缩,形成几何圆团;和朱见深《一团和气》构图相比,并没有做到完全的轴对称平衡,图中上部丰干脸朝右,下部两人一虎朝向左侧,整个团块形成顺时针旋转的动态暗示,也没有三人一脸这种精巧的“立体派”的构图。从构图的精巧、稳定来看,元代传世《四睡图》造型——托普卡帕宫《四睡图》——朱见深《一团和气图》由集合成团到几何成团再到对称图案成团的构图演变,前后演化的逻辑关系和线索是清晰的。
图三十三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院藏 15世纪时传入大不里士的中国作品《四睡图》
但是这样几何成团的构图演化结果在寒山拾得图像发展史上的意义并不仅在形式与图像模式、更在于它是观念演化的产物,也就是将玄奥的禅义在转化为通俗的和合观念过程中以一种很强装饰感的圆团形式符号对于圆满、如意、利市寓意的直白的比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