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今儿咱不说那才子佳人的风月,也不表那沙场征战的豪迈,单聊一桩怪事——为何那荧幕上的《聊斋》故事,十有八九,都只唱了半出好戏?这戏台子还没凉,角儿就匆匆下了场,留我等看客捧着颗心,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殊不知,那被省去的后半段,才是蒲松龄老先生呕心沥血,点醒世人的金丹妙药!
就拿那妇孺皆知的《画皮》来说事。影视里头是怎么演的?无非是太原王生,路上捡了个天仙似的娘子,谁知是个青面獠鬼,描画人皮,专害性命。最后必有那法力高强的道士或是高僧出面,拂尘一挥,宝剑一斩,妖邪伏诛,王生或许还能被救活,与那原配妻子相拥而泣,幕布一拉,皆大欢喜。这戏,热闹是真热闹,吓人也真吓人,可看完咂摸咂摸嘴,除了点人鬼恋的猎奇和降妖除魔的爽利,还剩下啥?
您且稍安勿躁,听我细说。这影视剧拍的,不过是《画皮》这出戏的上半阙,是那“奇谭”的部分,吊足了您的胃口。而蒲老先生原本的故事,在那恶鬼被诛之后,尚有洋洋洒洒三分之一的情节,那才是“志异”的真髓,是冲着咱们心窝子来的警世恒言!
却说那日,道士收了那厉鬼,庭院血污遍地,王生已开膛破肚,死状凄惨。其妻陈氏,悲痛欲绝,只得哭求道士搭救。道士叹曰:“我法术尚浅,不能起死回生。指你一人,或能救你丈夫性命。”
陈氏忙问是何人。道士言:“市集之上,有一疯癫乞人,常睡于粪土之中。你且去求他,他若百般羞辱于你,你万万不可忤逆生气。” 列位,您听听,这高人指路,指的不是仙山老祖,却是个滚在粪堆里的疯乞丐!这蒲老爷子,笔锋一转,便把故事从神怪斗法,引向了人心试炼呐!
那陈氏救夫心切,真个寻到了那疯丐。只见其人邋遢不堪,鼻涕三尺,正冲着路人痴傻嬉笑。陈氏跪地哭求,那疯丐却睁着浑浊双眼,笑道:“美人儿,人人都可做你丈夫,救他作甚?” 陈氏羞愤,却记着道士之言,忍辱再求。疯丐愈发过分,竟用拐杖击打她,又吐了一口浓痰在手上,递到陈氏嘴边,喝道:“吃了它!”
哎哟,您说说,这是何等的折辱!莫说一妇人,便是七尺男儿,也未必能忍。那陈氏当时面色如土,胃里翻江倒海。可一想到丈夫开膛破肚的惨状,她把心一横,眼一闭,竟真个将那污秽之物强咽了下去!只觉得那痰块入喉,硬如棉絮,哽在胸间,上下不得,痛苦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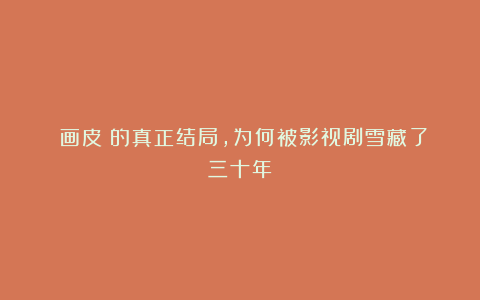
那疯丐见状,拍手大笑:“美人儿真爱煞我也!” 说完,竟起身扬长而去,再不回头。陈氏又羞又愧,回到家中,对着丈夫尸身,更是悲从中来。一边哭,一边想着方才所受屈辱,越想越恨,直欲呕出那心头块垒。正挣扎间,忽觉胸中那股硬物直冲而上,“哇”的一声,竟吐出一物来,不偏不倚,正落入王生被剖开的胸腔之中!
您猜那是何物?非是那口浓痰,竟是一颗勃勃跳动的人心!那心在王生腔子里滴溜溜转了几圈,旋即生出热气,渐渐与周遭血脉相连。不多时,那王生竟悠悠转醒,伤口也奇迹般愈合,只留下一道红痕,如红线缠绕。
故事到此,才算真正了结。看官们,您如今再品品,这后半段,才是蒲翁刀笔的真正力道所在!那前半段的画皮女鬼,不过是外邪,是外来的诱惑与灾祸,世人皆知该惧该防。可这后半段的“疯丐赐心”,才是直指人心的拷问!
那王生为何招此大祸?乃因他色迷心窍,不辨人妖,引狼入室。他是“心病”了,失了“人心”!所以,救他的不是道士的神通,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颗崭新的“人心”!这人心从何而来?来自其妻陈氏的“忍辱”与“舍己”!
蒲松龄老先生在文末掷地有声地叹道:“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 那画皮之鬼可怕吗?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中的那股淫邪之念,那股不识真心的愚昧!而最后救命的,并非外力,正是人间的至情至性,是妻子忍下天下至辱而换回的一颗赤诚之心!
影视剧为何不拍?因为这后半段不刺激,不香艳,甚至有些“恶心”,它需要静下心来品,需要刺痛自己去悟。它把一个简单的降妖故事,升华成了对人性、对婚姻、对忠贞的一场宏大隐喻。它告诉你,真正的妖魔不在窗外,而在你我的心窍之中;真正的救赎,也非天降神兵,而是身边那位你或许曾轻视、曾厌弃的糟糠之妻,她所能付出的,你无法想象的牺牲。
所以啊,列位,下次若再看那半部《聊斋》,您大可微微一笑,心道:“我已知那被剪去的真谛了。” 这,便是读原著的妙处,便是与三百年前那位淄川老秀才,隔空对话的滋味。
一段《画皮》真义,献与诸位品评。正是:
表面文章绘鬼狐,皮相易画骨难摹。
丹心须从污秽得,真谛总在幕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