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
20.2025
▽
▽
早晨送儿子去幼儿园。车上我跟他聊天,说到母婴室,他问我:“妈妈,那里是不是有个桌板可以放下来,你喂奶就躺在那上面?”我想了想说:“不是,那是给婴儿换纸尿裤的地方。”不过说来实在令我诧异。因为他只在很久以前进过母婴室,那么大点儿孩子,又过了这么久,里面的细节他居然还记得。于是我问他:“这些事,你会一直记得么?”他摇摇头,眼睛清澈见底:“不会。”答得极是坦然,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归途上,我想起自己六岁前的记忆,不过是几幅零星的画面。而且大部分都和留下的照片有关。新的经历像滂沱大雨纷纷落下,旧的回忆被深深掩埋,不留一丝痕迹。
小孩子尚不知记忆的可贵,也不知遗忘的可哀。他活在当下,像一株新发的嫩芽,只顾向上生长,哪管昨日雨露如何,前夕风霜几许。而我却已遗憾,人的一生,不过是记忆的载体。一边积攒,一边遗失,待到老时,所剩无几?
记得孩子未出生前,我曾独自去看海。那是个阴沉的下午,海边游人稀少。我坐在礁石上,看那海浪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起初觉得单调,继而却看出些意思。每一波浪花都不同,却又何其相似。它们涌上岸边,卷走几粒沙子,留下些许泡沫,旋即退去。新的浪花接踵而至,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永无止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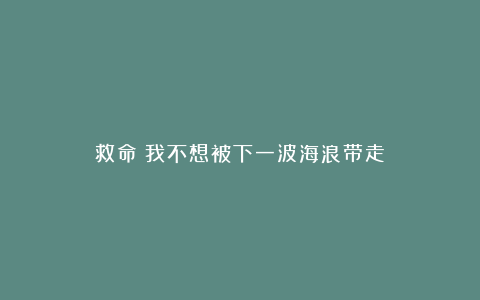
海边附近就是个小渔村,那天正巧有个渔民在村口补网。他手指粗大,动作却灵巧得很。网在他手中翻飞,破洞渐渐消失。我问他:“这网用了多少年了?“他头也不抬:“记不清了,总有二三十年罢。”我又问:“补过多少次?”他这才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数不清了。补了又破,破了又补,能用就行。”
他的话使我沉思。人生在世,不也是如此么?记忆如网,时间如海。我们不断修补着记忆之网,却总有些什么从破洞中漏掉,再也寻不回来。儿时的玩伴,青年的梦想,中年的壮志,一一消磨殆尽。到了老年,手中所持,不过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罢了。
那日我在海边坐了许久,直到暮色四合。海浪在黑暗中依然执着地拍打着岸边,声音沉闷而有力。我想,这海浪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究竟有何意义?转念又想,或许本无意义可言。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原因,正如海浪之所以为海浪,只因为它永不停歇地涌动。
那时归家路上,路灯次第亮起。行人匆匆,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他们的面孔在灯光下一闪而过,随即隐入黑暗。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忧愁。这些人,连同我自己,终将被时间之浪卷入遗忘的深渊。我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在宇宙的长河中,不过是瞬息即逝的泡沫罢了。
而今孩子出生已有四年,他的记忆之网才刚刚开始编织。他记得两三岁时的事,却不知能记到几时。而我,比他大二十几岁,记忆之网已不再崭新。有些往事清晰如昨,有些却模糊难辨,更有许多已然消失无踪。每念及此,便觉人生荒诞。我们如此珍视的记忆,竟如此脆弱不堪。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些已经遗忘的事。它们去了哪里?是彻底消失了,还是潜藏在意识的某个角落,再也无法唤回?如果记忆构成了“我”的本质,那么那些被遗忘的部分,是否意味着“我”已经部分地死去了?如此说来,人到老年,与年轻时的自己,岂非判若两人?
每天送孩子去幼儿园,他总在门前向我挥手告别,笑容灿烂,然后转身跑向同伴,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我站在原地,很多时候目送着他的远去,觉得释然,也觉得伤感。或许人生活得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因为记忆会消逝,此刻才显得珍贵;正因为生命有限,活着才值得珍惜。
遗忘之海终将吞噬一切,但在被吞噬之前,我们尚有时间可以坐在沙滩上,悠闲地看一会儿浪花。
最近的蝉鸣淡了许多,我也终于敢走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面,踩一踩斑驳的影子了。每一次我都走得很慢,想要记住这一刻的光景。虽然知道终将遗忘,但此刻的铭记,或许就是对遗忘最好的反抗。
人生如海,记忆如沙。或许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退潮前,多捡几枚美丽的贝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