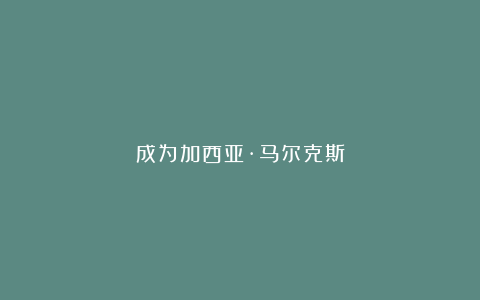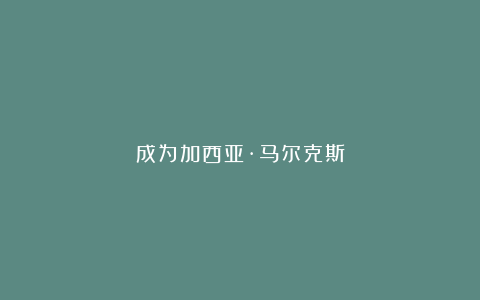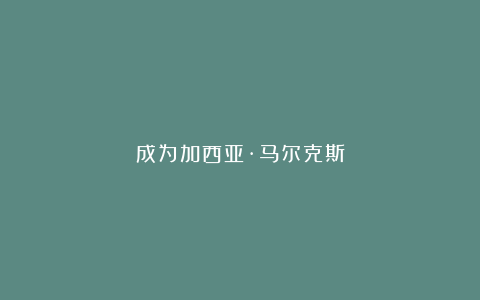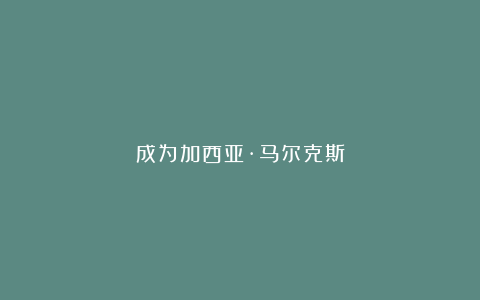
加夫列尔[也就是马尔克斯]八岁那年,外祖父一命归阴……他是跟着母亲来变卖外祖父那幢宅院的。往昔那个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彩色阳伞的车站,如今已然衰微破败,没有一个人影……一切都仿佛废墟,一派被遗弃的景象,一切都被炎热和遗忘吞没了。加夫列尔和他母亲一面胆战心惊地在破败的街道上走着,一面极力想从那幅潦倒的景象中辨认出对于往昔繁荣昌盛的遥远记忆。
母亲遇见的第一个女友……两个妇女彼此打量着,仿佛要透过各自疲惫衰老的外形,努力回忆起昔日少女时代美丽动人的容貌……两人于是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从那时,从那次相遇受到启迪而诞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这不仅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恐怕还要包括自此以后他的所有小说”。
这段年少时对时代沧桑的见证,并没有赋予马尔克斯“老成持重”的性格,反而激发了他对于时间结构超验性的感知,仿佛他由此觉察到人的个体存在与时间循环之间的支离。
换言之,他在彼时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深刻地意识到了一点,并非如西方工业文明所幻想的那样,时间只是被制造出来作为人类活动的指示器。
无论是在《百年孤独》之前还是之后,马尔克斯都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和话语表达着、回味着这种感觉,并结合着他成长后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背景,逐步构筑起那座巍峨的拉美文学殿宇。人们习惯以一种颇具政治性但又不失艺术味道的术语称呼他的写作,而唯有读过这本访谈录的读者,才会猛然觉察到其真正的内核。
这个术语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魔幻现实主义”,而这个所谓的内核便是他童年对时空以及人物变化的全部体验。
正如他在阐述《百年孤独》的创作初衷时说,我不过是“要为我童年时代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的文学归宿”。
在与门多萨谈起声誉时,马尔克斯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将自己结交的朋友根据《百年孤独》这部作品问世的时间为分界线分成了老友和新朋友,他也曾一度以为老朋友更值得信赖,而后来他才觉察到由于声誉而相识也算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情境。不过,在盛名与政治波澜之下,究竟马尔克斯与这些朋友有多么亲近,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有一点是可知的,那便是一切都会归于虚无的必然性。
有人因为这种必然性而陷入犬儒式的绝望,而马尔克斯则以坦诚的热情予以“近乎挥霍”式的拥抱。无论是与卡斯特罗,密特朗抑或是格雷厄姆·格林。当他发现自己写给朋友的信件被当作商品卖给大学档案馆时,他开始对文字保持警惕。然而,他依旧热衷于打电话,甚至会为了朋友的聚会而选择环球旅行(这里或许不包含他从略萨那收获黑圆圈的部分)。
这种浓烈到近乎浮夸的激情之下是波涛汹涌的孤独,因为被遗忘是注定的。正如他看待拉丁美洲的历史,同样“也是一系列代价高昂然而徒劳的奋斗的集合,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集合”。马尔克斯几乎是清晰地捕捉到了这种孤独的源头以及其宿命般的循环本质,这也构成了《百年孤独》显得荒诞却有在某个维度上极度真实的现实。
如果你读过《百年孤独》,一定也能意识到,这不仅体现在布恩迪亚家族成员名字的重复与性格的轮回上,同样显露整个马孔多小镇的命运轨迹。整个拉美社会如他童年见证的那般一样,从繁华到衰败,再一遍遍循环。《百年孤独》背后,是注定归于虚无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遗忘。从最初的开拓、繁荣(香蕉公司时期)、衰败到最终的彻底消亡,马孔多如同一个微缩的拉丁美洲,也正是马尔克斯曾见证的车站和街道,一切经历着从希望到幻灭的永恒循环。
正如马尔克斯在面对门多萨对于自己是否迷恋权力提问时的问答:
“毫无疑问,权力是人类雄心及意志的最高表现。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作家对于某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因素无动于衷”。
自命清高的人自然可以远离政治,但是唯有虚伪或愚蠢的作家才会无视政治在人类社会的巨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对权力的观察与政治的凝视是雕刻在马尔克斯这根“孤独-循环”的文学巨柱上充满超验意味的图腾。
正是这样的组合,使得马尔克斯以悲怆的力量撑起了《百年孤独》,乃至整个文学宇宙的叙事空间,使之超越地域限制,直抵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
这部经典的访谈中,马尔克斯所喜欢的读物与他的写作习惯必然也会是重要的关注点。而马尔克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的回答,实际上也暴露了评论者与作者之间永恒的矛盾和隔阂,双方往往都或多或少自诩最懂文本的人。
许多人会将马尔克斯的作品视为对福克纳的继承,而马尔克斯就算有一段时间把自己都说服了,可依旧忍不住会说自己的创作实际上是在努力“摧毁福克纳”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而除了马尔克斯自己,少有人觉察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他的影响。在访谈中,马尔克斯甚至说“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达洛维夫人》中的这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还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
除了他的阅读修养来源,读者必然也好奇他对于写作的看法。或许当读到他和许多作家一样,面对空白稿纸也会感到焦虑时,许多写作者会不由释然,毕竟如此热爱写作的大作家如此,你我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种焦虑了。不过相比于虚构本身,马尔克斯则更乐于将创作本质认定为现实,或许他更认可精神分析的逻辑,认定想象和梦境一样不过是粉饰,只是不一定是被压抑的欲望。
不过,他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在他看来“虚幻,或者说单纯的臆造,就像沃尔特·迪士尼的东西一样,不以现实为依据,最令人厌恶”。
马尔克斯对于书写现实的执念某种意义上似乎超越了作家本可能具有的对文本阐释的谨慎,在他看来,“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这跟梦境一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