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的发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元代高端瓷器风貌的窗口。在窖藏出土的 239 件瓷器中,19 件元青花已足够令人瞩目,而 4 件釉里红瓷器更以其稀少与精良,成为国内外馆藏中的珍品。
这四件釉里红瓷器 —— 釉里红线绘开光花鸟纹罐、釉里红芦雁纹匜、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高足杯、釉里红贴塑卷云折枝菊纹高足杯,与元青花、枢府釉瓷器等一同被精心安放于窖藏中心,完整的窖藏状态为我们探寻它们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一套完整的饮酒器:功能的默契配合
从器型与功能的适配性来看,这四件釉里红瓷器极有可能是一套协同使用的饮酒器物,各件器物的设计都暗合饮酒场景的需求。
釉里红线绘开光花鸟纹罐可以是这组器物中的 “储酒担当”。
其罐型规整,腹部饱满,具备良好的密封与储纳条件 —— 在元代,这类中型瓷罐常被用作酒器的 “基础容器”,用于盛放酿造好的酒液,为整套饮酒流程提供 “源头”。
而釉里红芦雁纹匜则承担着 “分酒” 的角色。这件匜为印坯成型,器身呈钵状,敞式芒口,有一槽形短流,流下贴有一卷云形系,平底略往上凸,涩胎,并无柄部,其器型设计本就带着实用巧思:槽形短流便于精准倾倒,手持器身或借助流下方的卷云形系辅助,即可平稳完成分酒动作。
宋代时匜已用于饮食场景,到了元代,它作为分酒器的功能更为明确 —— 从储酒罐中舀出酒后,倒入匜中,再由匜分注到杯中,既避免了直接倒酒的溢出,也让分酒过程更显有序。
最具巧思的是两件高足杯,它们皆是 “转杯”—— 杯身与高足可自由转动。
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高足杯为撇口,龙纹贴塑立体灵动;釉里红贴塑卷云折枝菊纹高足杯为直口,折枝菊纹疏朗雅致。这种 “可转动” 的设计并非无用:饮酒时,或许可通过转动杯身调整纹饰朝向,增添席间趣味;高足的造型也方便手持,契合元代宴饮时 “举足而饮” 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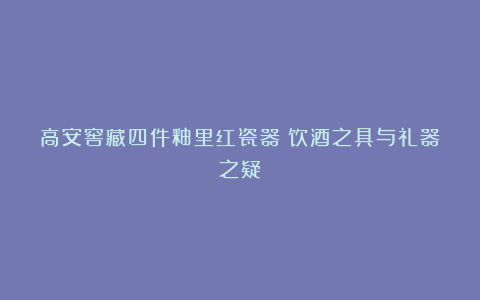
从 “储酒(罐)— 分酒(匜)— 饮酒(杯)” 的流程来看,四件器物功能环环相扣,显然是为了同一类场景设计,“饮酒套器” 的推测有着扎实的功能依据。
二、礼器的可能:儒家文化下的器物意涵
窖藏中与釉里红一同存放的元青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 这些釉里红瓷器或许还与 “礼” 有关。
在窖藏出土的 6 件青花梅瓶上,盖内壁与器底用墨书楷体写着 “礼、乐、书、数、射、御”—— 正是儒家 “六艺”。
这明确指向窖藏主人对儒家文化的推崇,甚至可能是身份与文化立场的表达。
而釉里红、元青花、枢府釉瓷器被一同放在窖藏中心,而非普通日用瓷的周边位置,足见它们在主人心中的 “特殊地位”—— 绝非普通日用品,更可能与 “郑重场合” 相关。
元代虽由蒙古族统治,但儒家文化仍深刻影响着社会上层。
祭祀、宴宾等礼仪场合中,器物的选择往往暗含 “礼” 的规范:釉里红瓷器烧制难度极大(铜红釉对窑温要求极高,稍有偏差便发色不佳),成品稀少而珍贵,用它作为礼仪场合的器物,本身就体现了对场合的重视;而若它与带有 “六艺” 墨书的青花梅瓶配合使用,或许是在通过器物传递 “礼” 的意涵 —— 比如祭祀时用罐储酒、用匜分酒、以杯敬祀,或是宴饮宾客时以成套珍品彰显礼仪。
当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如釉里红器物本身有礼仪相关铭文)证实这一点,但结合窖藏整体的文化氛围与器物的珍贵性,“礼器” 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它为这四件釉里红瓷器增添了更厚重的文化意涵。
高安窖藏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完整保存了这些器物的 “共存状态”—— 正是这种 “完整”,让我们得以跳出单件器物的局限,窥见元代人的生活与文化。
这四件釉里红瓷器,既是巧思满满的饮酒套器,见证着元代宴饮的雅致;又可能与儒家之 “礼” 相关,承载着器物背后的文化重量。它们在窖藏中沉睡数百年,如今在高安博物馆静静陈列,仍在向我们诉说着元代瓷器的精妙与那个时代的隐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