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米利·巴拉基列夫在1869年完成其钢琴曲《伊斯拉美》时,他不仅创作了一部日后被誉为“世界最难钢琴曲”的作品,也清晰地发出了“强力集团”的核心艺术宣言。以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居伊为核心的强力集团,其核心目标直指建立一种植根于俄罗斯民族音乐、区别于西欧主流的独特艺术音乐。
强力集团的诞生与发展,必须置于19世纪欧洲民族乐派崛起的宏大背景中。当时,从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代表的波希米亚乐派,到格里格代表的挪威民族之声,再到西班牙的阿尔贝尼兹和格拉纳多斯,欧洲音乐版图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民族化转向。这股浪潮是对德奥音乐长期主导地位的反叛,也是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追寻。强力集团正是这股汹涌浪潮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支俄罗斯力量。
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由安东·鲁宾斯坦创立)所推崇的德奥式学院派。安东·鲁宾斯坦主张俄罗斯音乐家应完全融入欧洲主流传统,成为其合格继承者。强力集团则针锋相对,他们将格林卡尊为精神导师。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开创性地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元素,为强力集团指明了方向:真正的俄罗斯音乐应立足于本土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独特的东正教圣咏传统、以及广袤国土上多民族的文化。
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是强力集团艺术理念的体现。这首作品基于作曲家1863年高加索之行采录的亚美尼亚和列兹金民间音乐素材。其严谨的三段式结构(ABA’):
A段(急板)以狂暴的节奏和复杂的技巧呈现高加索地区粗犷豪放的舞曲主题,极具冲击力。B段(如歌的行板)转入充满东方色彩的抒情旋律。A’段(更激烈的急板)舞曲主题以更为炫技和辉煌的模样再现,达到全曲高潮。这种“主题呈现 – 对比展开 – 主题升华”的结构模式,体现了强力集团的核心创作观:原生态的民族音乐素材,必须通过专业作曲技法,才能转化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
巴拉基列夫本人虽非音乐学院科班出身,却通过系统研究俄罗斯民歌集(如达戈尔梅日斯基的作品)和深入钻研西欧和声学(如凯鲁比尼的著作),掌握了将“野性”旋律纳入古典音乐结构的能力。尼古拉·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之弟)在1870年首演此曲,在场听众所感受到的,既是钢琴演奏技巧的展示,也是强力集团将东方文化元素整合进俄罗斯艺术音乐的探索。
强力集团的五位成员虽有共同的核心创作理念,但是其作品却呈现出丰富多元。
穆索尔斯基是五人中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他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堪称音乐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剧中,他大量运用俄国民间哭腔音调(普里奇卡尼耶)、平行和弦、以及非方整性节奏,创造出一种原始而震撼的音响效果。例如剧中圣愚在教堂台阶上的哀嚎,旋律来源于东正教圣咏和乡村哀歌,旋律不加修饰的“丑陋”感直接反映出沙皇统治下人民的深重苦难。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 中,《两个犹太人》一曲他运用沉重的低音区、增音程(尤其是三全音)和奇怪的节奏,深刻刻画了社会阶级的对立与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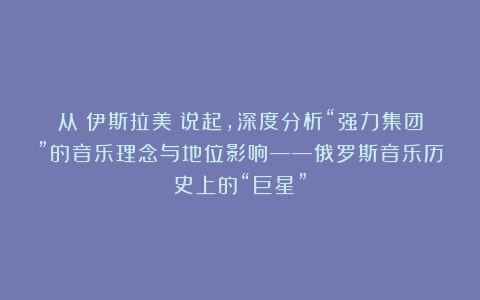
化学家出身的鲍罗丁,其音乐充满了对俄罗斯广袤疆域及其多民族的描绘。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是其代表作,乐曲开始,小提琴高音区持续泛音描绘出草原的空旷寂寥,随后由单簧管奏出悠扬的俄罗斯风格旋律,代表行进的俄罗斯军队或商队。接着,英国管奏出带有明显东方色彩(小调式、装饰音)的旋律,象征当地的土著民族。两个主题起初交替出现,最后在弦乐丰满的和声背景下融合,形成一首宏大的赋格。这展现的是优美的“异域风情”,也是沙俄帝国在亚洲腹地扩张及其所宣扬的“文明融合”的理念。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初是海军军官,后成为强力集团中作曲技术最精湛、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成员(他的学生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他的作品以极其绚烂华丽的管弦乐配器闻名。《西班牙随想曲》虽以西班牙民间舞曲的旋律和节奏为基础,却运用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带有浓厚斯拉夫气息的管弦乐技法(大量运用木管与铜管的亮丽音色、打击乐的丰富音色、以及独特的和声进行)对其进行塑造。其结果,就是这部作品包容了多种民族音乐,其既是西班牙的,又是俄罗斯的。
军事工程师出身的居伊,其创作成就相对其他成员稍逊一筹,但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家和评论家角色。他撰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音乐评论文章,在报刊上积极宣传强力集团的美学主张,抨击保守的学院派,是团体舆论的重要“笔杆子”。
当然,要全面理解强力集团的意义,必须将其与同时代另一位俄罗斯巨匠——柴可夫斯基进行对比。柴可夫斯基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接受过完整的西欧学院派作曲训练。尽管他也大量运用俄罗斯民间音乐素材(如《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1812序曲》),但其处理方式与强力集团截然不同。
柴可夫斯基倾向于将民歌素材个人化、抒情化,将其转换为更符合西欧浪漫主义审美标准的音乐中。例如《六月·船歌》旋律虽具俄罗斯气息,但其钢琴织体、情感表达、以及忧郁的气质,更接近于舒曼或肖邦的浪漫主义风格。在题材选择上,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强力集团的穆索尔斯基关注《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历史政治、《图画展览会》的市井百态;而柴可夫斯基则钟情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中的个人爱情悲剧、《悲怆交响曲》中深刻的个人精神。简言之,强力集团力图用音乐反映社会现实、塑造民族集体意识;柴可夫斯基则更专注于表达人类普遍情感、探索个体内心世界。前者向外,后者向内;前者强调民族集体性,后者侧重个人抒情性。
强力集团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成员大多非音乐学院科班出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后来成为教授是例外)。这种“业余”身份反而赋予了他们挑战当时德奥传统音乐的勇气。他们拒绝被既有的和声规则、对位法和形式束缚。穆索尔斯基大胆地使用不解决的不协和和弦(如《鲍里斯·戈杜诺夫》序幕中的钟声场景),制造出刺耳的音响效果,拒绝“粉饰”社会的裂痕与痛苦。鲍罗丁在其歌剧《伊戈尔王子》中,直接引入中世纪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旋律(如《鞑靼舞曲》),挑战了西欧音乐自定所谓“文明”的标准。巴拉基列夫指导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自学时,强调从分析格林卡、贝多芬、柏辽兹、李斯特等大师作品入手,而非因循守旧于教科书上的规则。
这些被当时保守乐评人诟病的“非专业”手法。他们反对的不仅是传统的音乐技法,更是西欧(尤其是德奥)音乐的霸权地位。他们主张俄罗斯音乐的发展道路必须独立自主,其根基应深植于俄罗斯本土的语言、民间音乐调式、东正教圣咏传统,以及帝国境内多民族的音乐瑰宝之中,而不是对意大利对位法或德国功能和声体系的直觉模仿。
强力集团的活动高峰期集中在19世纪60-70年代,但其影响深远绵长。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作为重要的后继者,在其恢弘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中,展现了强力集团传统与柴可夫斯基传统的深刻融合。
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深沉、凝重,旋律带有鲜明的俄罗斯民间圣咏特征,低音区充满穆索尔斯基式的阴郁力量,这是强力集团血脉的延续。而副部主题则迸发出宽广、抒情、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旋律洪流,其气息之长、情感之深,无疑是柴可夫斯基抒情传统的继承。
回望百年,《伊斯拉美》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演奏难度,恰似强力集团的历史地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独立音乐创作,永远需要高超的技巧(对音乐的掌握)与非凡的勇气(挑战权威、坚持自我)。他们从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和帝国边疆的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将异域的旋律(高加索、中亚、西班牙)巧妙地融入自身创作中,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音乐的文化想象空间。
强力集团以其独特的道路,为俄罗斯音乐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民族乐派乃至现代音乐的发展,其遗产早已融入世界音乐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俄罗斯民族乐派艺术殿堂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