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晚清是中国戏剧发生巨变的关键阶段,最直接最重要的一项因素即是西戏的到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格局。19世纪下半叶,我国的一些港口城市出现了西戏演出,如汉口、天津、上海等。[1]其中,上海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租界开放的演剧政策,西戏开演时间早,演出次数频繁,是首当其冲受西戏影响最大的城市。在此背景下,上海各种戏剧的现代化转型表现也最为明显,成为中国戏剧现代转型的一个窗口。故本文选取上海租界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的史料,以说明西戏东渐对中国戏剧产生的影响。这段历史一直潜藏在晚清戏剧史的最深处和最底层,暗流涌动,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关于晚清文化更多的是“西学东渐”“西风东渐”“西潮东渐”之说,少有人提及“西戏东渐”,虽是一字之差,却关系着晚清戏剧发展进程的真相。
随着晚清通商口岸的开辟,西戏自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华上演,开启其东渐之旅,如学界所注意到西人业余剧团1850年在上海新开业的新皇家剧团上演《势均力敌》《梁上君子》等剧目。[2]西戏有时也被称为“洋戏”,如《清稗类钞》中所说:“西伶之来华演戏也,道光朝已有之,当时呼为洋戏。”[3]中西戏剧并存构成晚清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戏剧生态,这既是中国戏剧转型的文化背景,也是催生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因素之一,但人们往往将西戏与中国戏剧的生存空间割裂来看,认为西戏多在固定场所演出,很少有中国人去看。如徐半梅称上海西人业余剧团和兰心剧院所演的外国戏剧“对于中国一般的民众并不发生关系,所以在中国剧运上,帮助是很少很少的”[4]。徐氏出生于1880年,只是就个人所见而言,并未对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情况做具体调查与深入研究,但他的观点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很多学者都沿用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开端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演剧。如黄爱华说:“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戏剧理念的冲击影响下,中国戏剧固有的发展进程发生裂变,并在艰难的蜕变和转型中开始其现代性进程……正是学生演剧,迈出了中国戏剧现代性求索的第一步。”[5]这一观点无形中忽视了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戏剧的裂变与艺人的探索,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开端推后了40多年。既然中国戏剧的现代性是伴随着接受西方戏剧开始,其开端无疑是50年代即开始的西戏东渐,正是在中西戏剧的交互碰撞中,中国戏剧艺人在上海这一大舞台上推动了中国戏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一 晚清“西戏”之名与实
西戏东渐及其影响被学界忽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理解的西方戏剧局限于“演剧”,远远小于晚清人语境中“西戏”的内涵。在晚清语境中,“西戏”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各种西方戏剧,也包括西方马戏、魔术、杂技、幻灯和电光影戏等演出。
“西戏”一词并非杜撰,确实存在于晚清国人的语汇里,频繁地出现在《申报》等报刊以及晚清人笔记中,他们并非奔赴国外的出使人员,只是国内关注戏剧者。从中可见,在当时语境中,西戏包括的范围很广,有时指英人轻歌剧,如《记观西戏》中描述在上海英国戏园看的一出戏[6],“其上出则三男三女,颇似中国说书模样,苐说书者时坐时起,此演戏者时出时入,不甚相同”,“时说时唱”;[7]有时指意大利歌剧,如《西戏来沪》中记载“上海新到意大利国戏班,善于清唱,此西戏来华以来之第一体面戏班也”[8];有时也指西人所演马戏、杂技等,如《续记西戏》中记载“飞马钻圈”等表演[9];也指西人所演影戏、活画戏、傀儡戏等,如《观大克傀儡戏记》中说“西戏之来沪上者有马戏、兽戏、变幻之戏、歌唱之戏,而于傀儡戏则不恒见也”[10]。可见,在晚清语境中,“西戏”泛指西人所演的各种西方“戏”和“剧”,其范畴比人们所理解的“戏剧”要广泛得多,当前我们并不把马戏、魔术、杂技等列入“戏剧史”,而是放在“杂技史”。晚清时西方人的戏剧概念也很宽泛,孙柏曾指出晚清时西方国家“杂技、魔术、马戏、歌舞,与作为叙事艺术的演剧,实属同类,并无二致”[11],“西方的这一戏剧文化格局,几乎无异于中国的百戏杂剧”[12]。晚清时西方戏剧即是以百戏并存的形态,出现在上海租界的娱乐空间中,与中国戏剧发生多元关系。
晚清人对西戏也有进一步分类,一种是按照中国戏剧传统将其分为文戏和武戏两大类。如静观老人说:“观正月三十日贵报’记观西戏’一则,而忆余于上海亦曾观西戏焉,同为西戏而大不同,以君所观者乃西国之文戏也,余所观者乃西国之武戏也。”[13]他所说的“文戏”是一场以表演故事情节为主,时说时唱,没有激烈打斗的戏;“武戏”则是四出马戏及杂技表演。另有人将西戏分为两大类,“一演各种故事,一演各种幻术”[14]。大致而言,西方“文戏”约是我们当前所说的以演故事为主的“戏剧”,“武戏”约指马戏、魔术、杂技等各类表演。但西戏在表演时并无严格规定,往往会混杂在一起演出,如《西戏开演》中说:“爱理生西戏班定于本月十五晚九点钟在张叔和花园内大开演,俾华人观看,班中有最大爱弟森留声机器,及泰西文武男女各戏。”[15]无论文武,在晚清人眼里都是“西戏”,是与中国戏剧相提并论的娱乐方式,而且是更加新颖有趣的娱乐方式。
由此,西戏在晚清人记忆中非常清晰,总是让他们大书特书。通过西戏,他们看到另一种奇异和精彩,如静观老人说:“此皆中国未有之奇也,不可以不记”[16]。晚清人认为可以借西戏开拓眼界,广博见闻,虽然语言不通,但并不影响他们对西戏开放的接受态度。如1876年一位观众说:“余既不谙其语,且立于看台最高且远之处,目力不佳,望去亦甚模糊,但觉西人观者拍手顿足,互相笑乐,当必有可取者矣,苐虽不辨其语不明其事,而西国讯案情形历历如绘,欲广见博闻者,亦须一观,幸勿以言语不通,竟裹足不往也。”[17]尽管看不懂内容,也甚觉值得一看。哪怕是对于高雅难懂的意大利歌剧,他们也认为:“中国人有喜听新声者,曷往观诸。”[18]报刊上的文案撰写者或许并不是单纯的观众,很有可能是受聘于西人的报刊主笔,就更使得西戏成为晚清文化和娱乐空间中具有独特意味的一道风景。
二 晚清西戏在上海的演出
和传播特点
西戏与中国戏剧并存于晚清上海的娱乐空间,通过多种渠道进入晚清人的视野与生活中,不能将其孤立、割裂来看。文化生态学主张“将文化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视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观察其交互规律”[19],还原西戏东渐在上海形成的文化生态,有助于了解晚清中西戏剧在交流互动中的发展历程。
1.西戏演出具有持续性
晚清西戏来华始自道光年间,其在上海的演出不是少量的、偶发的,而是持续性的。西戏中的“文戏”,目前所知较早的演出是1850年12月14日,西人业余剧团在新开业的新皇家剧团上演了有趣的小喜剧《势均力敌》(Petite Comedie of Diamond Cut Diamond),以及大型歌舞滑稽表演《梁上君子》(An Operatic Burlesque Extravaganza the Roofscrambler)等。[20]孤立地看这一演剧事件,对中国观众及戏剧产生的影响确实很小,但它却是晚清西戏东渐的起点,其背后隐藏着一股源源不断的潮流,对上海戏剧带来多种影响。
深入考察每一个在华西人剧团和每一座西人戏院,其演出都具有一定持续性。上海租界内曾经有过业余滑稽剧团(Amateur Burlesque Company)、上海浪子剧团(Shanghai Mounted Rangers Amateur)、业余戏剧社(Amateur Dramatic Corps)、音乐滑稽戏剧团(The Concert and Burlesque troupe),等等。其中上海爱美剧团(Shanghai Amateur Dramatic Corps, 简称A.D.C)演出时间最长,其演出始于1851年,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专场演出较少,从70年代开始,每年都有数十场专场演出,至1878年12月演至第60场[21],1888年3月演至第91场[22],1900年2月演至第119场[23],1911年12月演至第162场[24]。徐半梅说“它有四五十次的演出历史”[25],颇不合理。而且,西人剧团演出并非只给西人看,相反,他们很希望有更多中国观众到场,如1875年6月9日《申报》刊载:“西商于月之初七日在本埠大桥垝外国戏院内串演诸戏,并邀请各华人赴阅。”[26]同日还刊登《西商串戏》告白:“在大桥之戏院内复将前演之戏名《可克士及波克士》者而再演也,并有小戏一出名《一杯茶》。”[27]从《字林西报》可知,《可克士及波克士》即A.D.C在兰心剧院演出的英国轻歌剧《同居一室》(Cox and Box)[28],该剧是约翰·麦迪逊·莫顿(John Maddison Morton)创作于1847年的闹剧,1867年被改为音乐剧[29],上海西人所演应是这种新形式,同时还演出了独幕喜剧《一杯茶》(A Cup of Tea)。观众中十有八九是西人,十有一二是华人[30],可见自19世纪70年代就有华人观看西方戏剧。
西戏中的“武戏”在晚清开演时间也很早,观众较“文戏”更多,产生影响也更大。道光年间钱塘陈芰裳曾作《洋戏行》,描述“凹睛凸鼻皆殊形”的西人男女和儿童表演精彩的马戏、歌舞、杂技等节目。[31]19世纪60年代之后,较大规模的马戏团不断来中国演出,而且总获得轰动效应,如1868年大世界马戏团(The Great World Circus)来上海,有观众称“这是在上海看到的最精彩的事”[32],帐篷内人群拥挤,以至于一些人不得不站着。[33]有学者指出从《上海新报》刊登的一些外国戏广告中可以看出,在60年代之后外国戏已经开始深入上海公共生活之中,而且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笔者据《字林西报》统计,1870年、1872年、1874年、1875年、1877年、1878年都曾有较大规模的专业马戏团到上海演出;19世纪80年代,则每年都有较大规模的专业马戏团到上海演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车尔利尼马戏团。无论文武西戏,观众往往中西皆有,如《西人演戏》中说:“本埠各西人每逢英历十八号在西国戏馆开演诸剧,以作行乐之举……往观者则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34]上海观众生活在西戏连续上演的文化空间中,上海戏剧也在西戏持续上演的娱乐市场中求生存、谋发展。
2.西戏具有多重传播渠道
作为舞台表演艺术,西戏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舞台演出,在上海的演出空间,首先是西人剧院,晚清人习惯将其称为外国戏园。如《清稗类钞选》中说:“上海有外国戏园,华人亦有往观者。而西人演戏,于唱歌跳舞甚为注意,且男演男戏,女演女戏。如公共租界圆明园路之兰佃姆,南京路之谋得利是也。礼查路之礼查客寓,亦有戏场。”[35]外国戏园对所演何剧并不限定,同时也对中国人开放,只不过因票价高昂华人所到甚少。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曾出现过的外国戏园有皇家剧院(Imperial Theatre)、上海业余剧社剧院(Theatre of the Shanghai Amateur Corps)、上海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康科迪亚(The German Club Concordia,也称四马路弹子房)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兰心大戏院(常被称为圆明园路外国戏园),兰心并不只演出西方“文戏”,也曾演出多场专业的魔术、戏法、活画戏等西方“武戏”。有时所演魔术也具有一定故事情节,如1877年9月19日《申报》刊载的《外国戏园告白》(Lyceum Theatre)中说:“一、众客可偕克勒Kellar在蓬莱仙境盘桓一点钟之久,演毕暂歇十分时;二、神鬼希奇之会为克勒Kellar所演,而玲绿Ling Look助演;三、雅马提法Yamadera演蛇人之奇事,演毕再暂停十分时;四、幽冥之夜宴,为斯希奇人玲绿Ling Look所演”[36],可见这场演出不仅具有故事性,还具有一定互动性。
其次,是中国戏园。人们一般认为西戏在西人戏院上演,但实际上西戏经常在中国戏园上演。一种情况是中国戏园要借西戏谋生,如上海颇为著名的丹桂茶园1874年因亏损闭歇而改演西戏,告白中说:“特请英国戏院演术之瓦讷术师演戏,并演戏法、影戏各套,极其巧妙,变化无穷。”[37]1875年因遭遇国丧,中国戏园遵制不能演中国戏剧,丹桂茶园和金桂轩茶园无奈之中都改演西方马戏、影戏。西戏就是以此种方式闯入上海观众的娱乐生活中,激起中国观众的好奇心。一位观众说:“西戏本不奇,以西戏而演于中国戏园则奇。”[38]另一种情况是西戏为吸引更多中国观众,在中西戏园轮流开演,如瓦讷就是先在英国戏园开演,再到丹桂茶园上演;[39]再如欧洲戏士夏思美夫妇先在圆明园路戏园开演,再转到宝善街三雅园演出,然后再移至圆明园路戏园演出[40],从1883年4月演至5月,前后共30多天,几乎场场都爆满。1887年西人卫珀也是先在兰心大戏院演出,然后到丹桂茶园演出,“恐西戏馆中多欧洲士女,华人或不便杂居,因假座丹桂园”[41]。同样的西戏,在西戏馆里头等座位需洋3元,中国戏园只需洋1元,华人当然更乐意在中国戏园看外国戏。
然后,是临时搭建的中西公共戏园。马戏因为规模较大,往往需要临时搭建戏棚,此类戏棚还可以搬迁。为了争取更多观众,马戏班也会分别在西人聚集区和华人区搭建戏棚演出,如1874年意大利气亚里尼马戏班先在上海虹口顺泰码头演出,月余之后移至四马路处继续开演,目的即是“以便华人就近以观”,而且“将各价减半”[42],可见西戏具有流动性,并不限于在西人或中国戏园演出。马戏搬迁本身就是活广告,如1874年意大利马戏班在租界游行,“行道之人无不赞叹,有儿童未经见者,俱为之拍手狂叫,斯亦一盛会也”[43],引起街上的拥堵和轰动。
同时,西戏演出具有多元主体,一是在华西人组成的业余剧团,二是来华演出的专业艺人及专业剧团。另外,还有租界内各种教会团体,以及各级西式学校的师生们。各级学校的表演很像当前学校的文艺展演,热衷于表演的不仅是中学,一些西式小学在师长的组织下也进行公开表演。如1888年上海共济会小学、西童公学小学等都在兰心大戏院表演《美女与野兽》,受到观众欢迎。[44]西戏东渐在商业性质的演出空间外,还有一些非商业性的演出空间,如教会舞台、亚洲文会大厅等,这些演出往往也会对外开放,吸引更多观众前来。
此外,报刊、书籍等也是西戏重要的传播渠道,与舞台传播共同推动西戏东渐的潮流。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45],很多晚清人就是借报纸、书刊等媒介得知西戏演出盛况,并将其摘录在笔记中。即使现在,我们也是凭借晚清报刊、书籍等得知在华西戏的状况,勾勒西戏东渐的轨迹。
3.西戏具有前卫性、时尚性和经典性
西方各种戏剧、马戏、魔术、影戏、活画戏、傀儡戏等纷纭而至,构成晚清西戏东渐的大潮。来上海演出的西戏往往携带世界最新的技术。如丹桂开演的影戏,“该戏班奇巧万状,莫可名言,不特中国人未经见及,即在欧洲等处之人亦难得见之也”[46]。兰心开演的戏班则称自己“供奉各国皇帝”,“为各地方之新报及众人无不称为现活之戏士中最有名者”。[47]出于宣传目的,他们可能会夸耀自己的独特和神奇,但想要在上海娱乐市场站住脚,必定要有新奇技艺才行。
以演故事为主的西方“文戏”,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国家保持同步,演出颇为流行的新剧,展现出西方的时代风尚。如1863年3月上海业余滑稽剧团演出的滑稽戏《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是创作于1862年的新剧;《静水深流》(Still Waters Run Deep)是汤姆·泰勒和查尔斯·里德创作于1855年的家庭剧[48];1865年兰心大戏院上演多次并受观众欢迎的《混血儿》(The Octoroon)[49]是维多利亚时代剧作家戴恩·鲍西考尔特创作于1859年的新剧。[50]
另外,还有被反复演出的经典剧作,如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曾被不同剧团演绎过的莎士比亚经典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皆大欢喜》《小题大做》《仲夏夜之梦》等。[51]还有一些虽不能与莎剧相比,但也很具生命力的剧作,如兰心大戏院于19世纪80年代上演的滑稽戏《阿里巴巴》(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A.D.C.),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笔者按:有Signor Cagli’s Opera Company、Italian Opera Company两个剧团演出),《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the Masonic School);19世纪90年代上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DallasMusgrave Co.),舞剧《灰姑娘》(Cinderella,A.D.C.)等,其中《汤姆叔叔的小屋》《茶花女》等也在20多年后被春阳社、春柳社改编并演出。
4.西戏与中国观众具有一定疏离性
不可否认,中国观众与西戏之间具有一定疏离性,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以上海而论,虽然租界内华洋杂处,但有的区属西人居住,有的区属华人居住,戏园亦有外国与中国之分。为了争取观众并赢得利润,西戏往往轮流演出,努力打破空间上的疏离。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上。中国观众虽然欢迎西戏,但西戏使用的西语让他们产生明显的疏离感。华人在观看西戏后曾多次表示语言不通带来的隔阂,道光年间的陈芰裳就在诗中说:“方言蛮舌争玲珑。彼都士女笑且聆,我辈但能以目听。”[52]1869年来上海演出的美国侏儒“汤姆·拇指将军四人团”(General Tom Thumb miniature quartette),曾将一些特殊细节通过在大牌子上写汉字来解释。[53]1875年,一位观众看西戏后,建议公会董事“将所演戏名情节译成华字”[54],使华人明白戏剧内容。另一位观众观看西人马戏时也感觉到“西人观者均有西字戏单,华人得之亦不能悉”[55],建议增加翻译。19世纪80年代,西人注意到语言问题,一些西戏增加了翻译,1883年夏思美夫妇在上海演出时专设一人传话,使中国观众更乐于去观看,观众认为“最妙在有人传话,其戏中情节一一皆可心领神会,虽不解西语者亦得以深知其戏之妙处”[56]。翻译在演出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位观者记下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互动问答的情形,使演出别有一番趣味。[57]1886年,安特生在丹桂茶园的西戏表演也增加了翻译(按:当时称为“舌人”)。但增加翻译的多为西戏中的“武戏”魔术、杂技一类,在西人剧院上演的话剧,则少见增加翻译之说。这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西戏在近代前期对中国戏剧产生影响小的一个主要原因,西戏毕竟是用西语演出,与华人多有疏离,但很多华人确实从多种途径观看、接触或听闻过西戏之名。
晚清西戏东渐是娱乐市场全球化的一部分,其潮流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日本等东方国家和地区。许多来中国演出的西人剧团往往进行巡演,一种路线是从香港到上海,如1891年演莎剧的米恩剧团[58];或者是从日本到中国,如“汤姆·拇指将军四人团”从日本到上海演出[59]。另一种路线是先到中国演出,结束后再到日本,演出莎剧的美国珍妮特·华道夫小姐剧团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到日本演出[60],如演魔术的夏思美夫妇在上海演完之后乘船到日本演出[61]。无形中,上海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舞台,中国戏剧就是站在这个世界性的舞台上与各种西戏竞演。
三 晚清西戏对中国戏剧的
影响与冲击
上海租界堪称为中西戏剧文化“接触地带”的典型,在这一异质文化的“接触地带”内,文化交往持续发生。[62]《洋场竹枝词》描述上海戏馆的景象:“湖北京徽与粤东,两洋戏术复无穷。”[63]可见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内,地方剧种与各种西洋、东洋戏术争奇斗胜,共存于娱乐市场中,从而形成多元关系。
1.中西戏剧具有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
上海租界自1853年就开始了华洋杂居的模式[64],在这一地理空间内,中西戏剧、文化之间直接相遇,发生实质性的交往和互动。中西戏剧作为文化交流的方式往往会同场演出。如1873年英国领事在上海四马路弹子房“传唤中西梨园演唱中西戏出,在沪之西国官商莫不前往”[65]。在天津等通商城市,中西人士共同欣赏中西戏出的场面也常会出现。如《津门琐缀》中记载寓居天津之西人,“在总汇演剧辞年……中西人士履舄交错,固一时佳会也”[66]。
19世纪70年代,上海戏园开始出现中西戏剧同场演出。先是洋人正凤1874年延请丹桂茶园剧班,在外国戏园与西班会演,被称为“实创行之事也”[67]。中西合演的模式对观众具有相当吸引力,19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些中国戏园的常规。如《观剧小记》中记载西妇阁蜡在丹桂演剧,“园例每晚必先演京昆戏四五折,然后西剧登场”[68]。中西戏剧同演的形式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从相关广告上可以看到小子和、小连生、七盏灯、夏月润、林步青、李春来等艺人都有过合串外国戏的演出经历。同台合演使中西戏剧频繁接触、互动交流,有的艺人自幼在中西戏剧同台共演的环境中成长。如1889年丹桂中西戏合演,西国女郎表演水戏、表戏、巾戏、帽戏、盒戏、电戏等,年仅12岁的夏月润助演,“招之上台,以刀割巾者为雏伶夏月润,年甫十二,对之放枪两响,屹立不惧,亦一异也”[69],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中西戏剧在娱乐市场上具有竞争关系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戏剧具有交流互动关系,但从中国艺人和市场规律来看,中西戏剧之间则直接存在着一种激烈竞争关系。戏园是晚清人最为重要的休闲娱乐之地,戏剧市场的繁荣推动了城市的文娱产业。“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70]的上海,往往是西人来中国捞金的首选城市,看准商机并赢取利润是各种西人戏班不远万里来中国献艺的主要目的,无论是西戏中的“文戏”还是“武戏”,都要极力争取观众,赢得票房才能盈利。
租界内广大的中国观众是中西戏剧共同争取和吸引的对象[71],在同一娱乐时间段内,观众如果选择去看中国戏剧,就不能再分身去看西戏。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竞争和促销手段,如1872年5月29日《申报》上的一则马戏广告《外国男女马戏赠物》说“能于马上变幻百出,跳跃飞腾,并有多方奇巧”[72],仅标题就隐藏着诸种具有诱惑力的看点,外国马戏本就新奇,男女同演是当时中国戏剧所无,何况还赠送奇巧之物等。这只是一则普通广告,还有更多别出心裁的西戏广告,宣传力度更强。如车利尼马戏团来华演出,以精彩图片为广告开端(图1—图5),几乎占去《申报》广告版面的二分之一,中国戏剧被挤在版面的另一半。1882年6月至8月,短短2个多月,中英文报刊刊发该马戏团相关消息近百则,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消息,其中《申报》近60则,包括“马戏初志”再志、二志、三志、四志、五志等系列评论,还有《斗虎奇观》《荷人训狮》《象戏喜志》等特写,以及《兽戏推原论》《马戏不创于西人说》等论述文章。从中可以窥见中西戏之间的争端,如文中说:“咸以为得未曾有神而异之者,以为此戏固西人所独创,华人未有能望其项背者也,不知此戏中国向亦有之,特今则失其传耳。”[73]各种舆论将车利尼马戏推向大众娱乐的热点,“第一次中西人往观者甚众,约计有三千人”[74],后来演虎戏时观众则升至4000人[75]。获得成功带来的暴利之后,车利尼马戏团又在1886年、1887年等年份,以更大的阵势来中国演出多次。
图1 《申报》1882年6月10日广告插图
图2 《申报》1882年6月12日广告插图
图3 《申报》1882年6月14日广告插图
图4 《申报》1882年6月25日广告插图
图5 《申报》1882年7月5日广告插图
晚清观众将西方马戏视为“武戏”,无意中就会将中西武戏进行比较。如《马戏初志》描述车利尼马戏各种精彩表演时说:“四男一女,五人上台翻扑跳掷,各呈其艺,其觔斗花样翻新,异常出色,较之中国戏园不啻十倍。”[76]《再志西戏》中说:“四男一女共演之剧,有三人能踏肩层累而上,实为中国武生、武旦及跳虫等所不能及。”[77]明显要碾压中国戏剧,中西武戏之间的较量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票房竞争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实际上,在多种西戏评论中往往与中国戏剧相比较,而且认为西戏胜过中戏。如《西戏可观》中说:“新法奇技层见叠出,妙绝一时,以视华戏之鱼龙曼衍、金鼓喧天者,殊觉别开生面,有好奇者盍往观乎。”[78]可见,中西戏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所争夺的目标就是大量的中国观众和市场份额。
3.西戏对中国戏剧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晚清时西方商品倾销到中国,对本土商品带来冲击。各种西戏强势来袭对中国戏剧及娱乐市场也带来一定冲击,上海表现最为明显。但晚清人缺少危机意识,再加上政府对戏剧向来有各种打压,人们对租界的宽松制度还颇为赞赏。如《论禁戏》中说:“自通商之后,凡西商租界皆许伶人设馆演戏卖钱,始则创于香港,继则及于上海,后则至于镇江,今则又闻宁波亦有戏馆之设。盖缘西人以观剧为至乐,故西官推己及人,于此事不设厉禁焉。”[79]租界为中国戏剧提供了新发展空间,纷纭而至的西戏也直接给中国戏剧带来挑战。
中西戏剧竞相生存,西戏有着诸多优势,西人以马戏、魔术、兽戏等惊险奇异的技艺,声、光、电等先进技术,男女同演的开放态度,以及各种灵活的促销手段,在租界娱乐市场以颇为强势的姿态出场。而且,双方的竞争并不公平,西戏在一定程度上受“特殊政策”保护,能优先上演,中国戏剧则不能逃避官府的压制。如1875年连续遭遇两次国丧,中国戏剧停演数月,西戏却照常演出,乘虚而入,占尽商机。从《字林西报》上可以看到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常上演,1875年3月第二次上演《法定继承人》(Heir at Law)获得观众欢迎[80],自日本而来的法国马戏经过交涉也可以正常上演[81],并受到观众追捧。主演京剧的丹桂茶园只能改演英国影戏,消息中说:“窃思本埠自开正以来,各戏馆俱遵国制全行闭歇,在伶人固抱向隅之叹,而游客亦觉兴味萧然,今得外国戏前来,吾知击鼓三通,人皆仰首而望矣,其生意或得繁盛乎。”[82]另一主演京剧的金桂轩则改演法国影戏。[83]原来到戏园看中国戏的老顾客,此时只能到戏园看外国戏,一位观众还在《观演影戏记》中记录了在丹桂看到的奇妙影戏。[84]西戏借“特殊政策”更为广泛地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占领了娱乐市场更多的份额。恢复正常演出后,西戏因为受到观众欢迎,不但没有退出中国戏园,反而成为中国戏园颇有分量的节目,甚至成为戏园之间竞争和招徕观众的一种手段。在娱乐市场上,本来就有剧种之间与戏园之间的竞争,西戏的加入将本属于国内级别的“赛事”,直接升级为世界级。
四 西戏冲击下中国戏剧的
现代化突围
从“国赛”到“世赛”,晚清前期已经进入中国戏剧史上竞争最为激烈最为残酷的阶段,而上海作为中西戏直接交锋的第一赛场,用刀光剑影、火星四溅形容其舞台并不夸张。西戏虽有一定优势,但并非每一个来华演出的西人戏班都能赚到钱,如“意大利皇家歌剧院”1881年在上海兰心演出,正厅不过50人左右[85];西人马戏票房较好,但风险大,时有人员折损,如1874年意大利马戏班在中国卒一女伶和男伶[86],1882年车利尼马戏班一位演员被虎伤眼等[87]。中国戏剧与各种西戏同在一座城市的娱乐空间之内上演,同在一份报纸上的一张广告版面宣传,竞争的不仅是“胜负”二字,而是关系戏班和艺人的生死存亡。就是在这样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中国艺人集体奋力拼搏,勇于创新,在实践中将中国戏剧推上现代化的道路。他们的努力或许不被学术界在理论上认定为具有现代性,但他们却推动中国戏剧在舞台上、在市场竞争中与时俱进,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碰撞中,尝试种种通往现代化的路径,使中国戏剧绽放出异样光彩。这一过程并非温和平静,而是在“内忧外患”中(笔者按:“内忧”指国内剧种之间竞争,“外患”指与国外戏剧竞争),伴随着西戏的冲击和激烈竞争,由此,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初始期就具有突围的意味。
一方面,是武艺上的猛打猛拼。在西戏东渐风气中,上海观众19世纪70年代就形成追奇猎异、喜好惊险刺激的审美趣味,不新不奇不足以博得观众眼球。平心居士曾说:“戏馆如丹桂园、金桂轩、三雅园、天仙园、富春园之类,忽而勇夫血战,忽而美女艳歌,忽而孤孽悲哀,忽而滑稽嬉笑,愈演愈奇,愈奇愈新。”[88]娱乐风尚迅速变换,没有最新,只有更新,观众是真正的上帝和衣食父母,不能吸引观众则意味着戏园倒闭失业。中国艺人本能的办法是苦练武功,提高自身本领,追随娱乐市场潮流,以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京班有名的武旦和武生们个个身怀绝技:“如杨月楼之神采奕奕,艺容双绝,韩桂喜之飞舞跳跃,尽态极妍”[89],武旦黑儿则“身轻于燕,腰细犹蜂,跳踯则如猱升木,迅疾则如隼腾空”[90],精彩的身手堪比西人在马戏中的表演。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何19世纪80年代上海风行“三上吊”“空中飞”“云里飞”“云中漂”等高难度技巧和惊险动作的戏剧表演,因为他们不仅要和自己的中国同行竞争,还要和西戏,尤其是西戏中的“武戏”竞争。
另一方面,是奇巧变幻的技术创新。上海三雅园的灯戏频频翻新,如“新軿灯戏牡丹亭”全本,“各式楼台亭阁,倒彩变出花园景致……卸开另变一景,异奇精巧”[91];再如“灯彩新軿银河配”,“瑶台变化八仙下凡,全彩广寒宫……变化仙桥织女相会,异奇各式花样”。[92]仅相距一周,剧目和灯彩就更换了新鲜花样,反复强调奇异精巧、奇妙变化。但昆曲的竞争对象不仅是京班,还有时下流行的各种西戏,尤其是面对多次来演出的魔术、影戏等奇幻之戏,实在难以支持。1882年三雅园关闭,1883年改演西戏大受观众欢迎,消息中说“是晚之戏格外奇巧,竭尽所长,另用电灯幻出各样字画,翻新比奇,异样精彩”[93],戏剧市场就是如此无情。虽然晚清前期中西戏剧相竞的主要舞台在上海,但因戏剧和艺人具有流动性,其风尚也影响到苏州、天津等其他城市。
晚清艺人也认识到想要胜出,只有技术上的新奇还远远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吸收西戏的各种优点为我所用,凸显中国戏剧的精神和魅力。他们在对比中看到中西戏剧的不同美学特质:一讲求真实,一重视虚拟,并以艺人特有的敏锐、灵活和智慧对中西戏剧广采博纳,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表演。既然西戏的写实能吸引观众,那么中国戏剧也可以在虚拟中融入真实。19世纪70年代,上海京班在打斗中用的就是真功夫和真家伙。《观园琐谈》中记载:“《夺太仓》《忠节烈》等剧摹写豪雄忠烈之概,真觉神采奕奕,金鼓声中刀光飞舞,跳掷之技神化无伦……皆极能用真实本领,竭力献技,用相角斗。”[94]如此才能博得观众的赞叹,才能在中西武戏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京班所求的“真”并非只是“貌”——外在的布景、道具、声效等,而是更注重“神”——性格、感情及精神之真。岭南羁士在观看《雷轰张计宝》后说:“扮演张老之神情不真,则逆子之案情不露,是夜扮演者为吴凤鸣,能手也,声情激越,刻划逼真,观者佥发指,有陨涕者,顷刻间雷霆下击,玉虎鞫鞫,如闻其声……”[95]演出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对声效的运用也恰到好处,颇能表现中国戏剧的“真”精神。再如《名优演剧》中记载《迎宋灵》的演出:“为中国吐气而作也,命意既新,扮演尤妙,其旗帜之鲜明,士马之雄壮,而为二帝发丧仪从赫然有喇嘛僧,真是塞外风景矣。岳王忠心耿耿,声泪俱下……乃孙春恒所演,有声有色,令人忠义之气勃勃而生。”[96]该剧既贴合中国观众的感情,又有真的“喇嘛僧”出场,更有发自肺腑的真情表演,烘托出中国戏剧的“神”和“韵”,激发了观众的感情共鸣。
在与西戏长期的竞相生存中,上海戏剧形成迥异于传统的鲜明特色,其一项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西戏诸多元素的吸收和创新性运用。请看《西戏述新》中描述的一场西戏:“旁燃红色电光,忽一男子作杀妻状,匕首烁烁然,妻惧而折腰,旁两妇夺刀劝解,男子蓦刺妻胸前,妻倒地……斯时电光作紫色,幕复下旋……不觉抚掌叫绝。”[97]再看后来的《左公平西新剧》,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电光灯乍明乍暗……忽焉火把如林,鼓鼙动地,刀矛旗戟蚁聚蜂屯……令骂贼被焚死,夫人女公子守节不屈,先后饮刃,血溅横飞,座客皆惊,莫不浩然咨喟。”[98]剧中对灯光、道具的运用与西戏颇为相近,演绎的故事却更为感人,不仅使观众获得惊险体验,还带来情感升华。值得注意的是,主演此剧者正是自幼为西戏助演的艺人——夏月润,了解晚清戏剧者自然明白夏月润及其家族在晚清戏剧史与京剧史中的重要性,可见晚清中西戏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奇特。
综上所述,自19世纪50年代即开始的西戏东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我们需从史实出发,回归晚清历史语境,还原并理解“西戏”包含着各种戏剧、马戏、魔术、影戏、杂技等的复杂形态。虽然西戏与中国观众具有一定疏离性,但其演出具有持续性、多重传播渠道和多元表演主体,以及前卫性和经典性,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与中国戏剧及观众具有广泛的接触与交流互动关系。在上海租界的舞台上,中西戏剧既同台演出交流互动,又具有商业竞争关系。西戏具有新颖奇巧、惊险刺激等特点,并善于运用声光电等先进科技手段、广告宣传等营销策略,在对中国观众产生极大吸引的同时,对中国戏剧市场也产生了直接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晚清戏剧开始其现代化历程,中国艺人以奋力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开拓市场,通过苦练硬功、创新技术、汲取西戏优点为我所用等方法,创造出精湛绝伦的艺术,使晚清成为中国戏剧史上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一个时代,为中国戏剧在20世纪以绚丽的姿态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其智慧和精神对当前戏剧走出低迷具有启示意义。
需要注意,在晚清整个戏剧发展史中,西戏始终与中国戏剧竞相而存,是推动中国戏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构成独特的戏剧文化生态,只不过在晚清前期属于隐性阶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显性阶段,对于学界而言,通过探究隐性阶段揭示历史本源尤为重要。虽然“西戏”这一词语早已淡出大众视野,但是西戏东渐带来的中西戏剧文化之争并未停止,从历史经验来看,奋力拼搏、勇于创新正是戏剧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当前戏剧所应承继与发扬的重要精神。
(李云,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原载《戏曲研究》第13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4月版)
【注释】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天津报刊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3YJA751010)阶段性成果。
[1] 据《字林西报》相关信息可知,汉口1865年即曾有西人业余演出。参见“Hankou Theatrical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24,1865,p.2。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演过多场西戏。天津《时报》1886年9月4日第2版刊载《马戏将到》消息。天津作家张焘(张赤山)曾作《北城观西戏记》,收录于《海国奇谈》,上海文宜书局1895年版。《申报》1887年1月16日第3版《津门琐缀》中记载:“寓居天津之西人,于初六初七两夜,在总汇演剧辞年……中西人士履舄交错,固一时佳会也。”《国闻报》1899年5月31日第3版曾刊载《马戏先声》,介绍华伦马戏到津演出;《国闻报》1899年6月4日第3版《观马戏记》、1899年6月5日第3版《有目共赏》、1899年6月8日第3版《观戏志盛》,分别记录了该马戏班演出,及驻津美领事官邀请北洋大臣共同观戏的情况。
[2] 参见贤骥清《上海近现代剧场调查研究(1843—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22页。
[3] 徐珂编辑《清稗类钞选(文学 艺术 戏剧 音乐)》,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400页。
[4]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5] 黄爱华、李伟主编《新潮演剧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6] 有学者认为这是民谣歌剧《乞丐歌剧》,参见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
[7] 《记观西戏》,《申报》1876年2月24日第2版。
[8] 《西戏来沪》,《申报》1879年12月24日第3版。
[9] 参见静观老人《续记西戏》,《申报》1876年2月29日第3版。
[10] 《观大克傀儡戏记》,《申报》1894年3月28日第3版。
[11] 孙柏《十九世纪西方演剧与晚清国人的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12] 孙柏《十九世纪西方演剧与晚清国人的接受》,第43页。
[13] 静观老人《续记西戏》,《申报》1876年2月29日第3版。
[14] 胡祥翰、李维清、曹晟《上海小志 上海乡土志 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5] 《西戏开演》,《申报》1894年9月14日第6版。
[16] 静观老人《续记西戏》,《申报》1876年2月29日第3版。
[17] 《记观西戏》,《申报》1876年2月24日第2版。
[18] 《西戏来沪》,《申报》1879年12月24日第3版。
[19] 王祎《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
[20] 参见The NorthChina Herald,Dec.14,1850,p.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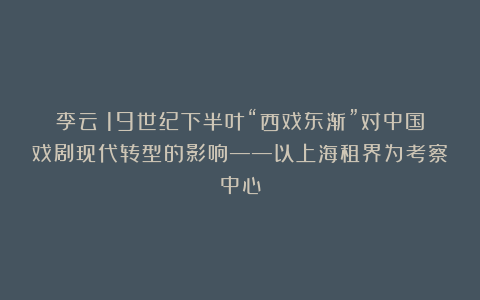
[21] 参见“The Sixtieth Performance of the A.D.C”,The Shanghai Courier,Dec.12,1878,p.3。
[22] 参见“91st Performance of the Amateur Dramatic Club”,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Mar.30,1888,p.18。
[23] 参见“The 119th Performance by the Amateur Dramatic Club”,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22,1900,p.3。
[24] 参见“Amateur Dramatic Club.162nd Produc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Dec.9,1911,p.17。
[25]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4页。
[26] 《西商串演戏文》,《申报》1875年6月9日第2版。
[27] 《西商串戏》,《申报》1875年6月9日第6版。
[28] 参见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8,1875,p.3。
[29] 参见[英]西蒙·特拉斯勒著,刘振前等译《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30] 参见《西商串戏纪略》,《申报》1875年6月12日第1版。
[31] 参见徐珂编辑《清稗类钞选(文学 艺术 戏剧 音乐)》,第400页。
[32] “The Circus: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22,1868,p.3.
[33] 参见“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the Great World Circu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22,1868,p.3。
[34] 《西人演戏》,《申报》1876年8月19日第2版。
[35] 徐珂编辑《清稗类钞选(文学 艺术 戏剧 音乐)》,第401页。
[36] 《外国戏园告白》,《申报》1877年9月19日第5版。
[37] 《丹桂茶园改演西戏》,《申报》1874年5月29日第5版。
[38] 《西戏翻新》,《申报》1889年3月13日第3版。
[39] 参见《英术师来申》,《申报》1874年5月12日第7版;《丹桂茶园改演西戏》,《申报》1874年5月28日第5版。
[40] 参见《三雅园开演夏思美奇戏》,《申报》1883年4月22日第4版;《奇戏将停》,《申报》1883年5月5日第3版。
[41] 《傀儡奇观》,《申报》1887年5月4日第3版。
[42] 《马戏迁移》,《申报》1874年8月3日第1版。
[43] 《看迎马戏》,《申报》1874年8月10日第2版。
[44] 参见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18,1888,p.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28,1888,p.3。
[45] 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
[46] 《开演影戏》,《申报》1875年3月18日第2版。
[47] 《外国戏园告白》,《申报》1877年9月19日第5版。
[48] 参见[英]西蒙·特拉斯勒著,刘振前等译《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第165页。
[49] “The Octoroon”,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13,1865,p.2.
[50] 参见[英]西蒙·特拉斯勒著,刘振前等译《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第164页。
[51] 参见李云《〈吟边燕语〉并非文明戏莎剧的唯一蓝本——清末民初莎士比亚中文译介与舞台演出关系新论》,《戏剧》2023年第4期,第114页。
[52] 徐珂编辑《清稗类钞选(文学 艺术 戏剧 音乐)》,第400页。
[53] 参见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第211页。
[54] 《西商串戏纪略》,《申报》1875年6月12日第1版。
[55] 《述马戏》,《申报》1874年8月14日第2版。
[56] 《鸟戏奇妙》,《申报》1883年4月29日第3版。
[57] 参见《出奇无穷》,《申报》1883年5月1日第3版。
[58] 参见“Mr.Miln and his Shakespeare company left Hongkong yesterday by the English mail and will arrive here early on Friday”,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15,1891,p.3。
[59] 参见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第210页。
[60] 参见“The Waldorf Troupe At The Theatre.As You Like It.”,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7,1903,p.5。
[61] 参见《印王赴东》,《申报》1883年5月16日第3版。
[62] 参见王祎《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第29页。
[63] 鸳湖隐名氏《洋场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12日第2版。
[64] 参见王祎《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第69页。
[65] 《英国领事清装游嬉观剧》,《申报》1873年4月2日第1版。
[66] 《津门琐缀》,《申报》1887年1月16日第3版。
[67] 《西国戏院合演中西新戏》,《申报》1874年3月16日第2版。
[68] 《观剧小记》,《申报》1889年3月18日第3版。
[69] 《西戏翻新》,《申报》1889年3月13日第3版。
[70] 晟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第2版。
[71] 据统计,1865年上海租界外侨2757人,华人146052人;1890年外侨4265人,华人202901人。参见王祎《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第71页。
[72] 外国戏园主人《外国男女马戏赠物》,《申报》1872年5月29日第6版。
[73] 《马戏不创于西人说》,《申报》1882年7月5日第1版。
[74] 《马戏初志》,《申报》1882年6月17日第2版。
[75] 参见《斗虎惊心》,《申报》1882年7月24日第2版。
[76] 《马戏初志》,《申报》1882年6月17日第2版。
[77] 《再志西戏》,《沪报》1882年6月21日第3版。
[78] 《西戏可观》,《申报》1883年4月27日第3版。
[79] 《论禁戏》,《申报》1876年10月18日第1版。
[80] 参见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18,1875,p.3。
[81] 参见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0,1875,p.3。
[82] 《开演影戏》,《申报》1875年3月18日第2版。
[83] 参见《新到外国戏》,《申报》1875年3月19日第2版。
[84] 参见《观演影戏记》,《申报》1875年3月26日第3版。
[85] 参见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第222页。
[86] 参见《看迎马戏》,《申报》1874年8月10日第2版。
[87] 参见《被虎伤眼》,《申报》1882年7月6日第3版。
[88] 平心居士《新年说》,《申报》1876年2月1日第1版。
[89] 都门惜花子《观剧闲评》,《申报》1873年2月3日第2版。
[90] 《观剧书所见》,《申报》1873年1月4日第3版。
[91] 《新增灯戏》,《申报》1879年11月30日第5版。
[92] 《三雅园灯戏》,《申报》1879年12月6日第6版。
[93] 《奇戏将停》,《申报》1883年5月5日第3版。
[94] 《戏园琐谈》,《申报》1872年6月4日第2版。
[95] 《观剧小记》,《申报》1872年8月13日第3版。
[96] 《名优演剧》,《申报》1876年6月27日第3版。
[97] 《西戏述新》,《申报》1888年12月31日第3版。
[98] 《观左公平西新剧有感》,《申报》1895年5月23日第1版。
编校:张 静
排版:王金武
审稿:谢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