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枥老骥|从绿皮车硬座到卧铺的“进化”
口琴曲:绿皮火车
写完那篇《抢票记》,盯着手机里12306的订单,突然就想起22年前那趟南下的绿皮车。那会儿我刚退休,兜里揣着第一个月的退休金,站在火车站售票窗口前,跟现在盯着”下铺”按钮时一样纠结,只是纠结的内容天差地别。
那年的夏天比现在还毒,火车站候车室的吊扇转得跟要散架似的,风里裹着汗味和方便面味。儿子在广州刚站稳脚跟,打了三个电话催我去看看。我攥着存折在售票窗口前徘徊了三趟,硬卧票价像块烧红的烙铁——268块,超过我当时退休金的三分之一。
“同志,要张硬座。”说出这话时,我感觉背后排队的人都在看我。不是心疼钱,是实在舍不得。那会儿老伴总说我,退休了该享享福,可一想到儿子在广州租的房子还没装空调,我就觉得这卧铺票烫手。
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买了硬座。上了车,对号入座时,却见一位胳膊上刺着猛虎的彪形大汉盘踞在我的座位上,那只猛虎正张牙舞爪地瞪着我。“师傅,这座位?……″我正嗫嚅着,却迎来一声猛喝:“是你的座位又怎么了?我先坐着,等会再归你″。我四顾,意图找列车员来调解,但根本就不见列车员的踪影,估计躲到哪儿纳凉去了。即便他在,恐怕也不敢冒犯这位“爷″。(请原谅我的懦弱,在铁塔似的凶神恶煞面前 ,我这文弱老头可没有什么优势可以与他对抗。今天回忆当年的情景,更觉开展扫黑除恶实属十分必要)。无奈之下,花了五元钱,向专事出租小凳的小贩租了一只凳子,在人缝中找了一个位置暂且安身。而那混蛋直到中途某站才摇摇摆摆旁若无人地穿过人群,从守车后门下了车,堂而皇之地扬长而去。我赶紧回归原位,那本来就是我的座位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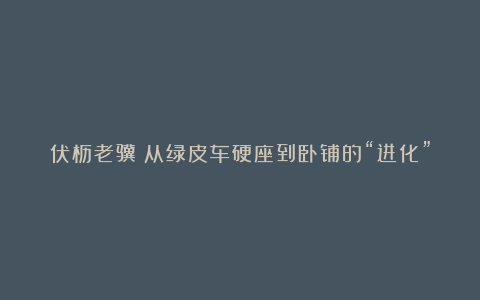
当年哪有什么高铁,放眼望去,这普通快车上人挤得满满当当,许多没有座位票的人就提着塑料袋包裹的行李,站在两排座位的中间。他们几乎全都是去广东打工的农民。想起当年的情景,毎每还是感慨万千呀!
那趟车是真热闹。硬座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过道里全是铺着报纸坐着的人,我对面坐了个抱着孩子的大嫂,孩子哭了一路,她奶也不够,最后掏出个干巴巴的馒头往孩子嘴里塞。我包里正好有老伴煮的茶叶蛋,悄悄塞给她一个,她非要给我两瓣橘子,那橘子酸得我牙都快掉了,却觉得比现在的进口水果还甜。
夜里实在困,就把头搁在小桌板上,没多久就被硌醒了。旁边座位上的小伙子看出我难受,往我身下塞了本杂志,说垫着能舒服点。那本封面都磨掉的《读者》,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卧铺替代品”。现在想想也有意思,那会儿大家挤在一起,谁也不嫌弃谁,分享个苹果、递瓶水都是常事,不像现在坐高铁,邻座全程戴着耳机,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
最狼狈的是快到广州时,我起身上厕所,刚站起来就被一个急刹车晃得差点摔倒,多亏后面一个大叔一把扶住我。等我回来,发现座位上多了件搭着的外套——是刚才那小伙子的,他怕我着凉,脱下来让给我披。那件带着汗味的蓝外套,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暖心。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后来应聘到广州某高校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就告别了硬座,一般放假回乡或长途出行都坐卧铺了。尽管高铁出现后,其快捷便利已经实现了“朝发夕至”,但其与飞机不相上下的价格,使得我们这些“不缺时间”的退休老人仍然对绿皮车青睐有加、不离不弃。于是买卧铺仍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特别是长途旅行时。
如今抢卧铺时,总忍不住跟老伙计们念叨:当年要是有12306,我可能还是会买硬座。并不是缺钱,而是少了点什么——少了那个塞杂志的小伙子,少了那个分橘子的大嫂,少了那种挤在人堆里,却觉得心里踏实的劲儿。
昨天跟孙子视频,他坚持让我坐飞机或者高铁去,我说还是坐绿皮车舒服。他不知道,我不是念旧,是总觉得,当年那个啃着馒头、攥着硬座票的老头,比现在躺在下铺里的我,多了点啥。大概是那种,日子虽然紧巴巴,心里却敞亮的劲儿吧。
今天的普通卧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