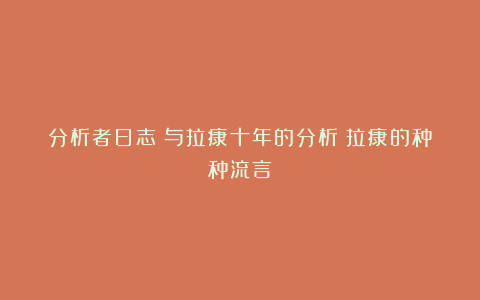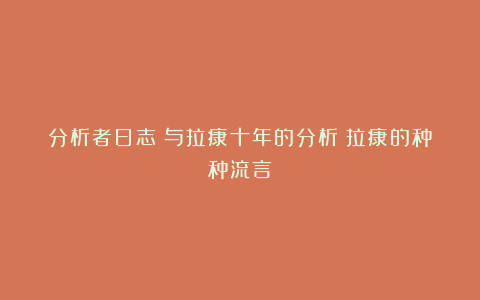|
与拉康分析的十年(死亡与欲望)
Une saison chez Lacan
作者:Pierre Rey 记者、剧作家
译者:张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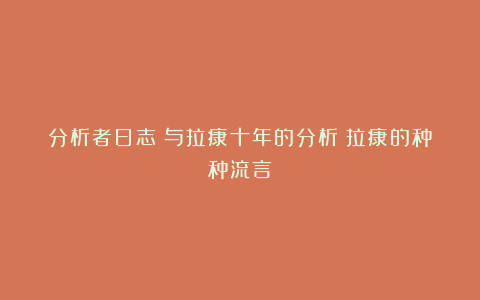 一些人对此理解错误,拥有过多却无法享乐,他们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金钱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身家上百万,他们会拼命榨取财富,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便获取双倍的金钱:通过给自身匮乏的无限性标上数字,他们跨越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界限。
金钱与分析相似。存在一个微妙的滑坡地带,在那里,目的与手段互相替代,颠倒了它们功能的逻辑。有时,说话的人由于不断说话,也会像倾听的人一样,变成沙发上的专业人士。言语、言语的实践、时间和收费,成为了生活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最终构成一种变态的颠倒结构,在这种存在中,实在被缩减为保持距离的文字之不真实,只有在话语的流动中,实在才会出现,但只是为了更好地消失。
就像他的来访者们无法没有他一样,他也在幻想中被他们的需求保护着,使他免于死亡;反过来,没有这群带着痛苦前来的灵魂,他能否存活?这些人来找他,让他为他们命名他们的欲望。
那么,他自己的欲望呢?当我们知道,在这套辩证法中,他被定义为“无为”者,固守死亡的位置,连他自己的生命都隐退其中?软包的房间,隔绝,封闭。有些人坐在河岸边太久,就冒着永远留在那里的最大风险。他们是行动的主人,激发着他们自己无法实践的行动;是中立的旁观者,他们的生命在大他者的话语洪流中消散,一旦走出诊室——他们真的走出来过吗?——便再也感受不到那炽热的脉动,精液与血液,心跳,撕裂,伤口。
我跟他说过圣人的功能、禁欲、放弃、退隐。他耸耸肩:
只有拉康那样拥有非凡广度的人,才能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进行分析,战斗,怀疑,愤怒,生活,探寻,享乐,受苦。无损地跨越由他界定的三个环套秩序——象征、实在、想象,并在每次疯狂回返后,都能以完整的、绝对严谨的满溢之言重新落地,从而使一切在别处重新打开,通向全然不同的事物。
有一次我病了。我告诉他,要取消第二天的预约。他的反应之迅速让我震惊,他立刻安排了接应,奇迹般地,几个小时之内,本该关闭的大门开启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人,只因为听到他的一句话,就开始对我视若珍宝。
暴风雨突袭。父亲回来接我。有人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父亲像捡起一根稻草般把我扛在肩上,为我挡住雨水,迈着稳健的大步,穿过寂静的村街,直至家门。那晚,我小小的身体随着他的步伐摇晃,被这股迎着暴风前进的巨大力量所眩晕,我感受到一种绝对的保护之强度。我之所以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那种能量的光芒,无论时隔多少光年,都被我感知到:曾经的孩子,蜷缩在父亲怀中,以及后来的我,在同样的力量面前重新成为孩子。在这两种情境中,都有同样的确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伤害我。
当时有传闻……“据说拉康那里有很多分析者自杀。”因为他接受倾听那些将死之人的话语,他成为极少数能接受他们无可避免之破碎风险的人。
几乎没有其他分析师会冒险去接触这些“向死而生”的人,哪怕只一次,只为直面他们的目光,也不愿让自己的名片上沾染上死亡的印记。
我注意到他那儿有个矮胖的黑发女人,爱笑,穿着一些褪色的、看起来并不昂贵的衣服。我在心里给她起名叫玛塞琳。
我们好几次都在后面的图书室碰面,那儿书架的阴影里藏着一本阿尼娅·泰亚尔写的《梦的解释》。
我曾在巴黎遍寻此书无果。不敢偷,也不敢请求拉康借给我,我只能在等待时狼吞虎咽地读,咒骂接待的格洛丽亚总是太快叫我进去,硬生生把我从那些秘密中拉走。
有一天晚上,她让我进去时,我想拿起那本书,却发现它不在原位。
我看到角落里,那位矮胖女人正拿着它。格洛丽亚请我跟她进去……
雨刷和雨水。我为自己提问的笨拙而懊恼,但我想知道。拉斯帕耶大道。
——因为孩子。我抱着他。是他替我承受了全部的撞击。
这样的绝望在他那里从不会被拒之门外。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把别人的生命握在手里。如果他稍有松手,稍有判断失误,说错一句话,沉默太久,或在不合适的时机多看了一眼,一切都可能坠入虚无:那些渴望死亡、注定死亡、几乎已经死去的人,被他从遥远的彼岸拉回来,没有他的介入,他们中有多少人能活下去?
还有另一个流言:“据说他有时候只让来访者待十秒钟。”
关于短时会谈的议论很多。这种方式冲击了太多既定观念,让那些把确定性寄托在惯例法则上的人目瞪口呆。也因为这件事,间接地,我惹恼了我的出版商。有一次,他偶然看见我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我和一位瑞士精神分析师同台。节目一小时。她前半场,我后半场。那位女士头发花白,身份显赫,庄重,刻板,说教,教条。我在轮到自己讲述刚出版的新小说前,半梦半醒地听着,忽然她说:
“在我那里,非常简单。会谈四十五分钟。我在桌上放个沙漏。最后一粒沙落下,结束。”
我愤怒地跳了起来:怎么能把一次会谈结束时那关键的停顿,交给一粒沙子的任意安排?她用四十年笃信不疑的语气,带着恼怒的轻蔑,把我狠狠贬到最底层。主持人如获至宝,立刻煽动起争执,直到我听到他说:“感谢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下周我们将……”
原来一小时已经过去:在激烈的辩论中,我竟一次都没有提及让我来到演播室的新书书名。
最初,拉康让我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如果他感到我有所犹豫或退缩,还会毫不迟疑地引导我继续。
在第二阶段,出于对听见他对我说话的恐惧,每当他想插话,我就焦躁地打断他。再之后,我完全服从于他的规则:真正的工作是在两次会谈的间隙中完成的,诊室只起到催化作用。我很快明白,他在一句话中途切断的字词之断裂,正是我需要探寻的地方,它的音节会萦绕在我体内,直到其中闪现出如雷击般的阐释。拉康猛然站起,那就是我必须寻找的地方——他所指示的那一刻的悬停。这个时刻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只要我接近一个出口,而没有他突然的起身,那把椅子推开的动作,以及他那熟悉的濒死般的叹息,这个出口就会对我保持隐形。十秒,二十分钟?我并不知晓。时间在这里不起作用:当缺乏强度时,那也只是死亡的无时之时。我这才发现,他在短时会谈中引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重新创造了生命本身的功能:让事物流动,通过重演那些让生命鲜活的意外,因为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是既成事实。相比之下,那种固定时长的安全感,在事后看来,只是一个无损于缄默的阻塞或陈词滥调所构成的口吃单调的舒适圈。
因此,从三段论推导来看,人们很容易看出,每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都在无意识里隐含着一种死亡的渴求。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通过职业规划来填补自己欲望的未知——到六十岁时,他将成为录用他的公司的总裁——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他选择将生活中所有可能带来享乐的未知排除在外,所以他是在渴望死亡,以逃避真正的生活。
但有一个矛盾的奇迹能把他从四十年的纯粹损失中拯救出来:失败。
然而,对于那些“赢得救赎”的成功者来说,谁又敢写出一部《失败论》呢?
当我想说的太多,害怕拉康不让我讲完时,我会飞快地倾泻而出,好让他吸收哪怕最微小的部分——始终害怕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天,我倾诉完所有,认为他要站起来了:但他没有。他坐在桌前,继续在便签纸上写着汉字,仿佛忘了我的存在。忽然,房间里失去了我声音的回响,我感到极度尴尬,在椅子上扭动不安;他仍无动于衷。门外,我知道患者们已经排起了队。他不可能让我在这场属于我沉默的全新折磨中待太久。然而十分钟过去,他依然伏案疾书。
肌肉紧绷,完全卡住,我正准备开口——但能说什么呢?——这时,他用那拖腔的语调嘟哝了他一贯的引导词:
这个“没什么”挡住了那本应以其强度让我意识到自己压抑之物的难以承受的焦虑。
一小时后,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彻底崩溃。我无法从喉咙里挤出任何声音,除了那句愤怒的“没什么”,它把我带回到一个我模糊感知到的“全部”,那广阔的无名感令我石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康以他那善变的节奏,不时重复这种延长带来的不安,直到我终于被那剧烈的动荡迫使去理解:什么叫作“抗拒的力量”。
有时,他会点起一支雪茄。凭借那螺旋形的造型,我认出是Davidoff出的Punch Culebras。这种雪茄只有在瑞士才能买到。我偶尔会去日内瓦。我问他是否需要我给他带一些,他接受了。我每次去都会买两盒,而让我格外享受的是,每次都要他付全款。
期间,他常用表情示意他对烟灰缸的不耐烦,因为我总要把手伸到他面前,我最终干脆把烟灰缸放在自己腿上。
我坐在窗前,窗外是院子里的石板路和一棵栗树。他伏在桌前,面朝墙壁,把右侧面容展现给我。很多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沉默已产生真理的效应时,会突然转过椅子,直视我,以一个手势为那看似未被听见的话语作结。在最初,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总是故作勇敢地坚持不低头。但我很快明白,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对抗完全源于我的想象界,从那以后,我的目光不再是挑战,而只是疑问。
有一天,他对弥漫在诊室里的烟雾发表了评论。他反复提到,直到我明白,最好在会谈中不要吸烟。
从此,我再也没有从口袋里拿出Philip Morris香烟:我的最后一种防御性自动动作,就这样被彻底放下。
这场持久的较量中,我先后学会了守时,将付费与工作本身联系起来,逐步舍弃那些会延缓工作进展的小动作、姿势或炫示性的姿态。这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
我不再想取悦他,也不再试图证明自己,不再装腔作势,不再想与他竞争。
必须说明的是,就在不久前,他给了我一堂深刻的课。有一个下午,我被他某次沉默——或也许是某次罕见的发言——激怒,愤怒地质问:
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令人瓦解的温柔,长叹一声,仿佛世界尽头般,然后轻声说:
从那一刻起,我接受了自己的赤裸,我只想去理解。但不幸的是,我走得越远,理解得越少。每一次向前迈步,都在我的意识中打开潜意识的新领域,但它的效果只是让我愈发失去对前一天似乎看见之物的掌控,并深切感受到那无尽的未知所带来的沮丧与绝望。
当我犯下解释错误时,他从不反驳我:可见他对治疗方向与自己思路的直觉有多么笃定,才能让我在那些把我自己迷失其中的曲折中随意挣扎……
缰绳牢牢握在他手里,他从不给我任何指引,也不指出我陷入的种种死胡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渴望他的认可。他只是微笑着点头。我带着握住真理的确信走出诊室,但夜晚很快就摧毁了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我有充分理由把他对我摸索和那些看似辉煌却空洞的诡辩的沉默,理解为一种谎言。
我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另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判断我所把握的答案是否正确,好让我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靠自己发现了:当我真正找到正确答案时,那个问题会突然失去所有内容,失去存在的意义,自然消失。在那时,问题的所有面向都会清晰地呈现给我:不再有任何阴影。在这种被感受到的确定状态里,平静与欢愉交融,我甚至不需要再去询问拉康的看法:我知道。
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不安:大他者的谎言,有时是通向自身真理所必需的。
一些人对此理解错误,拥有过多却无法享乐,他们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金钱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身家上百万,他们会拼命榨取财富,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便获取双倍的金钱:通过给自身匮乏的无限性标上数字,他们跨越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界限。
金钱与分析相似。存在一个微妙的滑坡地带,在那里,目的与手段互相替代,颠倒了它们功能的逻辑。有时,说话的人由于不断说话,也会像倾听的人一样,变成沙发上的专业人士。言语、言语的实践、时间和收费,成为了生活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最终构成一种变态的颠倒结构,在这种存在中,实在被缩减为保持距离的文字之不真实,只有在话语的流动中,实在才会出现,但只是为了更好地消失。
就像他的来访者们无法没有他一样,他也在幻想中被他们的需求保护着,使他免于死亡;反过来,没有这群带着痛苦前来的灵魂,他能否存活?这些人来找他,让他为他们命名他们的欲望。
那么,他自己的欲望呢?当我们知道,在这套辩证法中,他被定义为“无为”者,固守死亡的位置,连他自己的生命都隐退其中?软包的房间,隔绝,封闭。有些人坐在河岸边太久,就冒着永远留在那里的最大风险。他们是行动的主人,激发着他们自己无法实践的行动;是中立的旁观者,他们的生命在大他者的话语洪流中消散,一旦走出诊室——他们真的走出来过吗?——便再也感受不到那炽热的脉动,精液与血液,心跳,撕裂,伤口。
我跟他说过圣人的功能、禁欲、放弃、退隐。他耸耸肩:
只有拉康那样拥有非凡广度的人,才能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进行分析,战斗,怀疑,愤怒,生活,探寻,享乐,受苦。无损地跨越由他界定的三个环套秩序——象征、实在、想象,并在每次疯狂回返后,都能以完整的、绝对严谨的满溢之言重新落地,从而使一切在别处重新打开,通向全然不同的事物。
有一次我病了。我告诉他,要取消第二天的预约。他的反应之迅速让我震惊,他立刻安排了接应,奇迹般地,几个小时之内,本该关闭的大门开启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人,只因为听到他的一句话,就开始对我视若珍宝。
暴风雨突袭。父亲回来接我。有人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父亲像捡起一根稻草般把我扛在肩上,为我挡住雨水,迈着稳健的大步,穿过寂静的村街,直至家门。那晚,我小小的身体随着他的步伐摇晃,被这股迎着暴风前进的巨大力量所眩晕,我感受到一种绝对的保护之强度。我之所以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那种能量的光芒,无论时隔多少光年,都被我感知到:曾经的孩子,蜷缩在父亲怀中,以及后来的我,在同样的力量面前重新成为孩子。在这两种情境中,都有同样的确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伤害我。
当时有传闻……“据说拉康那里有很多分析者自杀。”因为他接受倾听那些将死之人的话语,他成为极少数能接受他们无可避免之破碎风险的人。
几乎没有其他分析师会冒险去接触这些“向死而生”的人,哪怕只一次,只为直面他们的目光,也不愿让自己的名片上沾染上死亡的印记。
我注意到他那儿有个矮胖的黑发女人,爱笑,穿着一些褪色的、看起来并不昂贵的衣服。我在心里给她起名叫玛塞琳。
我们好几次都在后面的图书室碰面,那儿书架的阴影里藏着一本阿尼娅·泰亚尔写的《梦的解释》。
我曾在巴黎遍寻此书无果。不敢偷,也不敢请求拉康借给我,我只能在等待时狼吞虎咽地读,咒骂接待的格洛丽亚总是太快叫我进去,硬生生把我从那些秘密中拉走。
有一天晚上,她让我进去时,我想拿起那本书,却发现它不在原位。
我看到角落里,那位矮胖女人正拿着它。格洛丽亚请我跟她进去……
雨刷和雨水。我为自己提问的笨拙而懊恼,但我想知道。拉斯帕耶大道。
——因为孩子。我抱着他。是他替我承受了全部的撞击。
这样的绝望在他那里从不会被拒之门外。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把别人的生命握在手里。如果他稍有松手,稍有判断失误,说错一句话,沉默太久,或在不合适的时机多看了一眼,一切都可能坠入虚无:那些渴望死亡、注定死亡、几乎已经死去的人,被他从遥远的彼岸拉回来,没有他的介入,他们中有多少人能活下去?
还有另一个流言:“据说他有时候只让来访者待十秒钟。”
关于短时会谈的议论很多。这种方式冲击了太多既定观念,让那些把确定性寄托在惯例法则上的人目瞪口呆。也因为这件事,间接地,我惹恼了我的出版商。有一次,他偶然看见我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我和一位瑞士精神分析师同台。节目一小时。她前半场,我后半场。那位女士头发花白,身份显赫,庄重,刻板,说教,教条。我在轮到自己讲述刚出版的新小说前,半梦半醒地听着,忽然她说:
“在我那里,非常简单。会谈四十五分钟。我在桌上放个沙漏。最后一粒沙落下,结束。”
我愤怒地跳了起来:怎么能把一次会谈结束时那关键的停顿,交给一粒沙子的任意安排?她用四十年笃信不疑的语气,带着恼怒的轻蔑,把我狠狠贬到最底层。主持人如获至宝,立刻煽动起争执,直到我听到他说:“感谢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下周我们将……”
原来一小时已经过去:在激烈的辩论中,我竟一次都没有提及让我来到演播室的新书书名。
最初,拉康让我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如果他感到我有所犹豫或退缩,还会毫不迟疑地引导我继续。
在第二阶段,出于对听见他对我说话的恐惧,每当他想插话,我就焦躁地打断他。再之后,我完全服从于他的规则:真正的工作是在两次会谈的间隙中完成的,诊室只起到催化作用。我很快明白,他在一句话中途切断的字词之断裂,正是我需要探寻的地方,它的音节会萦绕在我体内,直到其中闪现出如雷击般的阐释。拉康猛然站起,那就是我必须寻找的地方——他所指示的那一刻的悬停。这个时刻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只要我接近一个出口,而没有他突然的起身,那把椅子推开的动作,以及他那熟悉的濒死般的叹息,这个出口就会对我保持隐形。十秒,二十分钟?我并不知晓。时间在这里不起作用:当缺乏强度时,那也只是死亡的无时之时。我这才发现,他在短时会谈中引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重新创造了生命本身的功能:让事物流动,通过重演那些让生命鲜活的意外,因为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是既成事实。相比之下,那种固定时长的安全感,在事后看来,只是一个无损于缄默的阻塞或陈词滥调所构成的口吃单调的舒适圈。
因此,从三段论推导来看,人们很容易看出,每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都在无意识里隐含着一种死亡的渴求。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通过职业规划来填补自己欲望的未知——到六十岁时,他将成为录用他的公司的总裁——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他选择将生活中所有可能带来享乐的未知排除在外,所以他是在渴望死亡,以逃避真正的生活。
但有一个矛盾的奇迹能把他从四十年的纯粹损失中拯救出来:失败。
然而,对于那些“赢得救赎”的成功者来说,谁又敢写出一部《失败论》呢?
当我想说的太多,害怕拉康不让我讲完时,我会飞快地倾泻而出,好让他吸收哪怕最微小的部分——始终害怕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天,我倾诉完所有,认为他要站起来了:但他没有。他坐在桌前,继续在便签纸上写着汉字,仿佛忘了我的存在。忽然,房间里失去了我声音的回响,我感到极度尴尬,在椅子上扭动不安;他仍无动于衷。门外,我知道患者们已经排起了队。他不可能让我在这场属于我沉默的全新折磨中待太久。然而十分钟过去,他依然伏案疾书。
肌肉紧绷,完全卡住,我正准备开口——但能说什么呢?——这时,他用那拖腔的语调嘟哝了他一贯的引导词:
这个“没什么”挡住了那本应以其强度让我意识到自己压抑之物的难以承受的焦虑。
一小时后,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彻底崩溃。我无法从喉咙里挤出任何声音,除了那句愤怒的“没什么”,它把我带回到一个我模糊感知到的“全部”,那广阔的无名感令我石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康以他那善变的节奏,不时重复这种延长带来的不安,直到我终于被那剧烈的动荡迫使去理解:什么叫作“抗拒的力量”。
有时,他会点起一支雪茄。凭借那螺旋形的造型,我认出是Davidoff出的Punch Culebras。这种雪茄只有在瑞士才能买到。我偶尔会去日内瓦。我问他是否需要我给他带一些,他接受了。我每次去都会买两盒,而让我格外享受的是,每次都要他付全款。
期间,他常用表情示意他对烟灰缸的不耐烦,因为我总要把手伸到他面前,我最终干脆把烟灰缸放在自己腿上。
我坐在窗前,窗外是院子里的石板路和一棵栗树。他伏在桌前,面朝墙壁,把右侧面容展现给我。很多时候,当他觉得自己的沉默已产生真理的效应时,会突然转过椅子,直视我,以一个手势为那看似未被听见的话语作结。在最初,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总是故作勇敢地坚持不低头。但我很快明白,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对抗完全源于我的想象界,从那以后,我的目光不再是挑战,而只是疑问。
有一天,他对弥漫在诊室里的烟雾发表了评论。他反复提到,直到我明白,最好在会谈中不要吸烟。
从此,我再也没有从口袋里拿出Philip Morris香烟:我的最后一种防御性自动动作,就这样被彻底放下。
这场持久的较量中,我先后学会了守时,将付费与工作本身联系起来,逐步舍弃那些会延缓工作进展的小动作、姿势或炫示性的姿态。这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年。
我不再想取悦他,也不再试图证明自己,不再装腔作势,不再想与他竞争。
必须说明的是,就在不久前,他给了我一堂深刻的课。有一个下午,我被他某次沉默——或也许是某次罕见的发言——激怒,愤怒地质问:
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令人瓦解的温柔,长叹一声,仿佛世界尽头般,然后轻声说:
从那一刻起,我接受了自己的赤裸,我只想去理解。但不幸的是,我走得越远,理解得越少。每一次向前迈步,都在我的意识中打开潜意识的新领域,但它的效果只是让我愈发失去对前一天似乎看见之物的掌控,并深切感受到那无尽的未知所带来的沮丧与绝望。
当我犯下解释错误时,他从不反驳我:可见他对治疗方向与自己思路的直觉有多么笃定,才能让我在那些把我自己迷失其中的曲折中随意挣扎……
缰绳牢牢握在他手里,他从不给我任何指引,也不指出我陷入的种种死胡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渴望他的认可。他只是微笑着点头。我带着握住真理的确信走出诊室,但夜晚很快就摧毁了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我有充分理由把他对我摸索和那些看似辉煌却空洞的诡辩的沉默,理解为一种谎言。
我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是,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出另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判断我所把握的答案是否正确,好让我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靠自己发现了:当我真正找到正确答案时,那个问题会突然失去所有内容,失去存在的意义,自然消失。在那时,问题的所有面向都会清晰地呈现给我:不再有任何阴影。在这种被感受到的确定状态里,平静与欢愉交融,我甚至不需要再去询问拉康的看法:我知道。
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不安:大他者的谎言,有时是通向自身真理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