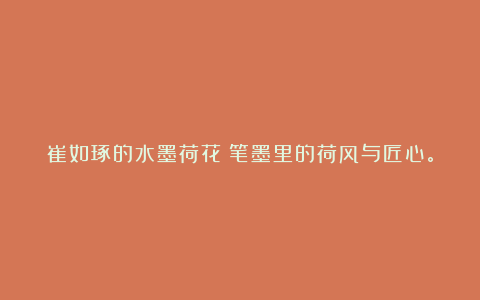崔如琢写荷,先以篆隶笔意立骨,再以指墨破形。荷茎如铁线篆,一笔勒出金石声;荷叶以阔笔泼墨,层层积染,破墨、焦墨、渍墨轮番上阵,边缘飞白似裂帛,墨色里暗涌风雨。丈二匹旧宣纸上,他每日研磨四砚墨汁,八日而成八幅《荷风盛世》:荷叶以“墨海”称雄,荷花只一点朱砂,宛如暗夜星火,照见“墨为主,色为辅”的孤高美学。
更绝的是指墨——指肚、指尖、指甲轮番叩击纸面,《醉秋》中荷叶的筋脉、虫蚀、风霜全在指痕里苏醒,偶然性与控制力被推向刀锋:一按一捻,便见天地洪荒;一提一收,又显秋毫精审。毛笔的“书写性”被手指的“身体性”替代,大写意自此有了心跳与体温。
崔如琢的留白不是空白,是风、是气、是“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浩瀚。十四米手卷《冷碧清秋水,秀色空绝世》,墨色铺陈仅三分,留白却占七分;观者循着空白呼吸,仿佛听见荷叶翻动的沙沙声,嗅到水气浮动的微凉。
他又将山水格局移入荷塘:枯笔飞白写湖石嶙峋,泼墨氤氲作云水流动,荷花在虚实之间亭亭而立,花是花鸟,势是山水。于是,盈尺小品也见千里之势,丈八巨制亦存芥子之微,传统花鸟的边界被悄然拆除。
《荷风盛世》长十八米,悬于人民大会堂。五十六朵荷花次第盛放,寓五十六族同心;叶如巨掌,谐音“和谐逢盛世”。崔如琢搭三层画架,汗透重衫,仍每日钤印一方,印文皆自刻——“荷风”“盛世”“指墨乾坤”……印与画、血与墨共同浇筑成一件当代“庙堂之作”。
这不是简单的主题先行,而是把个人体温、时代心跳一并摁进宣纸。他说“笔墨当随时代”,却坚持“随”不是迎合,而是让时代的风穿过自己的身体,再化作纸上雷霆。
《盛世荷风》在香港佳士得拍出1.28亿港元:焦墨塑叶,灰墨写影,花冠低垂却风骨铮铮,“娇艳而不媚,沉着而不浮”。
《玉露洗残红》:红白双荷顾盼,石青荷叶轻若云烟,指墨的朴拙撞见色彩的通透,恍若晨露滴落残梦。
盈尺小品《听雨眠》:只写一花一石,却通过指墨的涩重与留白的轻灵,将“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宋人诗意,转译成当代人心灵深处的微颤。
崔如琢说:“画画不是技术,是修养的体温计。”他的荷花,是雄强与空寂的合谋,是庙堂与山林的握手,更是千年笔墨与当下心跳的一次对视。无论丈二鸿篇,还是掌中小景,皆在指墨与留白之间,为这个时代留下一声低沉而悠长的回响。
崔如琢的水墨荷花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