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点赞和在看是
对我最大的鼓励
❤️❤️❤️❤️❤️
壹
前言
1948年盛夏,五常连着下了好几天雨。雨一阵猛过一阵,山上冲下的水裹着泥沙,把县城老法院后头那几间破屋冲得摇摇晃晃。到了第三天清早,靠东墙的那间土坯房塌了,一地砖瓦夹着黑泥,像是翻出了几十年前的事。
那天是个星期天,没啥人上工,工地上只留了几个修缮的老把式,蹲在泥水里清废料。一个小工用锄头刨地,刨着刨着“哐”地一下碰到个硬物。起初以为是哪年埋的坛子,可扒开泥后才发现,是一个玻璃缸,泥水里泡着个模糊的东西。
贰
致敬
老冯是工头,干了几十年土木活。他弯腰抬起缸,一手用袖子抹了抹缸壁。刚一看清,撬棍就从他手里掉了下去。玻璃缸里,是个人头,肿得厉害,但左眉骨上那道疤还在,一道斜斜的刀痕,从眼角一直拉到额头上。
有人站在边上咕哝了一句:“这不会是……汪雅臣吧?”
汪雅臣,这个名字在五常、桦树村一带,老一辈都知道。
听说他是抗联第十军的军长,脑门上的疤是蛤蜊河子突围时,被日本兵刺刀削的。那回他差点就逃出来了,结果身后跟着的叛徒突然开了枪,一弹打穿了他的膝盖。日军冲上来,把他活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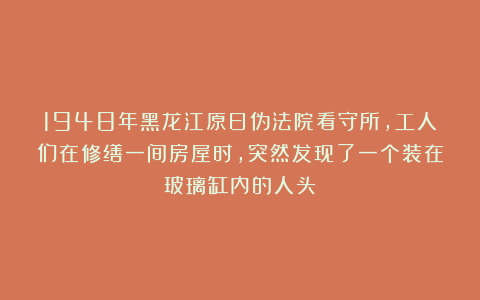
人们后来都说,那枪,是冲着腿打的,不想他死,要活捉。
缸底压着一块锈透了的铁牌,能辨出“匪首汪雅臣”几个字,剩下的模糊不清。但铁牌边缘有几道清晰的牙印,像是当年有人用尽全身力气咬住它,不让它掉下去。
这个消息像长了腿,没两天就传到了三十里外的桦树村。七十多岁的张老汉非得来看,孙子搀着,一步步挪进塌房的废墟。他手一摸到玻璃缸,先是愣住,然后哇地哭了出来。嗓子像是被烧过的破布一样沙哑,他一边哭一边说:“是他……是将军……”
他说他记得清楚,1941年冬天,他爹送粮去抗联,自己跟着。就在县城口,看见日军把汪将军绑在法院门口的柱子上,嘴里灌辣椒水。灌完又灌,辣得满脸是血。他还记得将军当时嘴角往上翘着,没低头。
“还笑,说东北人的骨头比刺刀硬。”
这话他记了一辈子。
查日伪的老档案,的确有记载:汪雅臣被斩首之后,头颅挂在五常城门三天示众。可第三天夜里突降大雪,天没亮就有人发现脑袋没了,只剩一根绳子还挂在钉子上,绳子是被锯断的。
谁干的?没人知道。
后来推测,是抗联的人潜进城,用锯子锯断的那根绳。抢下头颅,用棉袄裹了带走。可自此,这颗头颅就像蒸发了一样,没人再提,也没人敢提。直到七年后,连日暴雨把那座老房子的密室冲开,头颅才又出现在世人眼前。
那一年,哈尔滨烈士陵园还没完全建好。头颅被送去防腐修复,重新装进特制的玻璃缸,陈列起来。旁边摆着一截生锈的枪管,是他牺牲时手里握着的,紧紧的,怎么也掰不开。玻璃缸里的福尔马林里,还漂着几块褐色的碎布,是当年用来包裹头颅的棉袄残片,已经腐蚀得不成形。
县志里记了一笔,说当时全县百姓自发凑出三升高粱米,熬成稀粥祭拜。没人组织,没人通知,大家听到消息就来了。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
有个老太太,卖豆腐的,手上还戴着火气没散的棉布套袖。她拎着刚出锅的豆腐,一块块地摆在玻璃缸前,嘴里念叨:“他当年总拿炒面换我豆腐,问我豆腐好不好吃。”她念一句,抹一下眼泪。
还有老人说他小时候在林子里遇见过将军,说他笑起来有点倔,说话不多,常年咳嗽,说是肺里进过水——冬天冰河里爬出来的。
在烈士陵园的展柜前,如今仍摆着冻柿子,年年都有,不知道是谁开始的。陵园管理员说:“最早是个小孩放的,说是他爷爷讲过,将军最爱吃冻柿子。”
站在那缸前面,能看到水波轻轻晃动的反光。那缸里,装着一个将军的头颅,也装着这片土地不肯低头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