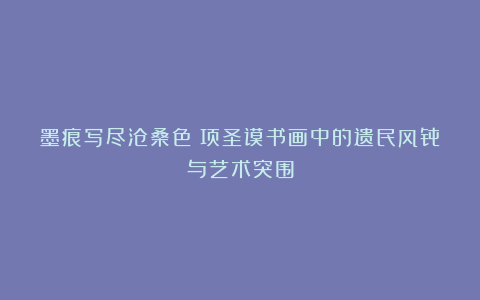《鹧鸪天·读项圣谟枯木图》
乱石嶙峋托病柯,残山剩水泪痕多。
朱阑梦断描金粉,墨戏神凝化剑戈。
松似怒,竹如歌,一腔孤愤寄岩阿。
谁言草木无情思?夜夜风涛吼大河。
在崇祯十七年那个春雨凄迷的暮春,项圣谟听闻煤山噩耗后,将书斋’易庵’改署’胥山樵’,这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实则是明末清初文人精神史的重要注脚。作为项元汴之孙,他本可承袭’天籁阁’的富丽风雅,却选择以枯笔焦墨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创伤记忆,这种抉择背后,是遗民艺术家面对历史断裂时的美学抵抗。
项圣谟的’墨戏’绝非简单的笔墨游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树风号图》中,那株虬曲盘踞的参天古木,根系裸露如苍龙之爪,树身皴擦似战甲鳞片,顶端却突兀地生出新枝。这种’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视觉隐喻,恰是画家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沉默反驳——当松江画派沉迷于柔润的’南宗’笔墨时,项圣谟以北方山水的峻拔骨力,重构了文人画的忧患意识。
上海博物馆藏《山水诗画册》中’松涛似带铜驼泣,墨点无多泪点多’的题跋,揭示了其艺术语言的精神密码。他将元代王冕’不要人夸好颜色’的墨梅传统,发展为更具张力的视觉政治学。那些看似随意的苔点,实则是《诗经》’黍离之悲’的图像转译;画中反复出现的空亭,既是对倪瓒美学的致敬,更是对’天下无道则隐’的儒家理想的坚守。
在《招隐图》长卷里,项圣谟创造性地将李唐《采薇图》的叙事性引入文人山水。卷首题’此去青山可埋骨’,中段却突然插入樵夫与隐士的激烈辩论,最终以’满目疮痍笔底收’的混沌山水收束。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结构,打破了吴门画派恬淡的园林范式,展现出遗民艺术特有的精神痉挛。
七律《题项圣谟山水册》
朱明残照落毫端,尺幅能藏万仞峦。
墨染铜驼荆棘泪,诗题铁马夜霜寒。
已删粉黛存筋骨,更借云山正衣冠。
莫道书生无血性,丹青原是剑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