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狮城掠影之市井烟火
图文/林海燕
一
晨曦初染,牛车水已在微光中醒来。像往常一样,我仍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晨七时,我立于居住的小区阳台前,打开窗户。新加坡的天光还未亮透,淡蓝色天幕下切割出天空的阴影,像是在提醒着:这座城从不真正沉睡。
乌节路两侧的雨树垂下气根,在晨雾中如同悬空的竖琴弦。晨跑者沿着滨海湾的步道慢跑,湿润的海风轻拂过脸庞,远处高楼大厦的轮廓在朝霞中渐渐清晰,新加坡的清晨总是充满活力与希望。
今天是旅途最轻松的一天,主要是逛街、吃美食,还有买美食。妹妹先是带我去商场购物,买好后放回家里,然后又去小印度街区购物。若不是三只行李箱实在装不下,还真想把商场都搬回家。
儿子帮我们拎包。他说:“早知这么累,还不如回家玩手机。”我马上问:“想买点什么送同学?”他说:“想送爸爸礼物。”我说:“你爸喜欢抽烟,要不买条烟?”妹妹说:“新加坡的酒和烟特别贵,不提倡也不适合买。”儿子立刻接道:“对,不能让他抽烟,必须要让他戒烟。”最后,儿子给他父亲选了南洋咖啡和营养麦片。
妹妹为了做好导游,自己先查阅了小红书,一路给我讲解。她常说:“你自己不会做攻略。”我说:“有你这样好的导游,还用得着我做攻略?”她问:“你总有自己喜欢的地方或食物吧?”我说:“我喜欢着你的喜欢。”妹妹说我是耍无赖。我笑笑。
一路上,小印度街随处可见大象雕塑。灰扑扑地立着,象鼻朝天卷起,倒像是向天讨要什么东西。那象眼是两颗玻璃球,嵌在石膏里,偏又反着光,竟显出几分活气来。
游人每每驻足,摸一摸象腿,便心满意足地离去。我也上前摸了摸,象腿早已被摸得发亮,青灰里透出黝黑,仿佛真有什么灵验。小贩支着摊,卖些珠串、香包,也卖小象木雕,说是“开过光的”。我也买了一串小饰品塞进包里,大抵是图个吉利。
我忽然想:这象快活吗?日日被人摩挲,风吹雨淋,还要驮着许多痴心妄想。我挤出笑容,在象前拍照,而象依然沉默,一副与人无关的模样。
立于天福宫前,仰视雕梁画栋间缭绕的香火,时光在飞檐斗拱上留下斑驳印记,仿佛百年光阴在烟火中无声流淌。
信步宝塔街,骑楼长廊下,油彩饱满的南洋旗袍与斑斓的纸扇悬垂于店铺前,如一道流动的东方长卷。阳光斜穿棚顶,光斑跳跃在青石板路上,古旧与新潮在此交缠共生。
移步小印度,空气陡然换了调子,浓郁咖喱与辛烈香料的气息如无形之手牵引鼻息。竹脚中心内,印度妇人纱丽飘逸,穿梭于各色摊铺间,指尖拂过金饰的光泽与纱丽的柔滑,市声喧哗如一首异域歌谣。维拉玛卡里雅曼兴都庙的塔楼上,无数神灵雕像被阳光镀亮,俯视着凡尘的虔诚与喧嚣。
小印度神庙的铜铃声中,步行至佛牙寺,未进寺内,便觉肚子疼得厉害。我对妹妹说:“实在熬不住,肚子太疼了。”妹妹说:“那到里面上个厕所。”我说:“不是想上厕所,就是纯粹的痛。”妹妹说:“先去里面参观再说。”我说:“疼得厉害,走都走不了,怎么参观?”
妹妹不明所以,我也莫名其妙。突然看到横梁上写着“百龙宝殿”,我对妹妹说:“我属狗,来到百龙之地,是否这个原因?”妹妹说我是迷信。我说:“不知是不是迷信,但确实疼得厉害,这是事实。”最终,妹妹自己去寺内参观,我留在门口等候。
闲来无事,我发信息给好友说明情况。他回复:“这是心理暗示,也可以说是种玄学,说明你有慧根有灵性。试着念:百无禁忌。”
说来奇怪,听他这么一说,我口念“百无禁忌”,肚子竟不疼了。我发信息给妹妹:“你们参观好了吗?我肚子不疼了。”妹妹回复:“在等电梯,准备下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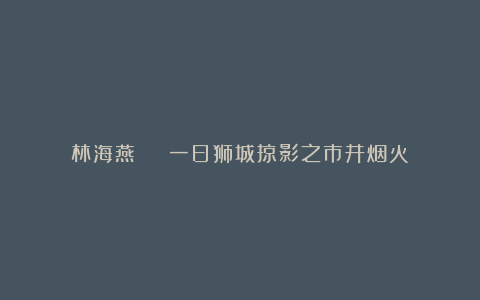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反正我信。
二
一日疾行,从牛车水的雕花窗棂到Supertree的冷冽光芒,从小印度的斑斓铺陈到植物园的夜露清芬。新加坡如万花筒旋转,每个碎片都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它不惧在摩天楼群中为古庙留一席之地,亦能在未来森林里容兰花幽然吐蕊。
行至食肆聚集处,香气骤然浓烈如无形之手牵引着我们。Nana泰国餐厅里,冬阴功汤翻腾着红艳气泡,辛辣酸香直冲鼻腔;金黄酥脆的印度飞饼被师傅凌空甩成薄翼,裹着咖喱的浓烈滋味在舌尖轰然绽放。南洋风味的浓墨重彩,在这方寸餐盘间酣畅淋漓地泼洒开来。
咖啡店在新加坡是极寻常的,横竖不过几步路便有一家。最有名的就是“南洋咖啡店”,招牌上照例画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旁边写些“传统”“古早”之类的字眼。店门口照例摆几张折叠桌,经年累月地立在那里。店家似乎很懂旅客心思,在桌上放着一只特色咖啡杯,供过路人拍照。
妹妹带着我走进一家,要了杯南洋咖啡。她说,来新加坡不喝南洋咖啡,相当于白来一样。店主是个五十上下的汉子,肤色黝黑,眼角的皱纹里夹着汗珠。他并不答话,只略一点头,便转身去摆弄那些器具。那是一只长嘴铜壶,壶嘴极细,倒像化学实验室里的什么仪器。他将咖啡粉装入布袋,吊在壶嘴上,沸水便从长嘴里泻下,穿过布袋,滴入下面的铁罐中。这过程极慢,一滴,又一滴,咖啡色渐渐浓了。
小印度的地面总是热闹的,柏油路被正午的太阳晒得发亮,人影投在上面,像洇开的墨迹。商贩的摊位前堆着金盏花环,橘红与明黄纠缠着坠到地面,花瓣被无数鞋底碾过,渐渐成了潮湿的碎末,混着檀香与咖喱的气味,黏在行人拖鞋底上。“新加坡小印度地区的地面画,通常是科尔姆画(Kolam)或类似的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宗教和社会意义。”妹妹一路向我详细介绍,“这些画常见于印度社区,尤其在节日或重要场合时出现。”
三
夜幕终于温柔垂落,狮城的海风挟着咸腥气息拂面而来。游人如织,大抵是些皮肤白皙的欧罗巴人,或是黄面皮的东洋客,皆向着那灯火辉煌处涌去。
我们依偎在滨海湾畔,一群带有“海”名字的人相约来到风景如画的东海岸,坐在珍宝海鲜坊,吃着珍宝海鲜。我们一边欣赏着波光粼粼的海景,一边大快朵颐着招牌辣椒螃蟹和黑胡椒蟹,欢笑声与海浪声交织成最动人的夏日乐章。
我们点的蟹来了。好一只朱漆也似的怪物!八足二螯,怒目横眉地卧在盘中,周身裹着浓稠的辣椒酱,间或露出几点雪白的肉来。侍者奉上围嘴、钳子、小锤等物,又端来一盆柠檬水,水上浮着几片柠檬,大约是供食客净手用的。
我一直捧着手机,妹妹大声叫着:“快点吃,就剩下你没吃了!”于是,放下手机,戴上手套,学着邻桌洋人的样子,先掰下一只螯来。螯极硬,用钳子夹了数次才裂开一道缝。雪白的肉嵌在红壳里,蘸了酱汁送入口中,先是甜,继而是辣,最后竟有些酸,三味杂陈,倒也新奇。蟹肉极嫩,与壳的坚硬恰成对照,使人想起某些外强中干的人物。吃着吃着,酱汁已从嘴角流至下巴,忙用围兜去擦。窗外,海水已完全黑了。游艇的灯火在水面拉出长长的金线,忽而被浪打碎,忽而又重新拼凑起来。
点菜前,妹妹告诫过我:“我点菜,你不许说话。”结账时,数目颇令人咋舌。
走出店门,海风依旧,只是多了几分油腻气息。回头望那“珍宝”二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像极了蟹壳上的油光。
当最后一抹余晖拖着星芒的余烬沉入夜色,心中盛满的并非疲惫,而是星火般跳跃的满足。这方寸岛屿上的一日奔袭,竟奇妙地浓缩了狮城精魂,如此丰盛的一日,足够在记忆里酿成一杯恒久回甘的南洋烈酒。
夜色已浓,我们心满意足地相拥告别离开,舌尖的辛辣尚未褪尽,衣襟间仍萦绕着海鲜的鲜香,而眼底已盛满星光。这夜的滋味,将如那颗辣椒蟹钳般,牢牢钳住记忆的味蕾,成为我们共同的南洋印记。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已近上午十点。妹妹在厨房唤我:“姐,快来吃早餐,粥要凉了。”我搁下笔走向她,轻轻给了她一个拥抱。这些天在新加坡的旅程,从行程规划到三餐起居,全赖妹妹悉心照料,实在辛苦。
游记即将收尾,窗外的南洋阳光依旧明媚。这一程,我们不仅收藏了鱼尾狮的喷泉、滨海湾的夜景,更珍藏了姐妹相依的温暖时光。
作者简介
林海燕
林海燕:笔名木子叶寒,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理事、宁波市评论家协会会员、宁海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墩诗社社长。出版个人诗集和散文集6部;合著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春到晴隆》。参与主编纪实采访文学《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主编《宁海市场监管》。
□编辑:海燕文化 □摄影:林迷糊
□题词:储吉旺先生 □LOGO题图尾签设计: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