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peutic approaches for the induction of robust, long-lasting and antigen-specific immune tolerance remains an important unmet clinical ne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autoimmunity, allergy,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gene therapy. Recent breakthrough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immune tolerance mechanisms have opened new research avenues an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in this area. Here, we review mechanisms of immune tolerance and novel methods for its therapeutic induction.
在自身免疫、过敏、器官移植和基因治疗方面,开发治疗方法以诱导稳健、持久和抗原特异性的免疫耐受仍是一项尚未满足的重要临床需求。最近,我们对免疫耐受机制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这一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和治疗机会。在此,我们回顾了免疫耐受的机制及其新的治疗诱导方法。
前言
免疫系统的激活对于控制病原体和癌症至关重要,但也需要调节机制来防止免疫活动过度导致免疫病理。这种平衡的破坏会导致感染、癌症、炎症性疾病或过敏。事实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影响着多达 5-10%的人口,并且呈上升趋势 。同样,无效的免疫调节会导致 20%-70% 的移植受者出现移植物排斥反应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而对病毒载体的原有免疫也会限制基因疗法的疗效。开发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是一项尚未满足的重要临床需求。
我们对免疫耐受及其调控的认识取得了重大进展。事实上,用于抗原发现、给药和细胞靶向的新技术为开发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的疗法开辟了新途径。在此,我们回顾了免疫耐受的机制,并讨论了调节免疫耐受的治疗策略。
免疫耐受机制
免疫耐受是一种对特定抗原无反应的活跃状态,涉及先天性免疫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细胞。自身耐受性的破坏可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而对外来抗原的免疫反应失调则可能导致超敏反应和过敏性疾病。因此,明确其建立和维持所涉及的多种机制非常重要。
中枢耐受
中枢耐受性是在胸腺和骨髓中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发育过程中分别建立起来的。骨髓来源的 CD34+T 细胞祖细胞在胸腺中获得 T 细胞受体 (TCR) 表达。随机的 V(D)J 重排产生了多样化的 TCR 基因库,可对多种抗原产生反应。携带不能识别 MHC 呈递的自身肽的 TCR 的 T 细胞会被忽略而死亡,而对肽-MHC 复合物亲和力低的 T 细胞则会分化成 CD4+或 CD8+单阳性 T 细胞。V(D)J 重排的随机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对自身抗原-MHC 复合物具有高亲和力的 TCR 克隆。高亲和力 TCR 克隆由各种中枢耐受机制控制,包括克隆删除和受体编辑。一些自我反应性 T 细胞逃脱了删除并离开胸腺,但表现出功能障碍和/或表达与耐受性相关的分子,而另一些则发展成自我反应性胸腺分化调节性 T 细胞(tTreg细胞),它们迁移到外周淋巴组织和非淋巴组织。
自身抗原-MHC 复合物由胸腺抗原递呈细胞(APCs)表达,包括特化的胸腺髓质上皮细胞(mTECs)、树突状细胞(DCs)和 B 细胞。转录因子自身免疫调节剂(AIRE)可促进mTECs表达外周组织抗原;AIRE的突变与自身免疫性病理有关。然而,并非所有 mTECs 表达的组织特异性抗原都受 AIRE 控制。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发现,mTECs 可表达 FEZF2 等转录因子,也可从外周细胞类型中共同采用系确定转录因子,称为拟态细胞(mimetic cells)。 这些 AIRE+、FEZF2+ 和拟态 mTECs 与胸腺 B 细胞和 DCs 相互合作,通过克隆 T 细胞删除和Treg细胞诱导促进中枢耐受。组织特异性抗原通过一种被称为合作抗原转移的过程从 mTECs 转移到 DCs,进一步辅助了这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报道称,肠道 DCs 会前往胸腺呈现微生物群衍生的抗原,这凸显了外周 DCs 对中枢耐受性的贡献。
在骨髓中,发育中的 B 细胞会获得 B 细胞抗原受体(BCR)的表达,这种受体会随机重新排列其 V、D 和 J 基因区,从而产生多样化的 BCR 反应谱系。高达 75% 的早期未成熟 B 细胞具有自身反应性,但其中三分之一的 B 细胞会发生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从而降低自身抗原反应性。其他自身反应性 B 细胞会通过克隆性删除而被清除。然而,中枢耐受并不能消除所有自我反应性克隆,例如那些对胸腺或骨髓不表达的发育受限抗原或诱导性抗原有反应的克隆。因此,自我反应性淋巴细胞逃脱了中枢耐受,而受到外周耐受机制的积极控制。
外周耐受
约25–40%的自身反应性T细胞12和约40%的自身反应性B细胞能逃避中枢耐受。因此,外周耐受机制(包括免疫无能、细胞清除及Treg细胞抑制)对于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对胸腺/骨髓外首次接触抗原(如食物过敏原、感染期或妊娠期呈递的抗原)的超敏反应至关重要。
T细胞活化需要三个信号。信号1涉及T细胞受体(TCR)与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的相互作用。信号2涉及共刺激受体与抗原呈递细胞上配体的结合,最常见的是T细胞上的CD28与抗原呈递细胞上的CD80或CD86,但也包括其他共刺激分子,如诱导性T细胞共刺激分子(ICOS)和CD40。信号3涉及细胞因子受体的激活。当TCR信号(信号1)在缺乏共刺激(信号2)的情况下激活,或在信号1和2之前受到强烈的细胞因子预暴露(信号3)时,会诱导T细胞失应性——即T细胞功能失活,无法增殖或产生IL-2。T细胞失能也可由反复抗原刺激、暴露于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或通过程序性死亡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等共抑制受体信号传导诱导。同样,B细胞需同时满足B细胞受体(BCR)结合、Toll样受体(TLR)信号传导或与辅助性T细胞相互作用才能完全激活。在缺乏TLR或辅助性T细胞协同刺激的情况下,BCR与抗原的高亲和力结合会诱导克隆性删除或失应性,从而抑制B细胞增殖及向抗体分泌细胞的分化,并整体缩短B细胞寿命。
长期T细胞失应答与表观遗传修饰相关,这些修饰使细胞对抑制信号更敏感,同时改变基因和表面标志物表达,并诱导类似于慢性感染或癌症中耗竭T细胞的功能变化。然而T细胞和B细胞失应答是动态过程,抗原暴露的消除可恢复其功能。此外,研究发现存在一类天然存在的无应答性T细胞亚群,其表达CD73和FR4,能够分化为功能性FOXP3+ Treg细胞和FOXP3–IL-10+ I型调节性T细胞(TR1),但该过程是否涉及特定抗原呈递细胞类型或解剖学利基尚不明确。
通过凋亡实现的外周T细胞和B细胞清除同样调控着自身反应性细胞。T细胞的内在凋亡主要依赖于促凋亡蛋白BIM——该蛋白在T细胞清除过程中上调,通过抑制抗凋亡蛋白BCL-2和BCL-xL,激活促凋亡蛋白BAX和BAK,从而穿透线粒体膜。T细胞的外源性凋亡涉及FAS或肿瘤坏死因子(TNF)受体信号通路,最终通过激活Caspase诱导凋亡。这些死亡受体的信号传导可限制自身反应性致病性T细胞和B细胞的应答。例如,中枢神经系统(CNS)驻留星形胶质细胞通过表达TNF受体配体TRAIL诱导T细胞凋亡,从而限制自身免疫性神经炎症。其他外周免疫细胞死亡形式(坏死性凋亡、铁死亡和焦亡)也参与维持外周免疫耐受。
在缺乏共刺激的情况下,TCR或BCR激活后自反应性T细胞或B细胞究竟会进入失能状态还是细胞死亡,其决定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假说认为抗原水平调控细胞命运:高水平诱导失应性,低水平则触发细胞死亡。此外,检查点分子信号传导(例如通过PD1、TIGIT、TIM3、LAG3和VISTA)可诱导T细胞死亡或功能障碍。
最后,Treg细胞在周围耐受中发挥核心作用。主要Treg亚群包括FOXP3+细胞和产生IL-10的FOXP3−Treg1细胞,但其他亚群也与免疫耐受相关,包括CD8+Treg细胞、调节性γδT细胞及调节性不变自然杀伤T细胞(iNKT细胞)。
FOXP3+ Treg细胞在胸腺中分化(FOXP3+ tTreg细胞),响应自身抗原表达,随后迁移至外周淋巴组织和非淋巴组织,以限制致病性自身反应并促进组织修复。部分FOXP3+ Treg细胞由外周对照CD4+ T细胞分化而来(FOXP3+ pTreg细胞),可对胸腺未表达的抗原(如食物抗原、过敏原、微生物抗原或妊娠相关胎儿抗原)建立耐受性。此外,皮肤、肌肉、内脏脂肪组织、及黏膜组织(如肠道和肺部)中的组织驻留性Treg细胞具有特异性表型与功能。
TR1细胞是IL-10+FOXP3–CD4+ T细胞,最初是在IL-10存在下经慢性刺激后被描述的。后续研究发现IL-27是更强效的TR1细胞分化诱导因子,同时抗原呈递细胞(APCs)上表达的IFNα、透明质酸、ICOSL、CD2及CD55也发挥关键作用(详见框图1)。FOXP3+ pTreg与TR1细胞的分化及功能受宿主与微生物代谢物调控,例如芳香烃受体(AHR)激动剂。TR1细胞可产生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同时分泌穿孔素和颗粒酶B,后者能杀伤抗原提呈细胞。TR1细胞同时表达抑制分子CTLA4和PD1,实现接触依赖性T细胞抑制,并表达CD39,该分子能降解促炎性细胞外ATP的同时促进抗炎性腺苷生成。
多种细胞类型参与中枢与外周免疫耐受。树突状细胞(DCs)因其处理并呈递抗原,同时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及刺激/抑制分子调控T细胞分化或诱导失能/清除,在免疫耐受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DCs常成为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的治疗靶点。
FOXP3对免疫耐受的调控
免疫系统破坏潜能的有效约束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通过其特有的抑制其他白细胞活化与功能的能力,确保免疫稳态的维持。转录因子FOXP3(Forkhead box protein P3)的表达是Treg细胞公认的特征,该蛋白在Treg细胞表型的建立与维持中发挥核心作用。本文综述了FOXP3的表达与活性如何受到多层次、多因素的调控,并探讨了这些机制在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前言
转录因子叉头框蛋白P3(FOXP3)属于叉头框-翼状螺旋家族转录因子。其作为基因表达广泛调节因子的作用,对最广为人知且研究最深入的免疫调节性T细胞亚群——即CD4+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身份与功能具有核心意义。这类Treg细胞的特征在于其FOXP3的恒定表达,尽管FOXP3表达也可在非Treg细胞激活时短暂诱导。Treg细胞的另一标志性特征是其抑制其他白细胞活化与功能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其维持免疫稳态的作用至关重要。Treg细胞还具有CD25(亦称IL-2Rα,即白细胞介素-2(IL-2)受体的高亲和力链)的恒定高表达特征;这使它们能够从其他细胞来源清除IL-2——这一特性至关重要,因为Treg细胞自身并不产生这种促进生存和扩增的细胞因子。
FOXP3+ Treg细胞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同亚群分布于特定组织并展现独特功能。总体而言,FOXP3+ Treg细胞通过多种成熟机制发挥抑制功能。例如,它们分泌抗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协同抑制分子(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和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蛋白(LAG3)),并能调节抗原呈递细胞(APCs)的活性。Treg细胞还能耗竭微环境中的关键生长因子,从而剥夺效应细胞的营养来源,迫使其因营养匮乏而陷入失应性或凋亡。已知它们会摄取并消耗稀缺氨基酸,同时通过表达胞外酶CD39和CD73促进腺苷核苷酸的积累,这种代谢干扰最终导致效应细胞失应性。此外,研究表明Treg细胞具备细胞毒性潜能,可通过直接杀伤效应细胞实现抑制作用。
这些抑制功能的执行需要Treg细胞内部基因的精确调控,而FOXP3的表达对建立和维持Treg细胞基因表达图谱至关重要。Treg细胞亚群还能够介导多种免疫外功能,包括血管生成(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表达介导)、组织修复以及在整体和T细胞层面的代谢调节。
小鼠和人类FOXP3突变的后果清晰揭示了该转录因子在免疫稳态中的重要性。Scurfy小鼠因Foxp3基因发生2个碱基对插入导致无义突变,其表达截短的基因产物。这类小鼠的Treg细胞丧失抑制功能,无法约束过度活化的T细胞及其产生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在人类中,FOXP3基因突变会导致致命的X连锁免疫失调多内分泌病肠病综合征(IPEX)。患有这种遗传性疾病的患者在出生后数月内会出现多种免疫病理症状,包括皮炎、肠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因内分泌腺功能障碍)和贫血。
FOXP3介导的基因调控
FOXP3能够结合超过2,800个基因组位点,这对应于发育中及成熟的Treg细胞中约700至1,400个基因。通过调控这些靶位点,FOXP3在功能上协同或可能强化了Treg细胞发育过程中由T细胞受体(TCR)刺激引发的表观遗传编程所形成的基因表达模式。尽管FOXP3对Treg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至关重要,其具体作用机制至今才逐渐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FOXP3直接结合的基因数量仅占其已知调控基因的极小比例(约6–10%)。因此认为FOXP3可通过与多种共因子相互作用,间接正负调控众多靶基因的转录活性。FOXP3与其结合伙伴形成一个庞大的蛋白质复合体,其分子量达400-800 kDa(甚至更大),涉及超过360种不同因子,其中部分为其他转录因子或染色质修饰因子。转录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和Runt相关转录因子1(RUNX1,亦称AML1)可结合FOXP3调控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已有研究证实这些因子与FOXP3存在相互作用,且破坏该相互作用会导致Treg细胞功能减弱。此外,干扰素调节因子4(IRF4)也被证实是与FOXP3具有重要协同作用的另一分子。IRF4通过与FOXP3相互作用,使其获得选择性调控Treg细胞基因表达特征(约20%)的能力。这些基因显然编码了控制T辅助细胞2型(TH2)反应的关键因子,因为IRF4缺陷型Treg细胞的小鼠在抑制TH2型细胞因子IL-4和IL-5产生方面存在选择性缺陷。此外,在小鼠关节炎模型中,IRF4与FOXP3的增强相互作用与对TH17细胞介导炎症的更强抑制能力相关。已知FOXP3通过与FOS-JUN复合物竞争结合NFAT17,促进Treg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此外,FOXP3还与转录因子GATA3、REL和RORγt相互作用,且很可能与其他转录因子也存在交互作用。
FOXP3的表观遗传调控与协同因子招募机制 FOXP3对基因的选择性激活或抑制,取决于其在靶位点促进表观遗传重塑的能力。例如,FOXP3与编码IL-2和IFNγ的基因结合后,会导致组蛋白H3去乙酰化——这种修饰可沉默基因表达。相反地,FOXP3通过在基因启动子区域诱导组蛋白乙酰化,促进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GITR,亦称TNFRSF18)、CD25及CTLA4的表达。FOXP3作为Treg细胞遗传景观表观遗传塑造者的核心作用,在于其已被广泛认可的与介导表观遗传修饰的分子结合的能力。这些相互作用伙伴通过改变靶位点甲基化状态影响转录因子结合,同时执行组蛋白修饰。FOXP3关联组蛋白乙酰转移酶——60 kDa Tat相互作用蛋白(TIP60,亦称KAT5)、p300及组蛋白去乙酰酶7(HDAC7)——即属此类。
Ikaros家族成员EOS是另一种关键协同因子,能将表观遗传修饰因子招募至FOXP3调控位点。该因子在Treg细胞中高度表达,对FOXP3抑制Il2等基因至关重要。EOS招募羧基末端结合蛋白1(CTBP1)及组蛋白赖氨酸N-甲基转移酶EHMT2(又称EuHMT2)等因子至Il2基因座。该机制通过抑制组蛋白H3K4三甲基化及组蛋白H3/H4乙酰化,同时促进组蛋白H3K9甲基化及Il2启动子区域CpG二核苷酸甲基化实现。EOS通过参与抑制复合体的构建,可促进FOXP3对靶基因的表观遗传沉默。
一组FOXP3协同因子(EOS、IRF4、SATB1、淋巴样增强子结合因子1(LEF1)和GATA1)协助FOXP3强化Treg细胞基因表达特征。这些协同因子在促进FOXP3调控作用方面似乎具有冗余功能,因单一因子的缺失可被其他因子的活性所补偿。这种功能重叠可能使FOXP3在Treg细胞中调控基因表达的能力具有相当强的韧性。然而,该网络在成熟Treg细胞中的冗余程度尚待确定。某些协同调控因子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对特定Treg细胞功能具有必要性。
FOXP3与其协同调节因子间相互作用改变的后果,在表达氨基端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GFP)-FOXP3融合蛋白的报告小鼠(Foxp3tm2Ayr小鼠)中得到了清晰验证。由于N端结构域对FOXP3与多种共因子相互作用至关重要,GFP标签的存在破坏了FOXP3与其多个共调节因子(包括TIP60、p300及EOS)的结合。尽管Foxp3tm2Ayr小鼠未表现出明显自身免疫症状,其Treg细胞却呈现病理特异性功能改变。例如,该背景下的非肥胖糖尿病(NOD)小鼠比野生型NOD小鼠更早发病,因其Treg细胞表达的功能性降低的FOXP3分子。然而有趣的是,表达这种GFP-FOXP3融合蛋白的Treg细胞对抗体介导性关节炎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源于融合蛋白与IRF4之间的优先结合。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特定共因子对Treg细胞介导的免疫调控至关重要,还表明Treg细胞可通过优化FOXP3功能复合体的组成成分,实现对特定炎症类型的精准抑制。
另一种FOXP3相互作用伙伴兼染色质修饰因子是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增强子同源物2(EZH2),该蛋白是多梳抑制复合体2的组成部分。EZH2可在Treg细胞中响应CD28信号而上调。FOXP3与EZH2在活化的Treg细胞中优先形成复合物,这些复合物能在炎症条件下及活化过程中稳定Treg细胞的基因表达。缺乏EZH2的活化Treg细胞表现出FOXP3表达水平不稳定及多基因去抑制现象。总体而言,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FOXP3某些相互作用伙伴在Treg细胞生命周期及异质性FOXP3+ Treg亚群中具有阶段特异性和功能特异性的作用。
FOXP3基因的调控
人类FOXP3基因定位于X染色体的短臂,这一定位通过IPEX综合征的遗传模式得到了明确验证。该基因包含11个外显子,人类与小鼠基因之间存在高度保守性,尤其在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处。当T细胞受体(TCR)信号与共刺激通路激活时,FOXP3启动子会被NFAT和AP-1等转录因子结合并激活。此外,研究证实FOXO1和FOXO3蛋白可结合Foxp3启动子及其他调控元件,而环磷酸腺苷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激活转录因子1(ATF1)复合物同样驱动FOXP3启动子激活(图1)。值得注意的是,FOXP3基因启动子被鉴定为具有较低的转激活潜力。相反,该重要基因座的转录高度依赖于保守增强子区域的贡献。
FOXP3转录的启动与维持高度依赖关键保守非编码序列(CNSs),这些序列作为多种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发挥作用(图1)。CNS3位于Foxp3基因外显子1与外显子2之间,该区域促进Foxp3启动子处允许性组蛋白修饰的积累,使其在成熟FOXP3+细胞及FOXP3−调节性T细胞前体中均保持表观遗传平衡状态。因此,CNS3作为表观遗传开关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响应REL蛋白的结合来调控这些细胞中的Foxp3转录——REL是胸腺中Treg细胞发育的关键调控因子。然而,尽管CNS3对启动Foxp3表达不可或缺,但似乎并非维持其表达所必需。
相对地,CNS2(亦称Treg细胞特异性去甲基化区)对维持胸腺来源Treg细胞(tTreg)在胸腺外周环境中的FOXP3表达至关重要。该区域位于Foxp3基因首个内含子内,其CpG元件在tTreg细胞发育过程中发生广泛去甲基化。CNS2区及其他FOXP3基因调控元件中的去甲基化CpG主题,可结合多种转录因子,包括REL、CREB-ATF1、RUNX1-核心结合因子β亚基(CBFβ)、ETS1、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5(STAT5)以及FOXP3本身。这种表观遗传状态的维持使tTreg细胞能在包括组织炎症在内的多种条件下稳定表达FOXP3。体外诱导的Treg细胞(iTreg)在FOXP3表达和抑制活性方面不如tTreg细胞稳定,其CNS2区域呈甲基化或部分去甲基化状态。相比之下,外周来源的pTreg细胞通常具有与tTreg细胞相似的表观遗传特征,且被认为具有功能稳定性。
甲基CpG结合域蛋白2(MBD2)通过结合CNS2区域招募十-十一转位(TET)去甲基酶,维持该区域的低甲基化状态(图1)。在小鼠中消除MBD2功能会导致Treg细胞数量减少,且残留Treg细胞的抑制活性降低。这些现象与MBD2缺失的Treg细胞在胸腺外周化后无法维持CNS2低甲基化状态相关。相反,DNA甲基转移酶1(DNMT1)已知会促进CNS2位点的甲基化事件。该酶及类似因子可能对抗调控tTreg细胞活性的表观遗传编程。最新研究证实促炎细胞因子IL-6可触发Treg细胞中DNMT1依赖性CNS2序列甲基化,而IL-2或维生素C则能激活TET酶维持CNS2低甲基化状态(图1,2)。IL-6暴露还会降低上游启动子处组蛋白H3的乙酰化水平,从而损害FOXP3转录。相反,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通路通过抑制DNMT1表达,与FOXP3表达的表观遗传稳定性相关。
CNS1增强子对T细胞中胸腺外FOXP3表达的诱导尤为关键。与CNS2相似,CNS1位于内含子区域,但其独特性在于必须参与TGFβ诱导的SMAD信号通路以激活FOXP3表达。激活的SMAD3与CNS1的结合是pTreg细胞分化过程中诱导FOXP3表达的关键事件,但对tTreg细胞则不然36。因此,CNS1缺失小鼠的pTreg细胞群功能缺陷,无法在肠道等屏障部位维持免疫耐受,但这些小鼠并未发生自身免疫。进化记录显示CNS1的出现与胎盘哺乳动物的出现同步,这强烈暗示在非Treg细胞前体中诱导FOXP3表达的能力,可能是维持妊娠期间母体对半同源胎儿耐受性的关键。
FOXP3 基因转录机制。在tTreg细胞前体中,TCR刺激触发核因子-κB(NF-κB)家族成员(如REL)的激活。这些因子结合FOXP3基因恒定“开放”的CNS3增强子,从而启动转录。缺乏该通路关键介质(如蛋白激酶Cθ(PKCθ)、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10(BCL-10)、含CARD结构域的MAGUK蛋白1(CARMA1;亦称CARD11)、 TGFβ激活激酶1(TAK1;又称MAP3K7)、IκB激酶2(IKK2;又称IKKβ)和REL)的小鼠模型,其胸腺Treg细胞产量显著降低。TCR信号传导与CD28介导的协同刺激通路对Treg细胞的正常发育和维持至关重要,该信号通路同时激活RAS-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该通路对启动FOXP3转录具有关键作用。这些信号级联最终招募大量转录因子至FOXP3基因的启动子和调控元件区域。
细胞因子的作用 IL-2受体信号触发Janus激酶(JAKs)激活,进而介导STAT5磷酸化。活化的STAT5结合FOXP3启动子及CNS2元件,驱动Treg细胞中该基因座的有效转录。缺乏STAT5或JAK3的小鼠其Treg细胞频率显著 lower 野生型对照组。相反,恒定性STAT5活性可挽救Treg细胞池免受IL-2剥夺的负面影响。已知IL-2在稳定Foxp3表达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IL-2受体亚单位CD25的高表达已被证实与Treg细胞中高度稳定的FOXP3表达及强效抑制功能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促炎细胞因子IL-6可通过招募DNMT1触发CNS2甲基化从而抑制Foxp3转录,而IL-2则能通过招募去甲基化TET酶阻止此过程。IL-6及其他炎症细胞因子(如IL-21)诱导的STAT3激活,亦可通过阻断IL-2激活的STAT5与Foxp3基因元件的结合来抑制Foxp3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促炎细胞因子TNF在某些情况下虽会拮抗Treg细胞功能,却也能支持部分Treg亚群通过STAT5介导的扩增。针对TNF作用下Treg细胞内稳定与失稳信号通路的潜在交互作用,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TGFβ在胸腺外来源的pTreg细胞发育中具有特殊重要性。TGFβ触发的SMAD激活会导致SMAD3-SMAD4异源二聚体与Foxp3基因中的CNS1结合。这一分子事件对诱导对照CD4+ T细胞表达Foxp3至关重要,从而促进其在周围组织及in vitro环境中获得Treg细胞表型。TGFβ可能也参与tTreg细胞的发育。尽管部分研究表明TGFβ并非tTreg细胞生成必需,但另有研究指出该细胞因子可在发育过程中促进tTreg细胞存活,且不直接影响FOXP3表达。持续暴露于TGFβ可防止iTreg细胞中FOXP3表达丢失,但TGFβ在tTreg细胞中是否具有类似稳定作用尚不明确。
维生素A代谢物全反式视黄酸(ATRA)长期以来被证实能促进iTreg细胞从对照CD4+ T细胞前体分化(图2)。这可能源于ATRA能增强TGFβ驱动的SMAD3磷酸化,或抑制干扰Foxp3上调的炎症细胞因子信号通路。此外,ATRA可通过在Treg细胞前体中诱导FOXP3基因座的组蛋白H4乙酰化,影响FOXP3基因转录。已有研究表明,CNS2区域的表观遗传修饰及FOXP3染色质结合能力的增强,可提升ATRA处理后Treg细胞的功能稳定性。此外,ATRA通过增强对Treg细胞破坏性细胞因子IL-6的抵抗力,可能在体内维持tTreg细胞的稳定性。
FOXP3转录本的加工。在人类中,FOXP3转录本可通过可变剪接形成多种变体亚型,这对编码转录因子的调控活性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TCR和协同刺激分子激活Treg细胞可显著改变其FOXP3剪接变体的产生。从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来源cDNA克隆的FOXP3异构体包括:FOXP3Δ2(缺失外显子2编码区域); FOXP3Δ7(缺失外显子7及亮氨酸拉链结构域);以及FOXP3Δ2Δ7(同时缺失外显子2和7)。全长FOXP3可抑制RORα、NF-κB和NFAT介导的基因表达,而FOXP3Δ2和FOXP3Δ2Δ7对这些炎症性转录因子的抑制作用显著减弱。转染研究表明,在T细胞中强制表达全长FOXP3可抑制其增殖。尽管缺失外显子7的变体构建体在二聚体形成方面存在缺陷,但其产生的FOXP3分子仍能完全抑制T细胞活化。事实上,与转染全长FOXP3的对照T细胞相比,FOXP3Δ2或FOXP3Δ2Δ7转染的T细胞表现出相似的激活动力学,以及CD25水平的类似上调和CD127水平的类似下调。这些发现表明,这些剪接变体仍能诱导Treg细胞程序的部分特征。研究还表明,FOXP3Δ2的过表达与全长FOXP3类似,可在体外赋予抑制其他T细胞功能的能力。然而另一项研究发现,FOXP3Δ7在克罗恩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普遍表达,且强制表达FOXP3Δ2Δ7反而能促进处于TH17与iTreg双重命运之间的近期激活FOXP3+CD4+ T细胞向TH17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克罗恩病患者体内促进炎症反应的剪接事件与IL-1β暴露相关——该因子被证实会破坏Treg细胞功能。目前尚不清楚这种IL-1β诱导的FOXP3剪接变体相较于全长蛋白在功能上存在何种缺陷。然而,这种FOXP3转录本加工的改变与免疫耐受性维持不佳相关。这些发现表明,FOXP3的不同同工型可能影响Treg细胞在体内的分化或功能。但目前尚不清楚单个Treg细胞是仅表达一种同工型,还是同时表达多种FOXP3同工型。随着各同工型的特性逐渐明朗,它们可能各自具有独特功能。此外,将小鼠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疾病时,需注意剪接变体仅存在于人类而非小鼠这一事实。
FOXP3的结构域。 FOXP3蛋白包含三个功能关键结构域:N端结构域、含锌指和亮氨酸拉链的区域,以及C端叉头结构域。所有结构域对FOXP3+ Treg细胞的正常功能均不可或缺,任何结构域的突变都可能导致scurfy或IPEX自身免疫表型。叉头结构域对DNA结合、FOXP3-NFAT相互作用及FOXP3分子同源二聚化至关重要,并负责抑制多个免疫相关靶基因的转录。值得注意的是,该结构域缺失后部分FOXP3功能仍得以保留,这一现象表明Treg细胞基因表达的调控高度依赖于FOXP3与DNA结合协同分子的相互作用。N端结构域同样具备抑制靶基因转录的能力(故被称为“抑制域”),但其不具备DNA结合能力。包括EOS和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内的多种蛋白质通过N端结构域与FOXP3发生相互作用。此外,包含HDAC7或HDAC9及TIP60的染色质重塑复合体被证实与该蛋白区域相互作用,表明其在构建“FOXP3相互作用组”中具有关键作用——即FOXP3与众多协同调控分子形成的复合体,这些分子在促进FOXP3诱导的基因调控过程中具有协同且可能冗余的作用。外显子2编码的序列还被证实可与RORγt和RORα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被发现对于抑制这些转录因子的活性至关重要,并能促进从对照CD4+ T细胞中产生Treg细胞而非TH17细胞。此外,亮氨酸拉链结构域和锌指结构域对FOXP3的同源二聚化至关重要,而该二聚化过程是其功能不可或缺的环节。最后,FOXP3蛋白内的特定位点被证实决定着该转录因子的细胞定位模式——在Treg细胞中,这些位点或确保或阻碍其典型的核定位。
DCs作为免疫耐受的核心调节者
DC细胞亚群及其功能
树突状细胞(DCs)表现出表型和功能上的异质性。DCs可分为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s)、经典(或常规)Ⅰ型树突状细胞(cDC1s)和Ⅱ型树突状细胞(cDC2s)。此外,单核细胞衍生的DC(moDCs),有时被称为TipDCs(TNF和iNOS双阳性DC),在炎症条件下会呈现DC样表型,但近期研究对其向淋巴结迁移并激活CD4+和CD8+ T细胞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人类还发现了一种兼具cDC2和moDC特征的DC3亚型。DC亚群内部存在更多异质性:例如cDC2可分为分别受转录因子T-bet和RORγt调控的cDC2A与cDC2B;此外CD103和CD11b可区分黏膜组织中的功能性cDC亚群。
树突状细胞主要分布于血液和淋巴组织,但在炎症期间会迁移至非淋巴组织。当主要通过TLR7或TLR9信号通路激活时,树突状细胞会产生大量I型干扰素,包括IFNα和IFNβ。在稳态条件下,树突状细胞对对照CD4+和CD8+ T细胞的激活作用较弱。然而,在感染期间,pDCs的一个亚群可刺激CD4+辅助T细胞1(TH1)细胞。pDCs还通过表达ICOSL、TGFβ和抑制性吲哚胺2,3-二氧合酶(IDO)促进耐受性及Treg细胞诱导。事实上,最新研究表明,pDC缺陷会导致器官移植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且pDC参与诱导口腔耐受性。
在稳态条件下,cDCs存在于淋巴组织和非淋巴组织中。cDC1和cDC2在不同组织中的分布存在差异,尽管两类亚群均可在组织与淋巴结间迁移,但cDC2似乎具有更强的迁移能力,并在肺、肠等黏膜相关部位富集。值得注意的是,在稳态条件下,cDC1、cDC2和pDC均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脉络丛及脑膜中,但在脑实质和血管周围间隙几乎无法检测到。事实上,cDC1是脉络丛的主要亚型,而cDC2在软脑膜和硬脑膜中最为丰富。在炎症状态下,cDC1、cDC2、moDC和pDC会浸润脑实质,并向T细胞呈递中枢神经系统特异性抗原。尽管cDC1和cDC2均能向CD4+或CD8+ T细胞呈递抗原,但cDC1在抗原交叉呈递和III型干扰素产生方面更具优势。在cDC2亚群中,cDC2A似乎比cDC2B具有较弱的促炎性,其表达更高水平的双向调节蛋白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而cDC2B则产生更高水平的TNF和IL-6。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中的cDC2已被证实能促进T辅助17(TH17)细胞分化。然而研究同时表明,cDC1和cDC2均能促进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和IL-10+调节性T细胞(TR1)的分化。
耐受性树突状细胞表型
树突状细胞(DCs)的激活与成熟状态决定其对免疫应答的影响。在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s)激活前,DCs以未成熟状态存在于黏膜部位、淋巴组织、外周组织或血液中。当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激活DC时,会上调其MHC I类和II类分子、共刺激分子及黏附分子(如CC趋化因子受体7,CCR7)的表达。这些成熟的DC迁移至淋巴组织促进效应T细胞分化。相反,未成熟DC表现出低水平的MHC I类、MHC II类及共刺激分子表达,能够诱导T细胞失应性、Treg细胞分化及效应T细胞清除。最初假设耐受性DC本质上是未成熟DC,但该范式早年即遭质疑。后续研究提出特定刺激可诱导耐受性DC表型,且耐受性DC会经历某种程度的成熟和/或活化。事实上,DC特异性转录程序决定其免疫原性或耐受性状态。例如稳态条件下β-catenin信号通路或吞噬凋亡物质可激活DC耐受性程序,促使DC迁移至淋巴结呈递自身抗原并维持外周耐受。此外,半成熟和成熟DC亦可诱导耐受性表型。例如,在人类外周血和脾脏中鉴定出IL-10+ DC-10亚型,其表达cDC和moDC表面标志物,但能诱导CD4+ T细胞低反应性和TR1细胞扩增; DC-10可在体外通过单核细胞在IL-10存在下的分化过程诱导产生。此外,肠道CD103⁺树突状细胞参与饮食抗原耐受性及口服耐受性的诱导。无论其起源与成熟状态如何,DC均通过多重机制参与免疫调节:包括下调共刺激分子(CD80、CD86和CD40)、表达抑制分子(PD-L1、ICOSL和BTLA)、抑制促炎细胞因子(IL-6、 IL-12、IL-23和TNF)以及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TGFβ和IL-27)和代谢物(IDO、视黄酸和乳酸)的产生(图1)。
多种刺激可诱导DC呈现耐受性表型。例如,IL-10能降低DC的MHC及共刺激分子表达,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产生,并促进T细胞失应答及Treg细胞扩增。IL-10对DC的这些抗炎效应依赖于芳香烃受体(AHR),这与先前关于AHR信号在DC中具有耐受性效应的报道相呼应。其他细胞因子如TGFβ、IL-27和IL-37同样能促进抗炎性DC表型。类似地,单核细胞或骨髓细胞暴露于低浓度的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可诱导具有耐受性表型的DC分化,而暴露于较高剂量的GM-CSF则诱导促炎性DC表型。此外,共生菌通过特定PRR(如TLR2)的信号传导可促进耐受性DC的诱导。事实上,某些微生物代谢物可通过激活芳香烃受体(AHR)诱导耐受性DC。具体而言,芳香烃受体激动剂可抑制DC中核因子-κB(NF-κB)的活化,驱动IL-10和IDO的表达,同时降低MHC分子、共刺激分子及IL-6、IL-12等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这些变化导致DC中FOXP3+和IL-10+调节性T细胞(Treg)增加,同时抑制Th1、Th17及CD8+效应T细胞。
其他诱导耐受性DC表型的因子包括维生素A(其代谢产物视黄酸可增强FOXP3+ Treg细胞诱导)及维生素D3(后者可增加IL-10分泌,同时降低IL-12和共刺激分子表达)。此外,由微生物群、活化DC或其他免疫细胞产生的乳酸,通过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驱动的NADH脱氢酶NDUFA4L2表达增加来调节DC功能,最终限制效应T细胞活化。
最后,摄取凋亡细胞可通过激活芳香烃受体(AHR)、合成前列腺素E2及经由MARCO等清道夫受体信号传导等机制诱导DC呈现耐受性表型。事实上,无论经典DC(cDCs)还是浆细胞样DC(pDCs),在摄取凋亡细胞后均会表达IL-10、降低共刺激分子表达并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增殖。
这些与耐受性DC表型相关的通路及其他机制,为开发治疗性免疫调节策略提供了机遇,具体将在下文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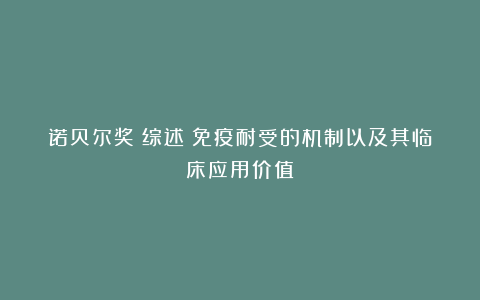
抗原特异性治疗策略以诱导免疫耐受
当前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排斥反应及其他由免疫反应失调引发的病理状况的治疗手段,主要依赖非靶向性免疫抑制,因而伴随显著副作用。因此亟需开发新型方法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既能靶向异常活化的T细胞,又不干扰针对病原体和癌症的保护性免疫。基于此,已开发出多种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的技术(图2与表1)。下文将探讨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器官移植及基因治疗领域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的策略(图3)。
基于细胞的耐受性治疗
通过识别诱导树突状细胞(DCs)产生耐受表型的刺激因子,指导了细胞治疗方法的发展。这类方法通常基于体外从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制备的DCs,并负载与疾病相关的抗原。然而,目前尚未建立标准化方法来体外制备耐受性DCs,研究人员已探索了多种操作方案和耐受性分子。例如,在低浓度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存在下体外分化的单核细胞来源树突状细胞(moDCs),即自体耐受性树突状细胞(ATDCs),表现出未成熟表型:MHC II类分子、CD80、CD86和CD40低表达,同时高产IL-10和乳酸。ATDCs在预防肾移植后排斥反应的I/IIA期临床试验中耐受性良好,需进一步试验评估其临床疗效。类似地,IL-10诱导的DC-10s负载疾病特异性抗原可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其临床疗效尚待评估。
维生素D3亦可在体外诱导耐受性树突状细胞表型。经自体维生素D3处理的耐受性树突状细胞负载疾病特异性抗原,已在I期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包括针对1型糖尿病(T1D)及多发性硬化症(MS)的研究(表2)。此外,在维生素D3和IL-10存在下分化的单核细胞来源树突状细胞(moDCs)被证实具有耐受性,并在非人灵长类异体免疫反应模型中诱导产生IL-10的T细胞。类似地,经地塞米松处理的moDCs呈现耐受性表型,特征为高水平分泌IL-10和TGFβ,同时低水平产生促炎性细胞因子。在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及视神经脊髓炎的I期临床试验中,经地塞米松诱导的耐受性树突状细胞负载疾病特异性肽后表现出良好耐受性。此外,克罗恩病I期试验中已测试了经地塞米松与维生素A联合诱导的耐受性树突状细胞。
另一种方法是体外将抗原与淋巴细胞和红细胞结合,以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性。该方法被认为是通过抗原结合细胞的凋亡及其随后被抗原呈递细胞(APCs)摄取来诱导耐受性,这些APCs在摄取凋亡细胞后获得耐受性表型。例如Watkins等人的研究中,抗原结合红细胞被BATF3+ cDC1s吞噬,通过PD1、CTLA4、LAG3和TOX表达诱导抗原特异性T细胞功能障碍。基于这些发现,Raposo等人开发出微流控加载技术制备抗原负载红细胞,可减少效应T细胞向靶器官的迁移。此外,抗原负载红细胞诱导旁观者耐受性,既抑制效应T细胞对红细胞内抗原的反应,也抑制对同组织内其他抗原的反应。旁观者耐受诱导对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多数自身免疫性疾病涉及多种抗原(其中许多未知),且不同患者可能针对不同抗原。
由于FOXP3+ Treg细胞或TR1细胞具有向炎症组织迁移、抑制致病性T细胞及促进组织修复的能力,多种耐受诱导策略均依赖于此类细胞。事实上,已有超过25项临床试验在1型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克罗恩病、器官移植及移植物抗宿主病领域测试了基于Treg细胞的疗法(表2)。这些疗法通常涉及从外周血中分离的自体多克隆Treg细胞,并在IL-2存在下体外扩增。Treg细胞疗法耐受性良好,且Treg细胞在体内具有稳定性。一项临床试验显示,体外扩增的自体多克隆Treg细胞在移植患者体内1年后仍有25%可被检测到,表明这些细胞具有惊人的长半衰期。然而,尽管多项研究在I期及I/II期试验中初步证实了Treg细胞疗法的临床疗效,仍需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此外,针对非特异性免疫抑制的担忧促使抗原特异性Treg细胞疗法应运而生。
基于Treg细胞的治疗策略进一步发展为构建嵌合抗原受体(CAR)修饰的Treg细胞。研究表明CAR Treg细胞可改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及其他免疫介导性疾病,且靶向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的CAR Treg细胞能在多发性硬化症(MS)小鼠模型中定向迁移至中枢神经系统(CNS)。近期针对TNF等促炎分子进行基因改造的Treg细胞,在GVHD小鼠模型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结果,这在病理驱动抗原不明或需同时靶向多种抗原的场景中具有应用价值。类似地,靶向B细胞的CAR Treg细胞在A型血友病小鼠模型中抑制了抗体反应,彰显了工程化T细胞疗法的多功能性。值得注意的是,CAR Treg细胞在高度促炎环境中仍能保持耐受性,缓解了其可能转化为致病效应T细胞的担忧。研究还证实CAR Treg细胞可诱导旁观者耐受性。
广泛应用细胞疗法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涉及临床环境中患者特异性细胞制备问题。基于基因编辑干细胞的策略或可突破部分瓶颈——通过生产通用型现成细胞系,实现对多例患者的耐受诱导。
基于合成粒子的递送系统
纳米颗粒为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方法。作为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的理想平台,纳米颗粒具有三大优势:无需依赖患者来源细胞、采用安全可生物降解材料制备、且可实现大规模生产且批次间差异极小。此外,纳米颗粒可定向靶向特定目标细胞并递送多种有效载荷,同时能提升小分子药物与抗原的溶解度及生物利用度。目前已有多种类型的纳米颗粒应用于免疫调节,包括金属、聚合物、脂质基及肽-聚合物纳米颗粒,各具优势与局限(图2)。
金属纳米颗粒(如金、银和氧化铁颗粒)可同时用于诊断与治疗,例如作为增强造影剂及表面偶联载体的递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与MHC II类分子结合肽偶联的氧化铁纳米颗粒能诱导TR1细胞,进而激活调节性B细胞并抑制多种小鼠前临床模型的炎症反应。在此机制中,TR1细胞的诱导依赖于纳米颗粒中高密度的MHC分子,这些分子在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上诱导出缺乏共刺激分子的TCR微聚集体。此外,肝脏中的调节性B细胞和T细胞可诱导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细胞,从而抑制肝脏自身免疫和纤维化。金属纳米颗粒可通过修饰提升性能,但改性后颗粒可能不稳定。事实上,表面偶联会导致金属纳米颗粒在生产过程中易于聚集,从而限制可载入的药物类型并干扰规模化生产。此外,金属颗粒不易生物降解,其在组织中的积累可能引发不良反应。
相反,由碳水化合物酸制成的聚合物颗粒(如聚乳酸(PLA)和聚乳酸-共-羟基乙酸(PLGA)纳米颗粒)具有易于修饰、制造相对简单且降解迅速的优势,尽管某些副产物会诱发不良反应。在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RA)和1型糖尿病的临床前自身免疫疾病模型中,递送疾病特异性抗原的聚合物颗粒通过诱导CTLA4+PD1+调节性T细胞、减少效应T细胞以及降低IL-12、microRNA-155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展现出治疗效果。此外,针对乳糜泻的I期和IIa期临床试验表明,包裹麦胶蛋白抗原的PLGA微粒耐受性良好,可降低麦胶蛋白特异性IFNγ产生及效应记忆T细胞。但需进一步试验以全面评估其疗效。值得注意的是,PLGA微粒展现出与载荷无关的特定情境下抗炎与促炎双重效应. 事实上,PLA和PLGA颗粒的主要降解产物之一是左旋乳酸,其通过激活HIF1α和抑制NF-κB通路抑制树突状细胞成熟及促炎反应。相反地,PLGA微粒可在DC中激活含NBD、LRR及嘌呤域的蛋白3(NLRP3)炎症小体,并使巨噬细胞向促炎表型极化。另有研究表明PLGA微粒可诱导效应性CD8+ T细胞活化及IFNγ分泌,同时兼具TH2细胞佐剂功能。
脂质基纳米颗粒广泛应用于化妆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癌症治疗及mRNA冠状病毒疫苗。根据制备方法和配方物理化学特性,脂质纳米颗粒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脂质体、脂质纳米颗粒和立方体脂质体。由于脂肪酸的两亲性,脂质纳米颗粒可在膜内嵌入疏水性分子,同时在水相核心携带亲水性物质或将其共价结合于表面。此外,脂质可经工程改造实现易降解特性。更进一步,通过引入二油酰磷脂酰乙醇胺或胆固醇等脂质,可调节纳米脂质体的融合活性,从而优化内体药物释放。事实上,细胞内胆固醇积累可通过激活肝X受体诱导树突状细胞耐受性。脂质纳米颗粒已成功用于递送自身抗原,在1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和重症肌无力的多种临床前模型中均展现出治疗效果,其机制与诱导耐受性树突状细胞、调节性T细胞扩增及抑制致病效应T细胞相关。此外,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Ib期临床试验中,同时封装胶原蛋白肽和NF-κB抑制剂的脂质体耐受性良好,可诱导循环中胶原特异性PD1+ T细胞增加并降低疾病活动度。
蛋白质基纳米颗粒提供可生物降解、无毒且稳定的递送平台,但因其与病毒颗粒的结构相似性而具有高度免疫原性,故鲜少用于抗原特异性耐受诱导。
纳米粒子的物理化学特性(包括尺寸、电荷、结构、疏水性及刚性)影响其免疫调节效应,可通过修饰改变纳米粒子的循环特性、细胞靶向性、摄取效率及免疫调节功能,从而最大化治疗活性。总体而言,纳米颗粒表面电荷是决定细胞摄取与免疫调节的关键因素。负电荷纳米颗粒被认为可模拟耐受性凋亡细胞,并通过巨噬细胞中的MARCO等清道夫受体优先被吞噬细胞摄取。相反,带正电纳米颗粒被认为能直接与带负电的细胞膜相互作用,从而被更多类型的细胞更快摄取,但这种特性也可能增加破坏脂质双层结构的风险并引发细胞毒性。带正电纳米颗粒还能通过上调CD80和CD86表达及产生活性氧,促进炎症反应。然而,关于粒子电荷对摄取、毒性和炎症影响的普遍共识尚未形成。
颗粒尺寸同样影响生物分布、靶向性、摄取及毒性。通常小于200纳米的颗粒被树突状细胞摄取,大于500纳米的则被巨噬细胞摄取。研究表明抗原尺寸可调控免疫应答,促进Th1、Th2或Treg细胞的诱导。此外,颗粒尺寸与刚性会影响免疫应答,使DCs和巨噬细胞向促炎或抗炎表型偏移。聚乙二醇常作为屏蔽剂使用,可减少与血清蛋白的相互作用,降低网状内皮系统的摄取,延长循环时间并提高生物利用度。将聚乙二醇链连接至蛋白质上对促进皮下摄取、减少补体激活及粒细胞招募也至关重要。最后需注意,基础研究中的制备工艺常与FDA批准疗法的生产工艺存在差异。因此在纳米颗粒生产规模化转为临床试验时,其电荷、尺寸等特性可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免疫调节活性。
特定细胞类型的靶向作用
大多数非靶向纳米颗粒通过清道夫受体和补体因子结合被树突状细胞(DCs)和巨噬细胞摄取。这种对DCs的被动靶向通常导致纳米颗粒递送的抗原在MHC II类分子上呈递。在缺乏共刺激分子的情况下,CD4+ T细胞识别MHC II类分子呈递的抗原会诱导克隆性T细胞清除,并通过PD-L1介导抑制作用,同时诱导FOXP3+和IL-10+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
纳米颗粒也可通过抗体或其他与特定细胞群反应的分子实现定向递送(表1)。例如,甘露糖基化抗原靶向DC中的甘露糖受体,诱导IL-10产生并建立抗原特异性耐受性。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I期临床试验中,包裹髓鞘肽抗原的甘露糖基化脂质体可降低血液中促炎细胞因子水平,但其治疗价值尚不明确。
另一种策略是基于靶向细胞中免疫受体的抗原特异性来设计纳米颗粒。例如,在缺乏信号分子2和3的情况下,展示重组MHC I类分子载入肽段的金属纳米颗粒可诱导抗原特异性CD8+效应T细胞失活及记忆样调节表型,通过IFNγ、IDO和穿孔素抑制DC。因此,基于表面分子表达或抗原反应性将纳米颗粒定向递送至特定免疫细胞,是靶向免疫治疗的理想策略。然而,在治疗性纳米颗粒中添加额外组分(如表面抗体)可能干扰其制备工艺。
将免疫抑制剂引入纳米颗粒
免疫调节的主要风险在于可能加剧病理性免疫反应。事实上,在测试免疫调节方法时,已记录了从局部反应到过敏性休克乃至致死的各种不良反应;临床试验因诱发过敏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复发而被迫中断。这些不良反应表明,安全的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需要激活耐受性通路。近期关于抗原-MHCⅡ类复合物评估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该复合物在三分之一受试小鼠中诱发炎症反应;而通过将地塞米松接枝至抗原-MHCⅡ类复合物,仅需200分之一的剂量(相较于单独地塞米松治疗方案)即可消除这种促炎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采用纳米颗粒和纳米脂质体递送自身抗原似乎不会诱发或增强促炎反应,表明某些平台因其固有特性在临床应用中更具安全性。然而,临床治疗性耐受诱导可能需要激活抗炎通路以同时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
早期将自身抗原与免疫调节药物结合的尝试之一,是利用脂质体协同递送抗原和NF-κB抑制剂,以FOXP3+ Treg细胞依赖性方式缓解实验性关节炎。类似地,基于芳香烃受体(AHR)在抑制NF-κB信号传导及调控适应性与先天免疫中的作用,通过工程化纳米颗粒联合递送芳香烃受体激动剂2-(1′H-吲哚-3′-羰基)-噻唑-4-羧酸甲酯(ITE)与疾病相关抗原,在多发性硬化症和1型糖尿病的临床前模型中重建了抗原特异性耐受性。 其他与抗原共封装的免疫调节剂包括IL-10、维生素D3及mTOR抑制剂雷帕霉素,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过敏反应及抗药抗体抑制方面均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事实上,在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模型中,将疾病相关抗原与多种免疫调节剂(维生素D3、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或转化生长因子β)联合给药,显示出显著的治疗效果,这与IL-10和PD1的诱导以及调节性T细胞和B细胞的诱导有关。
人类自身免疫性疾病通常针对多种自身抗原,且不同患者及疾病阶段所针对的抗原可能存在差异,这给仅针对单一或少数抗原/表位的免疫调节干预带来了重大挑战。然而,基于自身抗原与免疫调节剂协同递送的策略已被证实可诱导旁观者抑制效应。基于纳米粒子的抗原与免疫调节剂共递送体系,通过诱导FOXP3+和IL-10+调节性T细胞(Treg)向炎症部位迁移,实现了旁观者耐受性,同时抑制了局部先天免疫反应驱动的病理过程。类似地,在类风湿关节炎模型中,载有瓜氨酸化自身抗原和雷帕霉素的磷酸钙脂质纳米颗粒诱导旁观者耐受性;而在1型糖尿病模型中,脂质体联合递送维生素D3和自身抗原同样诱导了旁观者耐受性。综合而言,这些发现表明:联合应用免疫调节分子与自身抗原不仅能增强抗原特异性耐受疗法的治疗活性,更能预防某些治疗手段引发的自身免疫病理恶化。
基于核酸和病毒颗粒的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
基于核酸的方法(包括基于DNA和mRNA的方法)是实现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的理想手段。相较于肽类或蛋白质方法,这些技术具有多重优势:生产工艺简便、载荷(抗原与免疫调节剂)可灵活调整,且编码的抗原可在宿主内发生翻译后修饰,同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病毒颗粒为抗原递送提供了高效平台。其作为基因治疗载体已被用于向肝脏和胸腺递送自身抗原,从而诱导抗原特异性Treg细胞扩增、效应T细胞抑制及旁观者耐受表位。为应对安全性顾虑,植物病毒颗粒已在1型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前模型中进行测试。然而,病毒基因治疗相关的风险、针对腺相关病毒的预存抗体以及重复治疗诱导的抗载体抗体,限制了病毒基质方法在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中的应用价值。
核酸疫苗规避了病毒疗法部分风险。Waisman等人在开创性研究中,利用编码致病性T细胞克隆TCR的质粒,成功耗竭TCR特异性致病性CD4+ T细胞,并改善了多发性硬化症小鼠模型的疾病进程。在系统性红斑狼疮、1型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前模型中,编码其他抗原的疫苗也获得了类似的令人鼓舞的结果。基于这些初步发现,编码疾病相关抗原的DNA疫苗在MS和T1D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用于诱导耐受的DNA载体具有重要特征:通过去除质粒中激活TLR9的CpG序列,最大限度减少先天免疫激活。尽管这些试验显示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降低且存在旁观者耐受现象,但均未达到临床终点。因此,尽管DNA疫苗具有广阔前景且更多临床试验正在进行(表2),该疗法要取得成功仍需进一步发展,包括联合使用编码耐受性免疫调节剂的质粒。此外,质粒DNA固有的免疫刺激特性,加之对其半衰期、生物分布及摄取的控制受限,可能为抗原编码DNA疫苗在免疫调节领域的临床应用带来难以克服的挑战。
mRNA的稳定性低于DNA,需借助适宜的递送平台及修饰手段以避免激活先天免疫。纳米脂质体为mRNA的可控递送提供了独特平台。此外,与肽类疫苗不同,纳米脂质体mRNA疫苗无需针对每种核酸编码抗原进行大量优化。mRNA在体内快速降解的特性,消除了此前某些DNA疫苗引发的长期毒性及致瘤性担忧。对于免疫抑制患者而言,mRNA疫苗相比减毒病毒或细菌疫苗提供了更安全的治疗选择。
mRNA能通过TLR3、TLR7等参与感知病毒感染的免疫受体激活先天免疫,因此具有强效促炎佐剂特性。因此,接种mRNA编码表位可诱导强效的抗原特异性CD4+和CD8+效应T细胞。mRNA疫苗已被开发用于诱导针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等病原体的保护性免疫。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令人振奋的成果。
真核生物RNA经过深度修饰,有助于区分自身与微生物mRNA。因此,研究人员积极探索RNA修饰技术以最小化先天免疫激活并开发耐受性疫苗。例如,采用伪UTP递送的纳米脂质体mRNA疫苗编码髓鞘自身抗原MOG,不仅在多发性硬化症模型中抑制疾病进展,还诱导了对其他髓鞘抗原的旁观者耐受性。机制上,这些治疗效应与PD1和CTLA4依赖性诱导的抗原特异性Treg细胞相关。值得注意的是,mRNA还被用于将自身抗原特异性CAR转染至T细胞,在非肥胖糖尿病小鼠模型中展现出抑制致病性CD4+和CD8+效应T细胞的良好效果。综合而言,这些发现表明含mRNA编码抗原的疫苗可能为炎症性疾病治疗提供有效平台。
指导脓毒症精准医学的强化策略
精准医学是相对较新的概念,它在脓毒症管理中将个体患者特征纳入临床决策考量。这种方法与数十年来在脓毒症治疗中屡试不爽的“一刀切”策略形成鲜明对比。降低异质性的富集策略对精准医学的成功至关重要。
富集策略
富集研究主要采用两种互不排斥的方法:预后富集与预测富集。预后富集是从更大群体中筛选出具有更高临床重要结局风险的患者亚群。由于死亡率是常用结局指标,常采用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估(APACHE)及SOFA等疾病严重程度评分进行预后富集。在临床试验中,主要针对高危患者是合理策略,因这类患者的预后改善空间较大。然而数十项临床试验表明,仅采用预后富集无法有效筛选出对免疫调节治疗有反应的患者。
预测性富集旨在识别更可能对特定治疗干预产生反应的患者亚群。该方法通常基于潜在的(失调)生物学过程。其原理类似于通过ST段抬高与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的鉴别诊断,以确定驱动疾病进程的病理机制,进而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脓毒症领域同样适用此原则,但需注意的是:其驱动机制及针对这些机制的“正确”治疗干预措施均尚未得到证实。
未来临床研究亟需采用预测性富集策略,原因有二:其一,需确认特定驱动机制的存在及其相关性;其二,需识别针对这些驱动机制的治疗手段,或筛选出即使无法证实潜在机制仍可能对特定疗法产生反应的患者群体。当前普遍共识认为,精准医学要取得成功,必须平衡应用预后性与预测性富集策略。
免疫调节治疗的预测性富集示例
在脓毒症患者中使用皮质类固醇进行免疫调节或治疗肾上腺功能不全存在争议,因临床试验结果相互矛盾。表型分析可能有助于优化皮质类固醇用药方案。VANISH试验的事后分析揭示了亚组分类指导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潜在临床价值:在SRS2转录组亚组患者中,皮质类固醇治疗与死亡率升高相关,表明该治疗干预在不同患者亚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对VANISH试验数据的另一项分析显示,处于免疫适应性状态(基于基因表达评分定义)的患者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后死亡率高于安慰剂组。
地塞米松治疗被证实可改善需氧治疗的住院COVID-19患者生存率,其中机械通气患者获益最为显著,但无需氧疗者可能存在风险。COVID-19患者对皮质类固醇的差异反应亦见于原先针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描述的超炎症与低炎症亚组,以及COVIDICU临床亚组。这些研究表明,COVID-19患者的炎症亚型与地塞米松治疗疗效存在交互作用,暗示可通过预测性富集优化治疗。类似地,COVID-19患者中循环IL-6浓度较高者可能对托珠单抗治疗反应更佳。
其他可能惠及脓毒症患者亚群的药物包括他汀类药物和活化蛋白C(APC)。在ARDS患者的辛伐他汀HARP-2试验中,经回顾性识别属于高炎性亚组的患者,接受辛伐他汀治疗后生存率改善(28天及90天死亡率降低),而低炎性亚组未见临床结局差异。类似地,在针对脓毒症休克患者使用APC的PROWESS-SHOCK试验的次要分析中,研究者发现亚组间存在效应修饰:高炎症亚组可能从APC治疗中获益(死亡率32% vs 安慰剂组39%),而该干预在低炎症亚组中似乎有害(APC组死亡率23% vs 安慰剂组17%)。这些数据启发了针对ARDS患者的PANTHER IIb期自适应平台试验,该试验将实时识别高炎性与低炎性亚组以实现患者分层。
生物标志物和/或表型指导的富集策略在脓毒症免疫刺激治疗中也展现出潜力。例如,一项研究识别出38例脓毒症相关免疫抑制患者(定义为mHLA-DR表达<8,000单克隆抗体/细胞且持续2天),将其随机分配至靶向免疫刺激治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或安慰剂组。GM-CSF组全部19例患者mHLA-DR表达恢复正常,而安慰剂组仅3例(19/3)。此外,GM-CSF治疗可恢复体外TLR2/4诱导的单核细胞细胞因子产生,并显著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天数。但需注意GM-CSF作用机制广泛: 例如,GM-CSF可能驱动骨髓造血的病理性激活,由此产生髓系来源抑制细胞,进而导致适应性免疫抑制。
多项证据表明,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IL-1RA)阿那白滞素对部分脓毒症患者具有治疗效益。尽管一项针对非选择性脓毒症患者的阿那白滞素III期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因无效性提前终止,但对具有MALS特征(以肝胆功能障碍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为特征)亚组患者的事后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阿那白滞素治疗可使死亡率绝对风险降低约30%。另一项事后分析发现,在随机分组前IL-1RA水平较高(>2,071 pg/ml)的患者中,阿那白滞素治疗较安慰剂可使28天死亡率绝对风险降低11%。显然,事后分析存在局限性,解读时需谨慎。但这些结果表明,部分存在超炎症反应的患者群体可能从阿那白滞素治疗中获益。针对suPAR浓度≥6 ng/ml的新冠肺炎患者开展的SAVE-MORE试验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阿那白滞素治疗显著降低了28天死亡率、机械通气需求及住院时间。
IFNγ对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IFNγ生成或反应的遗传缺陷会削弱宿主防御能力,增加细菌、真菌和寄生虫感染的易感性。作为巨噬细胞激活因子,IFNγ可增强巨噬细胞的促炎反应,并在脓毒症等病症中对抗内毒素耐受性和免疫抑制。IFNγ还能在脓毒症患者中恢复mHLA-DR表达和单核细胞TNF分泌,并在健康志愿者反复实验性内毒素血症中逆转免疫麻痹。针对脓毒症患者的IFNγ治疗开放标签试验显示类似结果。基于这些数据及阿那白滞素的研究结果,两项II期临床试验 PROVIDE与ImmunoSep研究。在脓毒症患者中,根据血清铁蛋白水平(≥4,420 PROVIDE试验仅纳入36例患者,其中15例接受个性化免疫治疗(1例干扰素γ组,14例阿那白滞素组),这限制了对预后影响的可靠评估。Immunosep试验纳入280例患者,其主要疗效终点为入院至第9天平均总SOFA评分变化,目前尚未公布结果。这些试验为利用生物标志物实现预测性富集提供了范例。
结论、挑战与展望
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被视为自身免疫疾病及器官移植治疗领域的“圣杯”。数十年的研究已取得诸多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尽管临床前研究成果积极,目前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获批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或器官移植治疗,且极少有疗法能突破I期或II期临床试验阶段。
一个重要挑战在于我们对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免疫靶标广度的认知有限。事实上,抗原靶标可能从格雷夫斯病中的单一自身抗原,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多重抗原。表位扩散仍是重大障碍,这意味着成功的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阻止表位扩散、建立反复无偏见评估自身免疫反应特异性的方法、或诱导旁观者耐受。此外需注意,多数关于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的治疗研究均假设:调节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会同时降低致病性B细胞反应。然而,这种间接B细胞调节的强度、广度及动力学是否足以显著改善B细胞驱动的病理学,目前尚不明确。加之患者个体差异、阶段特异性自身免疫反应及HLA等位基因多样性,更使抗原特异性疗法设计复杂化。尽管如此,免疫谱系分析领域仍取得重大进展,包括抗原微阵列、高通量BCR和TCR测序、条形码四聚体多重监测以及表位预测的生物信息学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能识别诱导抗原特异性耐受的候选抗原,还能监测治疗反应,从而提供类似癌症免疫疗法的个性化方案。
另一项挑战在于: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免疫治疗干预往往在数年亚临床及临床病程后才启动,导致组织损伤累积、免疫记忆形成,并触发局部炎症机制与疾病病理进程。因此,尽管在某些疾病(如1型糖尿病)领域已取得进展,但开发有效生物标志物以实现患者识别和分层,仍是推进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的重要需求。这些局限性恰恰凸显了将前沿的临床前模型研究成果转化为人类疾病有效疗法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选择适合测试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疗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至关重要。例如乳糜泻为临床试验设计提供了独特机遇——遵循无麸质饮食的患者可在饮食挑战前接受实验性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最终,如何识别靶向信号通路以增强免疫调节疗法的治疗活性并预防不良事件?新型研究平台可为治疗性耐受诱导的候选信号通路筛选提供指引,包括:运用新方法研究炎症调控中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基于CRISPR的在体免疫调控研究平台;以及结合人工智力的斑马鱼等实验系统。这些方法已成功识别出具有治疗潜力的新型免疫调节机制。此外,近期发现的耐受性抗原呈递细胞群体可能为免疫耐受诱导提供额外靶点。只要这些关键挑战得以解决,结合靶向抗原与调控通路的新型鉴定方法,近期在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诱导技术领域的进展,有望推动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反应、移植及基因治疗的个性化抗原特异性免疫调节平台的开发。
推荐阅读
A nondeletional mechanism of thymic self tolerance. Science. 1989
Regulatory T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thymus. J. Immunol. 2019
Projection of an immunological self shadow within the thymus by the aire protein. Science. 2002
Fezf2 orchestrates a thymic program of self-antigen expression for immune tolerance. Cell. 2015
Thymic epithelial cells co-opt lineage-defin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to eliminate autoreactive T cells. Cell. 2022
Transfer of cell-surface antigens by scavenger receptor CD36 promotes thymic regulatory T cell receptor repertoire development and allo-tolerance. Immunity. 2018
Thymic development of gut-microbiota-specific T cells. Nature. 2021
Predominant autoantibody production by early human B cell precursors. Science. 2003
Receptor editing is the main mechanism of B cell tolerance toward membrane antigens. Nat. Immunol. 2004
Clonal deletion of B lymphocytes in a transgenic mouse bearing anti-MHC class I antibody genes. Nature.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