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代 美 术
Contemporary Art
为艺术抱薪者——钟涵的艺术与人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名誉院长|杨飞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二级美术师|仝紫云
摘 要:钟涵早年投身革命,后又到艺术院校深造,这一独特经历为其艺术创作积淀了浓郁的家国情怀与深厚的学养根基。他的艺术实践与教学对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本文从艺术经历与创作理念、个人特质与学养根基、师道传承与艺术贡献等方面,对钟涵进行全面的回溯与追忆,以期为当代中国油画发展提供烛照与镜鉴。
关键词:钟涵;油画本土化;主题性创作;中国风格;民族精神
在油画界,钟涵(1929—2023)先生是一位公认的读书多、学养丰厚、阅历非凡的艺术家,这也奠定了其最终的艺术高度。作为中国第三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他与同辈们共同将源自西方的油画艺术移植到中国文化土壤,并努力将其推向纵深,实现了从学习、引进到油画本土化实践的历史性跨越。
一
钟涵的成长经历始终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钟涵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梁思成、林徽因、李桦、李宗津等大家。这段求学经历不仅让他接触到严谨的建筑思维,更培养了他中西交融的文化视野。与此同时,钟涵积极投身革命,前往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学习。在解放区,钟涵担任“延安五老”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的秘书,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他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品质与革命热情,也提高了其逻辑能力和文字水平。
1955年,钟涵进入中央美院学习,随后参加了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该班是紧随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之后开办的。这两个油画班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深远的两次办学,培养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在“油研班”班里,钟涵的艺术创作深受名家大师们的熏陶,如在素描上深受钱绍武的启发,油画方面则受罗工柳的影响很大。
钟涵《东渡黄河》布上油画
165cm×380cm 1976年至1978年
钟涵早年涉猎很广,从建筑审美到革命实践,从文字秘书到艺术创作,这些丰富的经历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底子。靳尚谊讲,画油画须趁着年轻和精力旺盛的时候,一般在40岁以后就不太行了。可是钟涵除外。这恰恰是因为钟涵早年积累的学养足够深厚。钟涵曾说,他50岁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到油画创作上,很多有分量的作品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而之前的那些经历,不管是革命岁月里的精神磨炼,还是广博的知识储备,都成了滋养他艺术生命力的沃土,让他的艺术激情和创作灵感不断涌流。
钟涵50多岁的时候,被公派到比利时深造。出国后,他临摹了不少国外大师的杰作,包括安格尔的自画像、鲁本斯的女人体、恩索尔的作品,还有维亚尔的一幅很大的绘画。他临摹的作品风格跨度特别大,深入探究了不同艺术流派的精髓。回国后,钟涵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央美院高研班的教学工作中,与苏高礼等人一起执教,但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停下创作。即使年过九旬,钟涵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和教学热情。就像钱钟书说的,创作热情的消失就是创作才能的消失。钟涵的创作热情从来不止于某一张画的结果或者一时的评价,他的目标远大于这些,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史。这种超越个体成就的宏大视野正是他艺术激情的重要源泉。
二
钟涵的艺术创作,是深厚学养、精神追求和时代感悟的结晶,既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又蕴藏着深刻的艺术理念。他曾回忆自己早年接受的严格绘画训练。在乡下写生的3个月里,罗工柳对钟涵的色彩要求特别严,可就是这番磨砺,让他运用色彩的本事有了明显长进。他在“油研班”的结业作品《延河边上》,画的是傍晚时分毛泽东与当地农民沿着延河散步交谈的场景。画面上领袖背着手,朝着延安宝塔的方向走去。这个构思很独特,把领袖形象刻画得格外亲切、平易近人。
钟涵对雄浑的、英雄主义的东西,以及带有很强意志的东西,感情比较强烈;对于柔和的、婉约的部分,则兴趣相对较少。因此,钟涵的作品常常透着一种气势恢宏的情怀,而不是细腻温婉的小趣味。例如,黄河主题在钟涵创作中的分量很重,他经常画黄河船夫的生活,像《饮河者》所描绘的那样。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黄河水不能喝,画面人物比例也并非十分严谨,但是在他的画面上就成立。钟涵画了一个弯着腰的人,其实是把母亲河拟人化,赋予它一种很深的感情,非常有力度。又比如他画一个拿镐刨地的人和旁边的一棵树,就像米勒画的一样。不管大画小画都有很深的一种情感和情怀在里面,即便是下乡画一个写生的风景或很简单的几个色块,都拥有很重的体量。另外,中国古代碑刻也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像西安碑林,还有刻在大山上的著名石刻。他画的《江水与石头上的书(白鹤梁)》(见封二)就是以被江水淹没的石刻为主题,笔法抒情又有诗意,寄托着一种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思考。
钟涵《江水与石头上的书(白鹤梁)》
综合材料绘画 190cm×130cm 2004年
钟涵始终追求把个人画画的有限性认识放到中国文化或者人类文化这样无限大的背景下去审视。这种开阔的视野,让他不会被困在具体技法的难题里,而是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上。钟涵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学习,在阅读中思考,在探讨中研究,与不少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钱钟书、杨绛特别推崇,常常登门拜访请教。他还明确说过,画肖像就该选像杨绛这样学养品格深厚的人物去表现。当然,在具体的绘画技巧上,钟涵也很看重实践。比如,他强调“色彩要打翻身仗”。他在画很多素描,包括临摹大师作品的时候,在画面表达力上都很具体,指导学生的时候,也会亲自动手修改画作。然而,他心里始终清楚,技法只是工具和载体,他更关心的是:用这些工具和技法去表达什么?他坚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一个有情怀、有理想的艺术家,必须有更长远的思考。
钟涵在写实绘画里融入了浓浓的精神性,透着一种文人士大夫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例如,《雨天里画室来鸽》里那场倾盆的骤雨,《吾家大夫著书图》中灯下读书的温暖,《斗室光瀑》里开门瞬间像瀑布似的涌进屋里的光线,都是从生活场景里找来的灵感。这些画面虽说来自现实中的某个瞬间,可更是他用来抒发情感的载体,表达着更宏大的民族情怀,还有那种生命不停、奋斗不止的激情。
在如今这个时代,绘画的不少传统功能已经被其他媒介所取代。比如说,绘画的记录功能、设计功能被实用美术拿走了,剩下的实用价值可能变弱了,但对于提升人的审美、触动灵魂来说,好的艺术依旧有着无可替代的力量,它承载着关乎生命价值的深层意义。摄影术的出现,看上去好像夺走了绘画的不少功能,其实反倒让绘画回到了自身的本质,释放出更纯粹、更有生命力的潜能。从印象派之后,绘画的可能性被不断拓宽,它作为独立艺术语言的本体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这些价值恰恰不在实用上,而在它独特的审美表达里。艺术创作往深了走,作品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艺术家的境界和格局。判断一幅画是不是一流的,能不能成为“神品”,关键看它在精神层面有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在审美意趣上有没有展现出精妙之处,以及在情感力度上能不能触及到生命中最有价值、最深刻的地方。
钟涵《牧童睡了》纸上油画
36.5cm×46cm 1979年
钟涵《密云》布上油画
150cm×148cm 1990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钟涵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崇高又孜孜不倦的艺术状态。他年轻投身革命时就以信念坚定著称,后来转向艺术,又把这种特质变成了对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极致追求。有一次在一个讲座上,下面坐了很多学生,有人提问说到徐悲鸿和徐志摩,但提问者的态度特别轻浮,说得很随便。钟涵在现场发火,因为受不了那样去做学问,受不了说话随便、不严谨。另外,他还有一个非常不能容忍的事就是“俗”,绝对不能忍受艺术上的甜俗或者媚俗,他对俗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中国文字里面“美”的反义词是“丑”,但其实在中国文化里“美”的另外一个敌人是“俗”。因为中国文化一直讲“脱俗”,一旦俗了就不入流了,就不可造就了,与文化没关系了。钟涵对“俗”的排斥,其实是在坚守文化的底线和艺术的纯粹性。这种坚守让他在热闹的艺术圈里保持清醒,用有力的笔触抵达精神的高度。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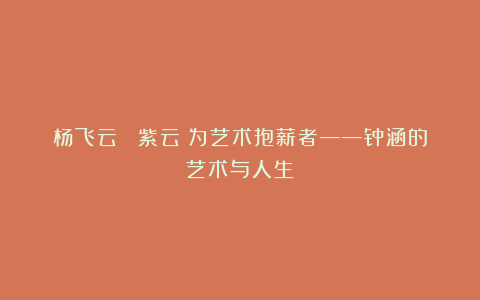
钟涵身上的文人气质,还有兼济天下的胸怀,是使他成为“学者型艺术家”的关键。这不仅体现在其艺术创作里,还深深融进了做学问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探索艺术的路上,从未停止对中西文化养分的吸收。从文艺复兴时期卡拉瓦乔艺术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到米勒、库尔贝对平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再到伦勃朗作品的深刻性,尤其是那些通过普通百姓展现高贵与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他都研究得特别透。比如,钟涵常常提起伦勃朗晚年没画完的巨作《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密谋》(The Conspiracy of Claudius Civilis),认为自己受了不少启发。另一幅对他影响很大的作品是维亚尔的一幅类似大写意风格的画,这也能看出他对抽象和带有表现性绘画语言的偏爱。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钟涵对中国文化的钻研也从没断过。他对古代器物和雕塑兴趣很浓厚,收藏了不少古代陶俑和雕塑精品,而且筛选极严,只留那些文化内涵和审美水平都达到一定高度的东西。到了晚年,钟涵专心研究苏东坡,还常常引用他的艺术理论。在油画家里,钟涵的书法水平很高。他和雕塑家钱绍武交情特别深,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文学。这能看出他们这一辈学人修养是非常全面的,心里装着深厚的文化情怀。他们一直在思索,作为现代艺术的探索者,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创作推动教育发展、促进民族文化进步。他的情感是民族情感,是对劳动人民有着真正的情感,而不仅仅是细腻的、柔软的情感。在新时代,艺术为社会、为人民的精神处在钟涵的整个认知里很高的位置,也成了他的艺术理想。
钟涵学问广博,始终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想法。他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对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也一直延续着读报的习惯。他对时代和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对新鲜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晚年愈发觉得自己时日不多,决定把手机、电脑这类与互联网有关的东西全都放弃。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对时事消息还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洞察力也十分敏锐。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积极学习的态度,他的精神状态才这么有活力,这也印证了中国文化里“苟日新,日日新”的道理。
钟涵《饮河者》布上油画
150cm×136cm 1990年至2008年
2013年,油画院为钟涵举办了“中国油画院油画家像研究系列——钟涵”的回顾展,并整理出版了一本文集。油画界很少有像他这样的文笔,苏高礼也曾感叹:钟涵写文章又快又好,下笔如有神助,几千字一下子就写完了,而且文风还很诙谐,思路特别清楚。他早年当吴玉章秘书,一方面是因为他本来就爱读书,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他出众的文字功底。在他看来,绘画就是视觉化的文字,文字里的思想和艺术所承载的生命力是相通的。他工作室里的藏书非常多,比得上一座小型图书馆,这在油画家里是不多见的。钟涵天生就有做学者的天赋,不仅爱读书,还能钻到书里去琢磨精髓,是能从阅读里吸取丰富养分的智者。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很多都来自长期的阅读积累,这种阅读的深度最终决定了他的艺术高度。
钟涵在人文学养方面有着广阔的文化视野,特别强调文化史的重要性,他觉得即使没必要非投入大量精力在文学和哲学上,但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或文化史却要有一个大体上的把握。他把这种基础性的文化素养积累看得特别重,认为这是理解世界、认识自己、滋养艺术的根基。在他看来,我们虽然没办法把所有细节都弄明白,但掌握历史的基本脉络、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中外文化的差别,是形成深刻认知和人文情怀的关键。这种做学问时的广阔视野,无疑让他的艺术创作里多了份深沉的历史感和超越时代的人文关怀。
四
钟涵的教学实践和他产生的时代影响,早就超出了个人艺术成就的范畴,成为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后辈艺术家,还深刻推动了油画艺术的本土化进程,其教育理念直到现在还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中,钟涵主要的教学工作就是带油画院的课题组和创作班,油画院的同人对此都深有体会。钟涵晚年觉得自己用在画画上的时间变少了,把很大精力都投入到教授学生上。他会仔细给学生看画稿,一遍遍地告诉他们怎么处理构图和色彩,把自己一辈子的艺术认识与学养,甚至那些没来得及实现的理想,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学生。即便到了90多岁的高龄,他依然坚持每天到教室来,要是看到学生没什么进步,他会感到着急。这种深沉的教育情怀,不仅来自他作为教师的责任心,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民族文化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深刻思考。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钟涵既重视基础训练,又善于因材施教。他设计的教学大纲很有特色。不管学生以前取得过什么成就、拿过什么奖,进了他的课堂都得从头来,要系统地进行肖像、人体写生训练,还要深入生活,下乡写生,目的就是查漏补缺,把根基打牢。他觉得只有原理清楚、基础扎实,艺术这条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他常常强调结构原理、造型规律和色彩基础这些核心要素。在他看来,这些常被忽略的“基本功”,恰恰是决定艺术能达到多高水准的关键。钟涵指导学生创作时,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现有水平来点拨,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他晚年带班时曾感慨,每一届学生都会带来新的挑战,就像“老兵遇上新问题”,因为每一届的学生都非常不一样。现在的问题用老办法不行了,因而对每一届学生重视的方面、关注的东西都有变化。
钟涵《延河边上》布上油画
180cm×360cm 1999年重绘
钟涵《望中犹记,晚潮明处》布上油画
170cm×340cm 2013年
钟涵与第三代油画家对油画民族化、本土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以广博的知识、独到的眼光与时代精神对话,给予年轻学子指导。他们将油画艺术与中国本土文脉紧密衔接,推动油画的纵深发展,使油画真正变成被中国人深入掌握的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追随或模仿。在教学上,钟涵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很多有基础的画家得到深造和提高的机会,这些学生大多是艺术院校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教师,从而成为将钟涵的教育影响力转化为推动基础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钟涵是一位不受世俗牵绊的艺术家,而命运和时代又把他推到了这样的高度。他们这一批艺术家在齐白石、徐悲鸿、马克西莫夫、吴作人、李可染等大师的教授中学画,中国精神、中国文脉、中国人的情怀等文化基因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如果说徐悲鸿等前辈主要是引进油画,那么他这一代则更进一步,把油画艺术和中国本土文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衔接与融合,使油画真正成为被中国艺术家深刻理解和掌握的艺术语言。与民国时期的画家相比,他们在艺术逻辑、表现能力、对现实的把握和社会影响力上都更成熟,对油画本体的理解和驾驭也达到了新高度。他们总是强调“本体语言”,其实是在推动构建一个更完整的油画艺术体系,通过自己的实践深入掌握其原理,把油画艺术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
中国第三代油画家,每一个人都各具特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力量。他们身上都有着开阔的格局和深厚的情怀,对艺术抱有执着的追求,还能脚踏实地去实践。所以,他们在中国油画界好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在艺术探索的前沿活跃着。
从更广阔的眼光来看,像钟涵这样的“先生们”,正是整个行业精神高度的象征。他们用一辈子的学术探索走到了专业领域的顶端,他们的权威从来不是靠外在头衔撑起来的,而是来自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还有人格魅力带来的强大感召力。这种影响力就像个无形的磁场,不仅给后辈树立了标杆,还构建了一种集体性的精神依靠,好像只要他们在,艺术探索就有方向、有坐标,行业发展的根基就稳当。这份担当不是出于私心,而是源于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当这样的先生们过世后,后来者如何带着这份传承继续往前走?如何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独立思考、打开新局面?这既是对个人的考验,更是一个行业能不能实现代际接力、持续发展的关键。这或许正是先生们离开后,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考。
For the Sake of Art: Art and Life of Zhong Han
Yang Feiyun, Honorary President of Oil Painting School,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Tong Ziyun, Postdoctor and Second-level Artist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Abstract: Zhong Han devoted himself to revolutionary endeavors in his early years before furthering his studies at art academies– a unique experience that endowed his artistic creation with profound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a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His artistic practice and teaching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oil painting,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artistic talents for it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on Zhong Han’s artistic journey, and analyzes his creation philosophy, personal traits, academic foundation, mentorship and artistic contributions, with an aim to providing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il painting.
Keywords: Zhong Han; localization of oil painting; theme-based creation; Chinese style; national spi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