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识:
满架葛藤打不打
曲则全矣
甲辰连山写
内容:庄子网上书院 第432次讲学 《外物》22
时间:2025年07月04日
整理:学人
原文文本: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今天的早课会延续庄子网上书院的进程,今天早上是上《庄子·外物》篇,没有书的学人,可以用手机百度一下,《外物》篇的最后一节。这几天我们在共学《人间世》,所以早上稍微跳一下,尽管是《外物》篇,文字可能跟《人间世》有所不同,但要讲的向度是一个东西。我们讲千回百转不离其宗,也不仅仅《庄子》一篇文本里面,你不要以为此一章彼一章、此一节彼一节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就是古今哲人不同的著作、不同的学派,所讲也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我是读老子、庄子,还是尼采、叔本华都没有不同,这里面关乎一个人怎么治学。古人说,圣人求同,小人求异,如果不能在万物一体处感知世界,无论干什么都是局促的,无论立多大的志向都会活成局促的小人。人不能得一,就没有办法以人的名义活在人间世,或者说只能以人的名义活在人间世,而没有真正活成人的样子,这是永恒的。
如果真的有古今学问的不同,中西学问的不同,那就没得学了,既然不同学什么呢,既然不同怎么学也不可能有感通。人与人之所以能沟通,能够有感通的可能,正是因为有一如的东西,两个人无论交换什么,一定是基于不可交换的东西才能完成交换,无论是两人谈恋爱还是市场的交易,你拿钱去买他的货物,体会到这一点,你治学就完成90%了,之后你不管看什么书其实都是印证,而不是去了解你并不知道的东西。一个人不可能了解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那个构成所谓了解的一定是基于共同的知道,所谓听别人说话,听着听着我明白了,他所说的那个东西原来你误以为你不知道,听着听着原来是和你印证了,这叫契,又叫符,心止于符,一下子印上了,你就会有击节之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那一刻千世万世如旦暮一遇。
你看庄子是不是这样说话的,不管间隔多少年,你突然发现像是一瞬间你俩见到了,这叫旦暮一遇,所以这个东西既不是思辨的东西,也不是你原来没有给你一个有,好像你一下子充实了,这才是每个学人能够学的真正的前提,这种前提被这些智者表述为本自具足。
我们治学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真正体贴到本自具足的过程,原来根本不假外求,原来确实在我这有,原来那个有只是传说,因着学你才发现这个有是真实可信的,圣人不欺我,因为越来越有不知道该找谁交流的冲动和快乐感,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知音难遇呀。他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所以不需要你鼓努用力说,我一定要学更多的知识,就知识来说,你当然可以学更多,就真正的治学来说,他没有更多,这个如果慢慢地有所明晰,你在治学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治学的方向,什么叫调整呢?学着学着你有下意识地把他作为可求的东西去外求了,这时候慢慢地调转调转再调转。
所以像佛陀这样的人都被慧能称为调御丈夫,什么叫调御丈夫,实际是自我调御的过程,越来越中的越来越有会心感,这就叫调御,调整的调,驾御的御,如开车一样,从一开始不会开,死死地抓着方向盘,到慢慢越来越人车一体。古人不是用方向盘,开车是驾马,从一开始人、马、车三个,车是车,马是马,人是人,人跟马之间的沟通变得很困难,因为马听不懂人话,你不能用言语沟通,也不像后世方向盘,而你手里面只能抓一根绳子,绳子怎么驾御马呢?绳子代替语言成为一个无声的语言,朝左抖抖,朝右抖抖,停,这个时候人要驾御马,马要带着车,实际上学驾御的过程就是让这三个没有关系的东西完成三位一体,三位同心。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这些都是天地啊,本来是各自分开的,现在你需要让它们会通到一个心上。“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人不就是学如何驾御自己的人生吗,而所谓驾御自己的人生不就是怎么驾御自己吗,所谓驾御自己不就是知是非美丑,知什么时候当行什么时候当止吗。夫子当行行当止止,不能读了就过去了,你一睁眼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清楚是当行还是当止,你没有睁眼的时候也得知道是睡还是起来,晚上该睡的时候是不是去睡,这个时候是不是做抉择,这不就是行止,这不就叫决断吗。
所以你发现你能正常的活着,恰恰呈现出你是不是高明的至简的驾御功夫,我们实际上是带着我们身体上的车走在人生的路上,什么时候该停车,什么时候该行走,这就关乎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喝,这也真的是既简单又复杂,所以你看越是有格调的人,他越是很轻松的打理自己的人生,小到吃喝拉撒,大到我们以为重大事情的抉择,其实那里有什么重大抉择,一样的,这个生意要不要做,这个人要不要合作,这都关乎你基本的判断。
你拿什么判断,这不就是孔子跟颜回讨论半天的事吗,颜回以为是对卫君,孔子说根本不是对卫君,只对你自己的仁心,就是今天上午要讲到的,“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这不仅仅是你,所有的圣人也都这样,没有一个外在的事值得你去关切,因为所有外在的事都是因为你要关切你的内心,才有关切外在的可能。比如睡觉,这个事情不是你需要努力思考的,你要是思考的是,是不是该去睡觉了,至于怎么睡觉,天理会决定的,你只要往那儿一躺,只要不干预就会睡着,要是你努力想睡觉,就睡不成觉,那些失眠的人不就是躺那里想睡觉吗?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觉,你把睡觉当事了。你看在上着课都睡的人,他不把睡觉当事,他坐着本来听课的,他睡着了。所以你越想有,越没有,这叫举重若轻。
题识:
甲辰节至大暑瓶花清供
连山
我们看《外物》篇最后几句也是这样的,这段很短,上周五讲到最后,“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是《外物》整篇的结尾,这一篇从“外物不可必”启动,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做结,言语本身就是外物,所谓忘言之人就是不会被言语黏着的人,这就回应了外物。不被言语黏着是个什么说法,言者心音,如果黏着在言语上,以为言语可以表达思想,那他就会遮蔽心。“巧言令色,鲜矣仁”,言语怎么能表达思想呢?尽管思想是通过言语表达的,但是言语是不能表达思想的,这句话你看前后对不上,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元旦在北京上《齐物论》时,讨论得很深入。
言语是个吊诡的存在,昨天我也提到近代德国的著名哲人维特根斯坦,好像只有维特根斯坦才有对言语本身做深切关系,不是这样的,但凡哲人不得不用言语表达思想的时候,他就要对言语本身做界定。特别是西方哲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梳理名相概念,任何一个哲人要用语言建构他的思想体系的时候,他一定先要对他所使用的语言,先做一个界定,比如涉及到“意识”“辩证”“存在”这些词,我所说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弄反了,之后我文中凡是用这个词都是我界定的这个意思才行。他为什么不用通常大家都认为的意思,是因为任何一个字,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需要用他表明特定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给它画个圈,我只用这个意思,不用其他意思,否则接下来没法对话,这就说明语言并不是一个普世性的,即便是同语系的人。语言是不是普世的,很好验证,比如“美”字,就是指美好吗?不可能,如果指美好,别人夸你美,你会难过呢。所以,文字是在语境中才有用,文字本身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开始就以为一定要先知道字的意思才能治学,他就先费很大劲学《说文解字》,这些人都会搞废的。
你知道吗,从此他看书只是按《说文解字》解释书了,这样不是搞偏了吗?比如我们以这一段为例,“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他就会字解经典,字解经典跟庄子要表达的东西完全不搭边。“荃者所以在鱼”,我们逮鱼用荃,逮鱼的工具,是个鱼兜子。逮鱼用荃,但得了鱼就把荃忘了,如果这样翻译,这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得了鱼会把荃忘了?一个渔夫用逮鱼的工具把鱼逮着了,把鱼拿走了说,把工具扔了,可以这样说吗?而且他跟这个“忘”没有逻辑关系,我为什么要忘了,记着不行吗?如果忘就是忘记的意思,我拿的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他怎么翻译呢,使用捕鱼的竹笼是为了捕鱼,捕到鱼就忘记了竹笼。傻子也不会忘呀,所以你如果不幸买了这本书,然后你看这翻译要么就是庄子傻,要么就是你傻,我要是信他我才傻呢。
这样如何传习?今天之所以斯文扫地,就是因为一大帮识字的人把斯文弄扫地了。下面是这样翻译:使用捕兔子的网具是为了捕兔子,捕完兔子就把网具忘了。搞不懂要干啥,使用语言是为了表达意思,明白意思了就要忘记语言。忘语言了下次怎么说话呢。然后接下来这句话更搞笑了,我那里能够寻找到遗忘语言的人和他交谈呢。我看完了也不知道在说啥呢。我就想到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庄子的时候,那时我辞职回家二十多岁,画画一年,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不知道该干嘛,不知道为啥要画画,不知道啥是美,完全没有再画下去的意思了,但是有潜意识里的不能放弃,所以就想买画论看看,然后画论又看不懂,这时候就弄了一本《庄子》,就是这种白话翻译,但是不是中华书局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叫《白话庄子》。最初我也是有机心的,那时候想文言文也看不懂,我们这一代人哪里学文言文,文言文都不好,繁体字也不认识,就买个简体版的《白话庄子》,附一点原文。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庄子》这本书,然后认真的开始看《逍遥游》,特别像我过得七荤八素的人,一看“逍遥游”几个字,眼里放光,想象我是不是也能逍遥一把。结果,才看第一段,我就火上来啦,气得把白话翻译都拿刀剪掉,净胡扯。即便我没读过庄子,看看原文,虽然不懂但有庄严感,再一看白话翻译,一下掉屎坑里去了。我那时候尽管不知道原文到底啥意思,但是我最起码知道白话翻译太扯,这样干不是谬种流传嘛。
我们来看看庄子要跟我们传达什么,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字。后世有一些人诟病庄子,既然得意忘言,为啥还要留文字给后代?这些都是属于望文生义的人。人在这个世间,不要说人,动物在这个世间互相之间还有传习。我们看动物世界,动物出生,动物爸妈也需要养它,需要教它基本的捕猎技能,这就是传习。没有学,任何活物都不能够在这个世间生存,《动物世界》讲大熊猫,一生下来,老熊猫带着小熊猫,最起码过一年要教他爬树,教他捕猎,教他吃竹子,啥都得教。老鸟得带小鸟练习飞翔。动物是有教学的,何况是人呢?动物是教它基本生存的能力,而人是要教人成人的学问。
既要教你生存,又要教你怎么样成人。所谓教成人,人因为有烦恼,有疑情,才会寻找老师解惑,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所谓圣人就是人在越来越迷茫被遮蔽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启蒙,帮你解开蒙在眼目上的幕布,这就是圣人。圣人具足慈悲,深怀悲心,“天下无道,圣人生焉”,这不是诋毁圣人啊,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才需要有人带来光明的可能,这是为什么圣人要降世。我们读先贤先圣的书,是为了寻一条光明的路,而这个光明,端在于你能不能知常。老子说“知常曰明”。自诚者明,学问只是在于“知常”和“自诚”。自诚是需要学的,不学就没有自诚的能力,尽管你有自诚的态度和志向,但是怎么样才能自诚是一门学问。这样我们就知道,先圣千言万言都是讲怎么自诚的。
题识:
甲辰连山写
“荃者”,学问是没法直给,因为不是个道理,没有办法语言直给,语言只能绕着弯给你,绕弯就是打比方,打比方就叫寓言,所以《外物》之后就是《寓言》。什么叫寓言?就是没法直接说,也组织不出来语言给你听,但是可以举例子,而举的例子必须双方都知道,都有这种经验。比如一个人没见过老虎,但他见过猫,那就好办。就告诉他,你没见过老虎没问题,老虎长得跟猫差不多,只是比猫大个十倍、二十倍,叫大猫,这时你脑子里面最起码出来一个形象了。这一交流不是只是靠语言哈,是语言要转化为一种图像,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语言如果是书,图像就叫画”,所以书画是同源的。我们实际是依赖对图像的认知,然后才接近真相的。
人为什么要画画,向日葵不是通过“向日葵”三个字知道向日葵的,是三个字代替了图像,凡是见过向日葵的人,而且知道它被命名为“向日葵”了,从此,你看到向日葵三个字,脑子里面一定是有这个图像的。没这图像,向日葵三个字是不可以,是没法告诉你它是向日葵的。写个水给你,你如果没见过水,那是没有用的,他跟你构不成交流,他不是你看水这个字你就知道水了。同理,你如果口渴了,我看到项医生喝了一口水,如果项医生口渴了,我给他写个字“水”,放在他面前,他是解不了渴的。他眼睛看到,这叫水,他也解不了渴。因为这只是你喝到水的前提,我们为了方便喝水,为了方便交流,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叫水,水是文明的结果。水先于人而在,但它不知道它叫水,它也没有名字。水有了这个名字,是由圣人开始的。
什么叫圣人啊?圣人为天地万物定名分。一言以蔽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圣人定的。为什么要定名分?定名分还不仅仅是有名相,既要有名,还要有分,叫名分。这家这个叫爸,这个叫妈,这个叫儿子,这叫女儿,既有名,又有分,还有位阶啦。那叫山,那叫水,那叫云,那叫天,那叫地,那叫木头,那叫石头,这一切名字都不是这个地球有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因为后来有了人,人跟人之间方便交流,然后就给万物开始命名。命名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语言交流关于山、关于水、关于云了。这就变得很方便,就像货币一样,一开始以物易物,到后来直接用货币,中间就有一个交易的中介。语言就是中介,就是在那个所谓的事项和人之间,文字就像钞票一样,只是个中介。
这个中介实际上没有用的,你说货币不是值钱吗?那你到博物馆,你看那已经过期的钱还值钱吗?已经废掉的原来的纸币,现在就是废纸了,除非是在古玩市场,有人喜欢它,它作为一个没有用的东西被人玩,就叫古玩,它已经没有用了。作为货币的功能是在时空之下被赋予的,这都是基于“外物不可必” 的背景来讲的。什么叫外物?世间所有的物质都是外物,不是有必然的作用。比如人的肉身,人的肉身对人来说,我们说是必然的,没有肉身就得死啊,但肉身在未必能活啊。你的肉身不是你的必然,所以养生只是养肉,就养错了方向。养生是通过养肉身这个手段来养你的性命。这肉身和性命是不二的,但如果你离开性命,只是养肉身,只是追求肉体的健康,你的良知已经大大的坏掉了,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已然是死了。
色身对我们当然重要,不能没有色身承载,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如果物质没有了,所谓的性命也没有寄托,色身是个因缘,不是个必然,所以“外物不可必”,只是因缘。所谓因缘,就像钟在那是不会响的。不是有个钟就一定能响,没有人叩它,它不响。不是有钱就一定能吃上饭,钞票不能管饿,有人就饿死在金山上。你拿钱去买食物,你吃的是食物,钱不能管饱。同样的道理,你身体被调理得特别健康,不等于不想自杀,哪里以为只要健康就好,都不是这样。人如果脑子执着在你以为的正确上,你会一生活不正确的。
这是《外物》篇要讲的东西。他依然是针对人,针对有可能读到这本书的人,针对立志成为一个活泼泼、光明的人留下的文字。而这文字就构成了你有可能反身而诚的因缘,文字不可能给你智慧,文字也不存在任何能量,更不存在这是经典一定要顶礼膜拜。有人一看到佛经、圣经,就觉得有巨大的能量,这都属于迷信、自嗨。之所以不轻慢经典,是因为它承载着圣人之言,我们基于对圣人的尊重,尊重书、尊重文字,并不是文字本身有什么超能量。
“荃者所以在鱼”,就是逮鱼,你有本事直接下手抓也可以,下手抓,手也是工具了,手脚都是工具啊,它是爪牙。要么就徒手抓,要么找鱼叉,要么编网去捕,总之需要有工具。那你需要这个工具是干什么呢?是为了逮鱼。并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工具。就像遇到一条河,为了过河,需要找一条船。如果没有这条船,你可以伐木造船。但是你人生绝对不是为了造这一条船,你的人生是为了淌过这条河。能直接过去不就行了,能直接过去当然可以,所以《诗经》说,如果浅水可以过去,如果水深你不会游泳咋过去呢,不能硬来,过去就淹死了。你不但过不去,还会溺死在里面,所以为了确保你能过去又不溺死,这时你就需要干跟过河没有关系的事。为了过河,需要去伐木,这实际上跟过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是造一个器物,这个器物也没有直接的表明跟他有关系,除非有人经历以后,有人说,过河需要舟,需要桥,所以你要么架桥,你要么做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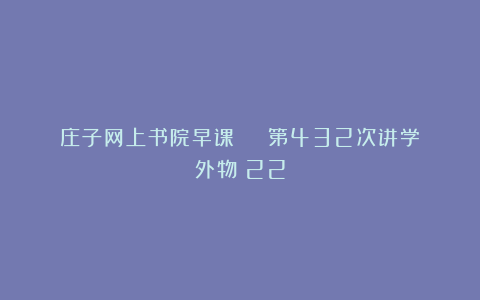
但是实际上本身,架桥和做舟这个事情都变成另外的事情了,跟过河完全不是一个事啊,你开始干一个闲事。你不干这个另外的事,你真实要干的事也做不了,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中庸》说,这叫“曲至”。人生但直行,却没有一个直道。所有的直道都是曲至。用今天的话说,你不做无用之事,哪里有有为之人生啊!你才能知道啥叫有用无用。但有些人说,我要有效率,我绝对不干任何好像不是直取的事,结果你越想走捷径,越绕弯路。
你越执着于捷径,终生不能抵达。因为人生根本没有你想象的捷径,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弯路来实现的。你想吃个馒头,世间绝对没有可以直接拿的馒头,除非你父母替你做好了。所以,农夫要吃馒头,首先要去耕地,而且耕地跟馒头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有了经验才知道,耕地是为了播种,播种是为了长庄稼,长庄稼然后收回家,还要去建磨坊,才能打面,打完了以后,最后还要去买锅,还要去弄灶,最后发现,出来是个馒头。谜底被揭之前,前面干的都是无用的事。
题识:
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甲辰 连山
你说你去割麦子,结果你去找磨刀石磨刀去了。这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说“磨镰不误割麦”。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割麦不好吗?但你的刀不快你所有时间都用来割麦,能割啥呢?什么叫“事半功倍”?所以,这个世间的事情是绕一圈的。《论语》中说“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他不会想抄近道的。因为没有近道可以抄,也不是故意要绕弯路。所谓的“近道”,就是弯路。你为了“走弯路”而走弯路,那你真的就走到一条弯路上去了。这个里面就需要有调御的功夫。而“调御的功夫”就是在于你要始终不离那个目标,但是你又得知道要达到目标,要干哪些跟那个目标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事。
咱现在有导航,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更有意思了。设置目的地后,它会有一根线连到那,但你绝对不是按照那根直线开车的。目的地本来是在北方的,你在高速公路上却是朝南走的,你得朝南绕一圈,但是那根线始终拽着你,绕来绕去,直到到那个地方。那根线,是每个人在人世间,无论绕多远都不能断掉的。那根线一断掉,你就迷失了。那根线就是不管你在世间横向地、外在地绕多远,那根通往你本性的线不能断绝。这根不断绝的线就叫“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贯的东西可不能断掉了,一旦断掉了你算是丢了。
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好的师友,没人随时提醒你“那根线不能断”,你就真得是瞎忙了。你想吃饭是为了养生,挣钱是为了养生,养的啥生?是“成性存存”的那个“生”,结果为挣钱而挣钱,就为挣钱而活着了。这就是那根线断了。即便最后你被世俗人称为一个巨富、大商人,但是你的人生不是为商人而来的。
所以我们正在学的《人间世》这一篇中,历史上是孔子到卫国去的,但是那些有眼目的人说“孔子不为卫君”。而庄子就编了个故事,颜回却为卫君而去卫国,孔子把他拽回来了。什么叫“孔子不为卫君”?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从鲁国到卫国,我们会以为他是为卫国去的。孔子不为卫君,孔子为了什么?孔子为了道义。但是不可以把“道义”作为一个目标,因为把“道”作为目标,“道”就变成你之外的一个目的地,它就叫外道,“道”就异化为外物。所以它不能是外在的。为了道义怎么样才能抵达呢?通过外物来抵达。那就去卫国、去宋国。对于庖丁来说,为了道义去杀牛,杀牛是他家的本分事。所以在世间法他的本分事是杀牛,他家世代杀牛,他甚至没得选。但是他生命的本分事是成人。通过杀牛、画画、逮鱼、逮兔子……,成就他的本分事。
惠能和尚混迹在猎户队伍中十五年,他不是去当个猎人的助手,但是这十五年他一定会去做猎户的助手,不然的话人家凭啥养他?他那个时候是逃难。他能逃到哪儿去呢?那么多同门师兄弟追杀他,还不是敌人追杀他啊。同门师兄弟是知根知底的。如果你是能和尚的同门师兄弟,你会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惠能?一定会在你判断惠能会躲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你千判断万判断,不会判断惠能是藏到杀生人家。因为作为和尚来讲,他认为一个和尚一定是不能杀生的,所以猎人之家惠能是不会去的,因为那不是惠能该去的地方。
所以惠能恰恰藏在了最危险的地方,他投寄到猎人家,可以确保他的同门不会找他。这就是他的智力降维打击到他的同门。因为同门认为的“杀生”是执着在杀生上的,而猎人就是以杀生为业的人。能和尚并不这样认为,杀了良知才叫杀生。所以,能和尚在猎人队伍吃肉边菜,帮着人拾兔子。猎人打死了猎物,惠能和尚肯定跑过去帮人拿回来。他得去干活,不干活就不可能在那待得住。而且这十五年猎人也没看出来他是个和尚。这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他藏不住。最多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从小就不喜欢吃肉的人。他是能入乡随俗,善于所谓“无行地”的人,即善于消掉自己任何痕迹的人。他才能从容地活在猎人队伍里十五年。这个就叫“忘”,“忘”不是“忘记”。什么叫“忘”?就是猎人家也不会意识到他是个和尚。同门也意识不到他会藏在猎人家。所谓“忘”,自有不忘的东西,只有能和尚知道他是谁,这个东西永远都不会动摇。
架桥是为了过河,造船是为了过河。造兔夹子是为了逮兔子,弄鱼筌是为了逮鱼。鱼筌是次要的,这叫“忘”。这段是要讲这个,讲的依然是外物,只是最后总结得特别奇妙。
所以“荃者所以在鱼”,要注意“在”字,从《大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海德格尔的“在”,都是这个。哪里有古今中西之变呢?我们看到中西古今的不一样,这是变,但这个“变”就是不变的显发!人从一岁长到二岁长到三岁,相貌一直在变,但是你还是你,你的本性良知从来都没有因为你的长相而变化。所以,人是因着这个日新的色身的变化,正是那个如如不动、永远不变化的、所谓“恒常之道”的显像而已。
千说万说都是为了让我们慢慢在这样一个所谓“大一”的宇宙,和我们自身同在的这个状态上,跟我们有相遇,有触发。这种相遇在《易·解卦》说“邂逅也”,一下子跟自己邂逅了,从原来那个识见的自己、跟本来面目的自己,一下子两个人相遇了。所以每个人都等待着一场艳遇,都等待着一场邂逅。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还要活着,就是因为你需要你跟你自己相遇的那个时候。自从一相遇,“金风玉露一相逢”,古人就有这样一个极美的表述,“只许佳人独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杳然难言也”。“得鱼忘筌”,编渔网志在得鱼,鱼得了,渔网就可以放下了。
禅宗公案说,架桥是为了过河,过了河,桥就可以忘掉了。这个“忘掉”,不是世俗所说的记忆。吃饭用筷子,但绝不是吃筷子,用筷子把饭夹到嘴里面,筷子立即撤出去,没有谁在那逮着筷子咬。那个东西就抽离出去了,它不再会成为你的累积和负担。就像人在世间做事,人在世间做事是为了成道的。政治家因治国的形式修道,至于治国之后所谓的“功劳”,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就如过眼云烟。哪里有什么功劳可言呢?只是做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该做的事情,没有这样一个因缘和机会,我还没有机会跟自己相遇呢。
题识:
枝枝梅花撑著月
甲辰结夏写此消暑
连山
我们就称为“为人子”,因着“人子”的责任去侍亲,可以使你有“成人”的机会。作为人子,是在侍亲中成人。每个家庭是不是这样的?当这个孩子突然知道有自觉于爱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孩子懂事了”。什么叫懂事了?就是他成人了。他一下有了人的自觉了,他不只是老是躺在那等父母疼他。只是等着父母疼他,就叫啃老的人,这种人叫“巨婴”。他长得再大,他都没有成人的机会。所以不是父母需要你疼他,而是你正是基于你主动知道疼父母的时候,反过来印证你这趟没白来。所以这时候,父母实际上是你“成人”的因缘,你不是施舍爱敬给父母,更不是你所谓的“报恩”。
报恩是一个彼此交易的关系,你有什么恩要报的呢?你只是尽你的责任。你说你报恩都报完了,你干啥去呢?它不是还账啊!你可以用这个名相说“父母恩情报不完”,这个名相可以用,但是名相是不能够准确地表达你实际的作为的。所以这叫“言而不尽意”。这不可能准确表达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不能准确表达,你就不至于对于言语本身是不是说得圆满在乎了。因此我们就能体察到,所有圣人的言语都有漏洞,它不圆满。所以你想批评圣人,那机会多多。
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善学,就是因为他一旦发现圣人的言语中有漏洞的地方,他就说圣人也……今天人巧言令色,写论文会用逻辑把话说圆了,说得无懈可击。诸位要知道,凡是能够把话说得无懈可击的人,都是骗子。所以一个君子不会试图把言语说得完满让人无懈可击。只有一个有机心的人才会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可以包裹他一个低劣的人。所以“言语”是一个试金石。只要用智力把言语说得很漂亮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几乎是培养把话说圆满的人。导师审核论文,只是审核言语上还有没有漏洞,理上是不是还有要补的地方。只要言语上没有漏洞就是好论文,就给你通过。他根本不问,罔顾事实,所以他可以论证“熟鸡蛋可以孵小鸡”。为啥这样的论文可以通过?是因为言语上可以说得滴水不漏。他可以用言语组织一个完满的理论系统。
天是有漏的,但是人可以用巧言令色把道理说得很圆满。所以后来我们人开始追逐圆满的道理,罔顾事实。人类不就这样堕落的吗?
所谓“忘”,即是得知道本末、先后、主次、利害。哪些东西只是工具?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工具。而我们那个真正的目的,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说的。但你不能把工具当做你人生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画家不以画画为目标。他不是轻慢画画,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目标,绝不是立志要当一个画家。所以“臣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所以孙过庭《书谱》说“书画小道,壮夫不为”,他为啥要这样说话呢?今天的这些书画家可不是这样说,那马上就要批判孙过庭,说孙过庭这样轻慢绘画也是不对的。你能听懂人讲的啥吗?所谓“壮夫”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顶天立地的汉子为的是啥?为的是成人成道,成为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大丈夫需要有个路径,这个路径是写字画画。我从黄山到杭州来,如果杭州是我的目标,如果杭州是我得道的一个所谓的“志向”,那我怎么才能到杭州呢?我自己开车,这是个工具,这是个载体。我坐动车,这也是个载体。原来的徽商要到杭州,他坐船,从新安江下来。如果还不行,他两条腿撒丫子走,走两个月来到了。总之你总得有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帮助你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工具,它叫“载”,“车载斗量”的“载”。
“文以载道”“画以载道”“技以载道”,三百六十行都是“载道”的载体,三百六十行都是工具。什么工具呢?使人成为人的工具。人来到这个世间志在成人,所以志向没有两个。志向只有一个,上天已经给你定好了。志向就是向度。人只要一生下来有了个人性,你就有天命了,你的天命就是你务必要这一生长成人。在长成人之前,饿死怎么办呢?所以为了不饿死,让神农氏来教你种庄稼,弄吃的。为了不冻死,让有巢氏来帮你弄房子,可以遮风雨。这时候就是先保护好脆弱的肉身,以给你留时间,让你有成人的可能,这叫“君子居易以俟命”。
《论语》为什么后来说“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就是最后,你一定得道才算是成了。我们说“成了”,“成了”啥意思?就是成人了。所以孔子是成大人的人,叫“大成”。孔子算是成了,大成至圣先师,这个封号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多高明。就是他成为大人了,他算是身体长高了,性命也充满了充实了。他是一个活得很饱满的人,他就是大人。我们一般人尽管有人形,也有吃有喝的,然后肉身也长到一米八一米九,最后生命并没有充实。没有充实,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样说这样的人啊?说“他终于活成瘪三了”,说他是个瘪子。“他活成瘪三”什么意思?他徒有一个躯壳,里面并没有充盈起来,浩然气没有充盈起来。所以孟子说要“善养吾浩然气”,使这个躯壳在本性中被充盈起来。这个才是一个充实而又光辉的人。
所以“言者所以在意”,他一步步朝里倒,都是打比方啊。“得意忘言”,这“意”是啥?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正需要交流的那个东西。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如何遇到一个真正能听懂人话的人?这才能讲话呀!这句话就是孔子对子夏说的“吾可以与你言诗”了,算是可以对话了。“言诗”就是可以“言志”了,“诗言志”,我可以跟你谈谈诗了,不是可以谈谈文学了。“诗”是借着语言来表志向。志向不可表,但是需要借语言,而在“诗”中的语言,不是语言的意义。“枯藤老树昏鸦”不是讲“枯藤老树昏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是为了讲个鸟。用打比方讲一个鸟比兴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用动物用鸟打个比方,结果一下子转到人那儿去了,讲到生命的气象那去了。也就是说,千说万说,千教万教,都为了导人归正。所以从孔子到陶行知都是在讲,如何成为一个真人的问题。如何因着语言,给人成为人做一个有效的提醒,你才不枉是识字一场。
题识:
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甲辰四月
连山
文稿由学人整理
听打:任锡珍、魏瑜、徐高伟
校对:子艮
编辑:闻和
连山先生著作推荐
庄敬身心,庄严国土。托不得已以养中。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愚者张真愿与诸仁,炮庄发药,自事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