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历史舞台上,不会有人真的忽视宋徽宗和宋高宗。两个人被记住,大多不是因为他们政务上的能力,而是因为作为皇帝犯过的错误让人难以释怀。这事儿很好理解,你要说宋太祖厉害,没人会反驳啊?可徽宗、高宗,他们谈政事就显得很别扭,总带着点尴尬。可一转身往艺术领域瞧,这两个人,居然比历史里绝大多数帝王都要耀眼。是谁规定皇帝只能会打仗?不能抚琴作画?咽喉之中总在问,这算是讽刺吗?
宋徽宗自小聪慧,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可他最爱的,偏偏不是端坐龙椅数钱谋国——而是溜进花间画竹题诗。宣和年间,无数文士云集宫廷,“翰林图画院”如盛极一时的艺术学校。徽宗主持下,北宋绘画体系极其严格,画家如工匠分科,每一笔都讲章法。谁能想象,徽宗拿自己的闲心,几乎奠定了后来数百年绘画标准。可他朝中的政务,也就是……乱得跟三月的雾霾天似的。是不是人真没法什么都兼顾?皇帝也罢。
很多人对宋徽宗的记忆不过是“靖康之耻”——金兵攻破汴京,上千皇家子弟被虏北方。可徽宗身上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超脱。当国破家亡,他面对世界的崩溃,却还能在北地写下“燕山雪花大如席”这类句子,心里那点艺术火苗始终不灭。可能换个人,早就哭天抢地了。徽宗做不到治国安民,却能写诗作画,这两种天分,很难说哪个更高贵。
他创立了瘦金体。横平竖直、干净利落、宽字紧结构,不遵古法,偏矫偏美,那种纤细里夹杂锋芒,一眼认出来就是他写的。有意思的是,宫廷女官都被要求练习这种字体,连日常档案也要“美如画”。大宋的美学趣味,全凭一个皇帝的审美来定。这事儿搁到今天,估计能直接上热搜。
徽宗信道好花,亲自划分天下花卉,每一品都要有传世图册,文官武将都跟着学,气氛热烈得不像朝廷。谁会想到,历史上最懂园林与山水、最会写字画画的皇帝,最后也能成为亡国之君。世事真的说不准,蛮荒与繁花一线之间。
说回宋高宗赵构。他比自己父亲能忍。那个“靖康之难”,他是极少数逃脱了金兵魔掌的人。就凭这一点,坊间猜测忒多。有人说他不思进取,有人说他曲意求全。可赵构不是个懦弱的人。他继位后,江山已碎一半,大宋只剩下南方那点地盘。可他就是靠着一点点,把宋室残魂聚到一起,不容易!只是,南宋的生存方式不同了,不硬拼,讲究保存自己。
治国算不上成功,战事也是屡屡折损。宋高宗其实心情很复杂,他一面要忍辱负重,一面要维持文人的自尊。他不像徽宗那么洒脱,心结更重,却不死心地想给自己留名于世。这事儿换作谁,也许都不会好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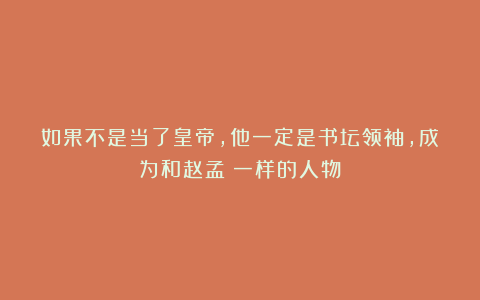
他和徽宗一样,被艺术治愈一生。书法,是他的难得慰藉。他的字不像父亲那般锋利奇谲,反而更厚重、含蓄。宋高宗非常推崇二王,从王羲之、王献之诸帖中寻摸刀痕。人说他的字气息柔和、筋骨藏锋,没有张扬的气焰,只有一股澹泊。赵构学书,旨趣在于求魏晋遗韵,他对米芾推崇,但总归希望自己的字像东晋风骨。为啥?大魏、大晋,都是在国祚动荡中,文人的精神依然在。会不会,他其实挺羡慕那点超然?
他的用功程度非常到位。宋人王明清称他勤临法帖,每天抄书不下百纸。江南翁同龢、陆游等人,甚至点评他“翰墨盖世”。但同时也有同僚背地里说,“皇帝写字,终究只是皇帝的消遣。”这话有点刻薄。可赵构这么着打磨、精进,书坛风气就变了。南宋书家一时风起云涌,元代的郑杓、赵孟頫这些大拿,都受过他影响。
要说矛盾也有。有时候觉得,赵构的才华不仅限于书法,他懂得诗、琴、画,甚至迷恋鉴赏、历代法帖的收藏,是全方位的文化皇帝。可看他上朝的章程和政策,胆子小得很,有点失望。而有时候突然站他一边,他这样做或许只是为了守住家底,别让国祚彻底断掉?说到底,大部分南宋读书人,也是这么想的。难为人家了。
现在风向变了。以前被人嘲笑的两位皇帝,渐渐开始被重新打量。尤其徽宗。他画鸟画花,小到羽毛细致,大到气势铺陈,世界都得服气。他的“瑞鹤图”被每日万人浏览,伦敦大英博物馆都乐意为之守夜。贵为天子,却能低头画鹤描花,妙得很。徽宗的瘦金体还在网络书法圈流行,10后都认得。
赵构所推崇的“复古”,过去被批评为守旧,现在有些人反感创新反而主动去临二王法帖,他的流行又回来了。历史就是摆动的钟摆,谁说准来回转到哪一侧。
艺术的繁荣,有时候建立在国家多难的土壤上,也见得多了。你看,两个人如果不是登上皇位,也许真能像宋初苏轼那样,隐居江南,安心钻研自己的天地,够自由。可上天并没有给他们选择。
有人觉得,“如果徽宗、高宗不是皇帝,或许会成为艺术圈第一把交椅。”这话太绝对了吗?不见得,有人在位反倒有资源,能调动最顶级的工匠资源,也有最高等级的自由度。可名与灾祸交杂着来,同样一张画,来自亡国之君和普通书家,心境怎会一样。真要论艺术高度,或许正是国事不能为,才让他们的内心世界爆发出的美术能量难以替代。
徽宗与高宗,其实都曾试图改变命运,但都没有逃开历史洪流,身上的艺术天分反倒成为历史清流。人未必真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可能一切不过是随机与偶然的错位。
有时反而怀疑了,这种命运也许可笑。可换一句,人性本就被境遇推着走。成王败寇、艺术余光,好和坏真的能够分得清楚么?偶有专家一边写论文一边在线吵,哪种说法能算数?还是现代人自己随便评判?
每回看到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瑞鹤图》,想起故宫南迁的国宝,一二十年里不停地奔波,就像徽宗眼中那抹残雪。再看看赵构那些清润的字迹,好像有某种历史斑驳的遗憾没有化解。想装作无所谓,偏偏心头堵得慌。大宋的皇帝们,终究用另一种方式,写下了他们的存在。这到底算是失败,还是另外一种胜利?
每个人都期待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却大多被命运胡乱安排,甚至连成为英雄或罪人,都是个误会。大宋的两位帝王,给后人留下了审美的样本,也留下了遗憾。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交错,每个人只能走属于自己的路。这事究竟该怎么看,也没个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