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们这个政治时代的书籍,会让人感觉仿佛被困在一间哈哈镜屋里。每一本书都承诺给出一个答案,一剂诊断我们政治体病症的良方,然而它们所映照出的影像,却往往和它们试图解释的现实一样扭曲。它们谈论极化,谈论部落主义,谈论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
但在这些术语和头条新闻之下,当你翻阅政治心理学、传播学和民主理论的文献时,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更为根本的诊断: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想什么,更在于我们如何思考。我们陷入了二元的束缚,退缩到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虚假安逸之中。
这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认知怪癖,一种已经演变为国民信条的思维捷径。在一个感觉复杂到令人恐惧的世界里,它散发着绝对主义的诱人魅力。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堆积如山——它们既是分析,也是哀叹,又是为这个四分五裂的共和国开出的自助手册——它们都在试图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关乎我们认知构造中的一个特性,一个简单的思维捷径,如何被我们的政治所武器化,又被我们的技术所放大,最终使我们的公共话语沦为一片废墟。
那么,这种思维习惯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当我们审视这片残骸时,这些作者中是否有人提供了一条可信的出路,一条通往灰色地带的回归之路?而一个功能正常的民主,必须生存在那片灰色地带。
理论化这场分野
心理学家用他们临床的、冷静的方式称之为“二分法思维”(或二元对立思维、非黑即白思维)(dichotomous thinking)。这是一种通过二元选项、通过两极对立的视角来感知和解读世界的倾向。这是心智退入了一个思想上的“门禁社区”,在那里,一切事物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细微差别的空间,也没有同时容纳两种矛盾想法的可能性。
文献向我们保证,这并非一种罕见的病态。它是一种认知默认设置,一种可以追溯到大脑最基本生存功能(趋近或规避)的返祖现象。孩子们就是这样学习世界规则的。麻烦始于,当这个发育阶段变成一种永久的政治状态,将成年人困在一种持续的“战斗或逃跑”模式中,此时,更高层次的推理能力被那种将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的原始本能所“短路”。
这种思维模式的语言是一个信号。它充斥着绝对主义的明显迹象:诸如“总是”、“从不”、“每个”、“完美”和“灾难”之类的词语。一个政治对手不仅仅是在某项政策上不正确,他们还是“邪恶的”。一个政党的纲领不是好坏参半的理念集合,它“总是”错误的。这通常与其认知上的表亲——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相伴出现,即从单个数据点跃升为普适法则的巨大跳跃。
一项失败的政策倡议,成了对方“永远”无法胜任治理的证据。这些都是更深层次的认知僵化的症状,一种无法适应新信息、在混乱世界中拼命需要二元分类所提供心理确定性的表现。这与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截然相反——那种罕见而珍贵的能力,能够拥抱细微差别,看到灰色地带,承认对手可以是错误的但并非邪恶的,且一项政策可以同时有利有弊。
历史学家提醒我们,这并非一种新的病症。围绕二元对立来构建思想的习惯,在西方有着悠久而传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他们给了我们“存在”与“非存在”、“理性”与“激情”的对立。这种通过互补对立来获得意义的知识结构,成为了思想的基石。但在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二元对立并非源于哲学家的论著,而是来自一次室内布局的偶然。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中,希望废除君主制的激进派坐在议长的左边,而希望保留君主制的保守派则坐在他的右边。从这张简单的座位表,诞生了那个框定我们两个多世纪以来辩论的简化政治术语:左派与右派,一场变革与维持现状的简单较量。
“右翼”与“左翼”这两个术语,正是源自当时的座位安排:“右翼”代表那些维护强者特权的人,而“左翼”则代表那些捍卫被排除者利益的人。
纵观历史,这种二元逻辑一直是动员和正当化的强大工具。宗教原教旨主义在神圣与世俗、信徒与异教徒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革命理论将历史描绘成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单一斗争。殖民计划则由一系列二元对立所支撑——文明/野蛮,主人/奴隶——这些对立通过将被殖民者描绘成低人一等的“他者”,来为统治提供合法性。
但没有人比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令人不寒而栗且在哲学上更严谨的辩护。阅读他1932年的杰作《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就如同遇到了我们当前困境的思想教父。对施密特而言,政治的本质,其不可简化的核心,就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他坚称,这并非隐喻。敌人不是商业竞争对手或个人宿敌。敌人是一个公共实体,是另一个其生活方式本身就对你的生活方式构成生存威胁的集体。政治,真正的政治,始于这种对立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包含了“实际肉体消灭的可能性”的那一刻。
施密特的作品是对自由主义的持续攻击,他认为自由主义试图中和这种生存冲突,用议会辩论和经济竞争来驯服它。对施密特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他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人民”,只有在将自己定义于一个共同的敌人之上时,才真正形成。“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篇关于他思想的分析文章这样写道,“除非他知道自己反对谁。”今天读施密特的著作,会让人感到一种不愉快的似曾相识。现代民粹主义的言辞——将移民描绘成入侵者,将精英描绘成叛徒,将政治对手描绘成人民的敌人——无论其是否自觉,都在使用一种施密特式的语法。
这就引出了哲学家提出的那个核心界线,那个困扰着所有这些文献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坚定的、有原则的信念止于何处,而有害的、教条式的思维又始于何处?前者是一种公民美德,是持续行动的基石;后者是一种认知恶习,是理性和对话的死亡。这些书籍表明,区别不在于一个人信念的内容,而在于他与信念之间的关系。
有原则的信念与认知谦逊(epistemic humility)是兼容的,即一种对自己可能错误的默然承认。它是一种愿意考虑新思想,在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前修正自己信念的准备。其认知过程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是深思熟虑探究的产物。
相比之下,教条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和确定性的姿态。教条主义者将自己的信念误认为普世真理。当一个政治立场被提升为“道德信念”时,它就成了一个不容谈判的事实,不受妥协或成本效益分析的影响。这种确定性通过僵化和自动化的认知过程得以维持,即依赖思维捷径和分类判断。对异议的回应不是参与讨论,而是不容忍。持异议者不是对话者;他们是敌人,要么愚蠢,要么心怀恶意。他们的论点不应被考虑,而应被驳回、忽略或压制。这便是我们时代的思想版图,在这片土地上,有原则信念的空间似乎随着每一个新闻周期而缩小,被教条主义者喧嚣的确定性挤占。
敌意的建构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关于我们国家衰落的书籍提供了一组我们熟悉的罪魁祸首,一个制造分裂的供需系统。需求来自我们内部,来自我们自身认知构造中的缺陷。供应则由那些精通极化艺术的政治精英提供。而整场交易又被社交媒体这个技术市场所加剧,其算法就是那只引导我们走向敌意的无形之手。
阅读认知心理学的著作,会让人因心智本身对简单性的追求而感到谦卑。我们并非自己想象中的理性行动者。我们的推理被一系列偏见所扭曲,这些偏见将我们推向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比如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即当新信息与我们珍视的信念相矛盾时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为了缓解这种不适,拒绝信息往往比更新信念更容易。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是治愈这种痛苦的强效药膏;如果那个不便事实的来源属于“邪恶”的外部群体,那么它的主张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被驳回。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加剧了这一点,即我们倾向于寻找、偏爱和回忆那些证实我们已有信念的信息。在一个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这导致我们长期接触着自我验证的内容,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使我们最初的信念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而这一切的底层是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即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处理信息不是为了探求真相,而是为了得出一个期望的结论——特别是那个能肯定我们身份和我们部落正确性的结论。支持我方的信息被点头接受;挑战我方的信息则要经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式的严苛审问。这些机制为简单的、肯定身份的叙事创造了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
现代数字生态系统已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冷酷高效的供应商。主流叙事,如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的《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The Filter Bubble: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一书所普及的那样,认为个性化算法正在为我们每个人创造独立的“信息宇宙”。通过学习我们喜欢什么并向我们展示更多同类内容,这些平台将我们与对立观点隔绝开来,将我们困在“回音室”(echo chambers)中,在那里,我们自己的信念被无休止地验证和放大。在这些数字围墙内,我们变得更自信、更极端,也更无法理解另一方。
《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然而,学术文献提供了一幅更复杂,或许也更令人不安的图景。一些大规模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实际上可能通过来自朋友和弱关系的“偶然接触”,让人们接触到比他们自己会主动寻找的更多样化的观点。这项研究表明,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算法,而在于我们自己。用户的自我选择起着巨大作用。虽然大多数人的信息食谱可能相当均衡,但一小部分高度参与且意识形态化的少数派,会利用这些平台有意识地为自己策划一个政治上同质化的世界。对于这些用户来说,社交媒体与其说是一个气泡,不如说是一个堡垒,一个用来放大自身确定性并向世界广播的工具。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敌意的建构者面前:那些精心打造非黑即白叙事并主导我们话语的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他们是这个分裂市场中的主要供应商。他们的技艺涉及一套精心磨练的修辞和情感策略。最基本的是部署“我们 vs. 他们”的语言。通过不断援引一个有德行的内部群体(“人民”、“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并将其与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外部群体(“精英”、“非法移民”)进行对比,他们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一场简单的道德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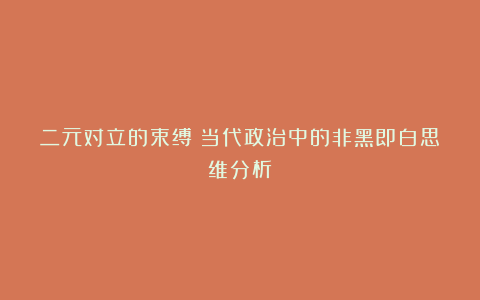
这种分裂通过情感动员而变得强大。特别是新民粹主义,在利用恐惧和愤怒方面堪称大师级。恐惧被用来将外部群体描绘成对国家文化和安全的生存威胁。愤怒则指向精英,他们被指责背叛了人民。这些情绪会“短路”分析性推理,使我们倾向于通过一种简单的、基于威胁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这种背景下,身份政治成了载体。当政治生活围绕着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身份轴心——无论是民族、种族还是政党——来组织时,它会扁平化我们复杂的自我,并培养对那些不共享该身份的人的敌意。结果是一个似乎并非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激活和赋权那些本就倾向于僵化、教条和二分法思维的人而设计的政治景观。
二元思维的代价
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那些记录我们民主衰退的书籍提供了一份严峻的账目。其后果并非抽象的;它们具有腐蚀性,正在败坏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制度。
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是公共政策。需要细致、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的复杂问题,被强行塞进虚假二分法的紧身衣里。正如大量事后分析所详述的,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成了这种失败的案例研究。辩论立即被框定为“健康与生命 vs. 经济与生计”的零和权衡,这个二元对立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场失控的大流行将摧毁两者。这个最初的虚假选择又催生了其他选择:“无限期封锁 vs. 无限制重开”,这种框架排除了更务实的中间地带策略。结果是公共卫生信息混乱,信任受损,以及悲剧性的无效应对。
类似的情形也困扰着气候变化的辩论,它被无情地框定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严峻选择。这种二元对立掩盖了不作为的巨大经济成本和绿色转型带来的机遇。它将辩论变成了一场关于价值观和指责的战斗,而不是对解决方案的务实探索,从而造成了政治僵局,使妥协看起来像是对原则的背叛。
超越政策层面,二分法思维还撕裂了社会结构本身。政治分歧从思想的较量转变为部落之间的冲突。“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或称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的兴起,是这类社会学文献的中心主题。党派身份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政策偏好的标签;它已成为社会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类似于宗教或种族。对部落的忠诚和对对手的敌意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部落主义加剧了社会信任的急剧下降。在美国,相信“大多数人可以被信任”的人口比例已经骤降。这种不信任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多数人都表示不信任投票给对方党派的任何人。这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使合作变得不可能,助长了阴谋论,并滋生了一种毒害公民生活的普遍敌意。
在这种有毒的环境中,建设性的公民对话枯萎死亡。当对手被视为心怀恶意的敌人时,对话的目标不再是说服或寻找共同点,而是击败对方并使其丧失合法性。跨越分歧的对话变得“充满压力和令人沮丧”,并被简单地回避。人们退回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孤岛中,造成了一个强化和深化极化的恶性循环。“民主辩论的失落艺术”被一种充满不文明和僵局的“粗鲁民主”所取代。
最终,这种腐蚀蔓延到民主制度的根基。当政治是一场零和博弈时,那些本应作为中立仲裁者的机构就成了另一片战场。对选举结果的信任蒸发了。一次失败不是政策上的挫折,而是一场生存上的失败,这使得失败方容易接受关于舞弊和选举被“窃取”的说法。像司法机关这样的中立机构被攻击为党派行动者。当法院做出不利裁决时,它不被视为法律的适用,而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导致对司法独立的攻击。而拒绝与“敌人”妥协直接导致了政治僵局。主要目标不再是治理,而是确保对方一事无成。这种瘫痪不仅妨碍了紧急问题的解决,最终还侵蚀了公民对民主作为一种可行治理体系的信心。
寻找解药
在如此严峻的诊断之后,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这些书中是否有任何一本提供了治愈之法。是否存在摆脱二元束缚的解药?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种多样,从个人精神卫生到宏大的系统性改革。
这一系列著作中的“自助手册”部分侧重于个人。如果我们的认知偏见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解决方案必须从重新连接我们自己的大脑开始。这些作者借鉴认知行为疗法(CBT),为个人去极化提供了一套工具。它始于注意自己的用词,识别并挑战使用如“总是”和“从不”之类的绝对主义语言。它涉及有意识地列出其他可能性以打破“非此即彼”的框架,并练习换位思考以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
第二套个人工具属于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范畴。在一个充斥着虚假信息的世界里,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来源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技能。这意味着在接受一个主张为真之前,要质疑假设、识别偏见、核实来源并寻求不同观点。这些都是对批判性思维这一更广泛承诺的组成部分,而批判性思维是抵制简单化叙事的根本解药。教育文献坚持认为,这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而是必须被教授和实践的,最好是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法等方法,迫使学生从多个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推理。
但个人的努力感觉就像用滋水枪去救森林大火(杯水车薪)。一批更具雄心的作者认为,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该模式涉及召集有代表性的公民群体,进行长时间、信息充分且有主持的讨论。“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ies)等现实世界实验的证据惊人:当人们在这些条件下进行审议时,基于议题的极化和情感极化都急剧下降。他们不仅在政策上更加靠拢,而且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也产生了更大的尊重。
另一个改革目标是选举制度本身。在美国常见的“赢者通吃”制度被视为极化的主要驱动力,它鼓励了一个两党垄断的局面,候选人只需迎合狭隘的基本盘。像排序复选制(Ranked-Choice Voting, RCV)这样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来改变激励机制,在这种制度中,选民按偏好对候选人进行排序。为了获胜,候选人必须争取成为其对手选民的第二或第三选择,理论上这会带来更文明的竞选和更倾向于共识的领导人。
最后,还有人际层面——我们之间的空间。在这里,文献提供了弥合分歧的技巧,一次一次的对话。像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这样的框架试图通过关注我们政治立场背后普世的人类需求来重塑冲突。其目标是从一场关于谁对谁错的辩论,转变为共同寻找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解决方案。一种更新的,或许也更有效的方法是深度访谈(deep canvassing)。这种方法超越了传统的竞选话术,专注于非评判性的倾听和脆弱地分享个人故事。严谨的研究表明,这些简短而充满共情的对话,即使在最根深蒂固的问题上(如LGBTQ+权利和移民问题),也能产生持久的态度转变。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一个激进的前提:建设性对话的主要障碍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人际连接的缺失。
窥探未来
我们正走向何方?这些书的最后几章通常是最具推测性也最令人不安的。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宏观趋势呈现出一幅矛盾的画面。虽然更紧密的互联本可以培养细微思考,但它们产生的经济和文化焦虑往往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我们 vs. 他们”这种简单而确定的叙事。
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人工智能(AI)的幽灵。AI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双重用途技术,它既有能力成为二元思维的终极加速器,也有潜力成为促进细微思考的强大工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且迫在眉睫。AI可被用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成超个性化的虚假信息,制造深度伪造(deepfakes)和量身定制的宣传,这可能会粉碎我们共享的现实感。它可以极大地加剧社交媒体的算法极化,在满足我们对情绪化、分裂性内容的胃口方面变得更加冷酷高效。
然而,还有一条更充满希望、尽管可能性较小的道路。AI可以被用来创建复杂的事实核查和媒介素养工具。大型语言模型可以被训练成“细微差别引擎”(nuance engines),从多个视角总结复杂的辩论,帮助用户识别逻辑谬误和虚假二分法。作者们警告说,这个选择将不是一个技术选择,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选择。当前数字世界的商业模式绝大多数都与AI的加剧功能保持一致。如果没有一次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干预,将我们信息生态系统的健康置于原始互动量之上,那么默认的轨迹将是黯淡的。
纵览这片庞大而焦虑的文献,会让人感到一种深刻的挑战,但并非完全绝望。“二元束缚”并非偶然。它是一个由心理脆弱性、政治犬儒主义和技术加速共同作用的强化系统的产物。要瓦解它,需要一套同样整合的策略:改革我们的制度以奖励妥协,教育我们的公民以珍视复杂性,并重新发现那种旨在理解而非取胜的对话艺术。它要求我们抵制简单的故事,拒绝轻易树立的敌人,并拥抱那艰难、混乱但不可或缺的、生活在灰色地带的工作。简而言之,它要求我们去思考。
END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