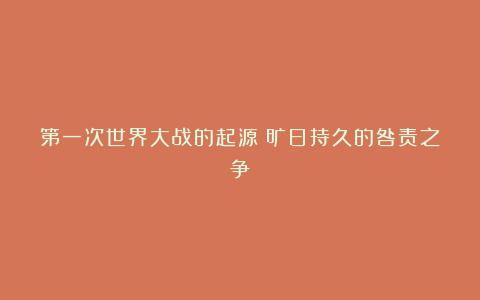书名: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Long Blame Game(《一战诸因:旷日持久的咎责之争》),2024年;初版为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ontroversies and Consensus(《一战诸源:纷争与共识》),2002年
作者:安妮卡·蒙鲍尔(Annika Mombauer)
译介:存真社
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自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引入“战争罪责”这个概念以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们就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指责游戏”。在探寻战争根源的漫长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发掘了大量原始资料,撰写了浩如烟海的文献,使得这场战争成为“迄今为止历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国家间战争”[1]。正如历史学家乔治·P. 古奇(George P. Gooch)在1938年指出的那样,“世界大战的悲剧性部分就在于,每个交战国都能为自己构建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脱责)理由”[2]。
九位君主齐聚于温莎,出席爱德华七世国王的葬礼,摄于1910年5月20日
本书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为何历史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争论持续了如此之久且如此激烈?为何他们至今仍未能达成一致?本书探讨了人们长期以来执着于(却又无力)解释战争根源的原因,并引导读者们穿越纷繁复杂的争论迷宫。它追问: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对战争起源问题的理解始终存在分期?以及,为什么他们在一个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所拥有的证据比任何其他历史事件都多的问题上仍能对此各执一词?简而言之,为何这场“指责游戏”如此得漫长?
本书旨在探究推动这场百年辩论的环境因素以及参与者的动机,而非单纯叙述或解读引致战争的一系列事件[3]。它考察了为何在特定时期,关于一战起源的某些特定观点会脱颖而出,并表明占主导地位或新兴的解读往往与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这场循环往复的辩论中,各种解释不断被修改、推翻,然后又被新一轮的修正主义浪潮所取代。这或许并不稀奇。正如 T. G. 奥特(T. G. Otte)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修正主义的。”[4]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与持续时间。本书也就这场辩论为何持续如此之久,以及为何很可能继续持续下去,提出一些思考。
地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势力分布图的颜色标记说明,其中红色代表同盟国,绿色代表协约国,黄色代表中立国。
后续的章节将分析从1914年直至百年纪念之后的辩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有三个时期各方分歧尤为强烈。每次都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正统观点,一部分历史学家试图推翻它,而另一部分则竭力维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正主义者力图修订协约国在凡尔赛作出的战争罪责裁决;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在《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中提出的一战起因学说,即“费舍尔论题”(Fischer thesis),改变了历史学家们先前认为“各国都难辞其咎又皆可免责”的共识,这令那些持传统观点者深感不安;而在战争百年纪念前后,有历史学家再次修正了原有共识——强调德国对战争负有更大责任,但遭到了不认同此种重新诠释的学者的强烈反对。
《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随着每一轮辩论的进行(以及争议较少的修订期间),更多证据被发掘,无数文章和书籍付梓出版,这使得学生、教师乃至专业学者都越来越难以理清不同的论点。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在1929年总结了研究战争起源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阅读数万份外交文件,搜寻并审度数百名证人的证词,穿越争议和辩论的迷雾以寻求偶然的突破性发现——这就是着手探究……世界大战起源这一关键问题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5]。
如果说在1929年似乎已是荆棘载途,那么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后,这一任务并未获得任何放松。[6]
本书探讨了导致这场辩论持续不止的一些因素。例如,战争伊始,各国政府就极其擅长利用宣传来为辩护自己在催发战争之事件中的无辜。他们在战争期间如此,战后亦然。其中一些宣传具有持续的说服力,并在多年内影响了相关解读;这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政府官方出版物和学术文献汇编中对证据的篡改伪造则使争论变得更加复杂。有时,历史学家近乎侦探,试图从过去挖掘证据以拼凑出1914年发生的事件。他们不得不耐心等待国家档案馆的开放(有些需在事件发生50年后)。他们必须学会不轻信经过编辑的证据,并在档案中进行对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实。他们的进程受阻,因许多文件的散佚——或是被作者故意销毁,或是毁于二战的战火之中。尽管如此,他们仍对现有史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就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
战争本身的性质也是使得这场辩论如此漫长且充满争议的另一个原因。它给数百万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不仅在亲历者中引发了错综复杂的情感反应,也惹得后世研究该主题的历史学者们心绪缭乱。由战争导致的空前灾难催生了一种问责文化(事实上这正是《凡尔赛条约》中前所未有的战争罪责指控的体现),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德国国内的防御性姿态,并对这种指责矢口否认。除了战争结束时亲历者们遭受的直接冲击之外,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战争罪责指控以及战争本身可怖的性质和后果产生着情感共鸣。在战事发生的数代人之后,这个话题仍未完全归入历史,百年纪念期间在德国和塞尔维亚上演的公开论战,正是这一点的生动注脚[8]。
战争归责的问题之所以持续引发关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被视为二十世纪“重大灾难性开端”(the great seminal catastrophe)[9]。它开启了一个战争的时代,而后又为一场更为巨大的冲突所取代,而许多人认为二战的种子早在1914年就已埋下。1945年后,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存在关联的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前者的起因,同时西德也再度否认其前身德意志帝国发动了1914年的战争。同样,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的基础,冷战也是难以理解的。鉴于二十世纪的热战与冷战交织并存,此时对1914年战争爆发负责的利害关系甚至比1919年时更高:这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道德负担。对西德而言,一战起源问题已演变为关于德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侵略性之延续的争议,这直接动摇了1945年后两德统一的任何希望。
最后,1914年危机升级的过程似乎也为避免未来可能的战争提供了教训,以持久作为历史的警示符。从古巴导弹危机到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再到2014年(恰逢七月危机过去整整一百年后)的克里米亚危机,人们常常将这些当代冲突与1914年动荡的局势相提并论。鉴于这种当代关联性,该议题对“国际冲突诸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10]。它吸引了政治科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分别运用“均势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同盟理论、经济相互依存理论、攻防理论,以及替罪羊机制、僵化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错误认知理论”等进行研究。正如杰克·S. 利维(Jack S. Levy)和约翰·A. 瓦斯克斯(John A. Vasquez)所解释的,这场冲突常被用来“阐释和检验各类国际冲突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几乎每一位国际关系冲突理论家都无法回避的研究案例”。他们特别指出,关于一战的史学争论强调的诸多论题,与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议题高度重合:
仅举几例:结构与能动性;国际与国内诱因的相对重要性;个人特质与信仰体系的因果作用;决策过程的理性与连贯性;安全困境的动态变化;国际规范与制度的功能;以及战略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11]。
这便是该议题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吸引着专业历史学者以及非学术界人士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并未完全解释为何历史学家未能就战争成因达成共识,亦未能解释学者们在争论之时的剑拔弩张。
协约国代表在凡尔赛宫镜厅,见证德国代表接受《凡尔赛条约》各项条款
几十年来,层出不穷又往往相互矛盾的解读令人眼花撩乱。这场争论最初围绕着《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war guilt clause)展开——该条款将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同盟国,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家随后依据所能获取的官方文件,开始就文本的细节与语境展开辩论。某些观点还引发了分支讨论,例如学者们曾就特定人物的意图以及历史责任展开辨析,其中包括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也成为争议焦点,有些人指责他在七月危机期间的优柔寡断。他们对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责任认定也存在分歧,指控他怀有打一场复仇战争的意图。此外,诸如驻伦敦的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Max von Lichnowsky)和驻圣彼得堡的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这样的大使的影响力也被置于显微镜下仔细审视。当然,青年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及其同谋者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行为,更是被反复剖析。
历史学家们始终针对各种军事与海军计划的重要性及意义展开辩论——无论是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蒂尔皮茨计划(Tirpitz Plan),还是法国第十七号计划(Plan XVII)。他们既争论这些动员行动的时机选择与后续影响,也对1914年夏季究竟何时踏上了战争的不归之路、又是谁的决策最终将欧洲推向战争边缘这些问题存在分歧。对于通过档案研究发现的若干史实之重要性,学者们亦存在分歧:例如1911年8月的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这是否标志着英国已决心在德法战争中支持法国,从而奠定了英德军事对抗的基调?),或是1912年12月德国’战争会议’(此次会议究竟是标志着德国领导人确认了开战决心并将战争推延至1914年夏季?抑或其本身并无实质重要性?)。他们争论英德的海军军备竞赛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英国在1914年选择参战究竟是为了捍卫帝国利益,还是为了保护比利时?对原始史料的真实性与学术价值,他们论辩激烈。在预防性战争的概念辨析及战争目标的性质界定问题上亦始终存在分歧。论点的对立往往取决于对细枝末节的剖释或对同一证据的不同解读,从而导致历史学家们得出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无怪乎研习者与历史学者都会对此争论感到无所适从。
原始史料始终是这场论争的基石。前所未有的是,战争爆发伊始,各国政府便纷纷公布了他们的外交机密文件——名义上为表示己方在导致战争爆发的事件中的清白,实则是为揭露他国的责任。这些文件都经过谨慎筛选,只保留了那些能够佐证其立场的史料。战后,各国又陆续披露了更多官方档案,声称要揭露欧洲各国内阁的内幕决策。的确,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厘清从萨拉热窝的致命枪击到8月初各国宣战的时间链条,或者追溯更早的根源,阐释那些导致欧洲走向1914年夏季外交对决的事态进展。事实上,关于1914年“七月危机”事件本身,学术界并无太大分歧,但对于如何解读这些事件、如何评估决策者的意图及其决议之重要性,以及如何判断谁的决策最终导致七月危机升级为欧洲战争,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尽管已有大量史料,历史学者已然难以就这些问题达成定论。
大战之前的欧洲外交阵营。奥斯曼帝国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德国。意大利在1914年保持中立,并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
本书采用时序框架切入主题。开篇首章剖析战时及战后初期的争论,彼时,各方的无罪宣传逐渐让位于《凡尔赛条约》所确立的“战争罪责条款”。这份裁定使得否认德意志帝国的开战,成为德国政学两界的核心关切,一场漫长的论战由此拉开序幕。
第二章聚焦两次世纪大战期间的学术论战,当时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与反修正主义者纷纷围绕着《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的战争罪责指控展开激烈交锋。这场辩论最初由数届德国政府主导推动,他们竭力证明德国在1919年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为此后的一切讨论定下了基调。在1920年代,修正主义者与反修正主义者曾并行存在,双方皆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和广泛的非学术受众。然而,在德国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其中多人受雇于德国外交部)的共同努力下,主流舆论逐渐发生扭转。直到1930年代初论战首达高峰时,将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观点已不复主流。
第三章着重考察了这一在二战后得以存续的基本共识,如何在1960年代遭受到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颠覆性质疑。他不仅将主要的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从而复兴了1919年协约国的主张,更论证了德国在1914年所推行的侵略性战争目标,揭示出从一战到二战之间令人不安的战略延续性。他观点引发了所谓的“费舍尔大辩论”(Fischer controversy),将讨论推向第二次高潮,此时该议题的影响远超越学术领域,进入了公众视野。随着辩论渐息,国内外学界共识再度转向,普遍认为德国相较于其他强权更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
第四章旨在剖析二十世纪后期发生的范式转型:历史学者逐渐超越费舍尔学派的德国中心范式,通过研究其他大国的行为,从而为1914年夏季及之前的决策过程构建更为完整的图景。
最后一章(第五章)探讨了在百年纪念前夕及期间再次兴起的学术辩论。部分缘于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梦游者:欧洲如何走向“一战”》(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一书的出版,既有共识再次受到挑战。随之而来的公开论战充分表明,战争起源的探讨始终与当代关联,并能持续引发公众的关心:在塞尔维亚,修正主义的论调冒犯了现代人的民族情感;在德国,公众辩论的再兴起更证实了战争起源问题始终未归入历史档案。
《梦游者: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德国在这场争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原因主要如下:首先,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协约国将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自那时起,魏玛政府便将驳斥这一指控作为其使命,从而引发了相关论争。也正因为《凡尔赛条约》明确写入的“战争罪责条款”,学术争论始终聚焦于“德国是否应承担罪责”这一核心问题。因此,尽管并非所有修正主义学者都来自德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早期修正主义著作仍大多集中于德国出版。
IMPERIUM ROMANO-GERMANICUM oder DEUTSCHLAND MIT SEINEN ANGRÄNTZENDEN KÖNIGREICHEN UND PROVINCIEN.
地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及其毗邻王国和行省图。由普法尔茨选侯国的Julius Reichelt(1637–1717)设计并部分绘制。在18世纪期间,该地图出现了许多衍生版本。本幅复刻版由尼古拉斯·费舍尔二世(Nicolaes Visscher II, 1649–1702)出版。
其次,战争罪责条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场争论。自1919年以来,关于战争起源的探讨都不得不以’德国罪责’为出发点——不论历史学者们试图论证德国确实发动了战争,还是强调某个或多个大国也应共同承担责任,抑或主张不应将责任归咎于任何特定政府。
其三,最激烈且最富争议的辩论始终在德国本土展开——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学术交锋、1960年代的’费舍尔争论’,还是2010年代初百年纪念时的争论。尽管这三个阶段有关战争起因与德国罪责的讨论均吸引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各国历史学家的参与,但唯独在德国,这些争论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公共辩论浪潮。正如多米尼克·格珀特(Dominik Geppert)所指出的:
在德国,关于国家立场的争论往往以历史辩驳的形式呈现——这一现象远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正因如此,历史争议也因而常备高度政治化,甚至带有令国外旁观者侧目的道德批判倾向。[12]
因此,史学论述的重要部分始终围绕着德国的学术论争展开。
简言之,若无德国在《凡尔赛条约》后主动挑战所谓’战争罪责谎言’的举动,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大打折扣。当然,有人或许会指出,倘若最初根本不存在战争罪责的指控,争论本身便无从产生——但这已属于另一层面的讨论了。无论在何种分析中,德国始终处于核心。因此,本研究虽聚焦于历史学者如何阐释德国在战争起源中的扮演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排除国际史学界的多元观点。尽管德国是否应当承担罪责已成为大多数(即便非全部)论述或隐或显的前提,学者们早已超越协约国单一归因的论断,转而通过考察所有大国乃至部分小国的决策过程,以追溯战争根源。本书力求客观地呈现多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虽难以涵盖所有相关著述,但仍试图从多维度、多视角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复杂成因。[13]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研究战争长期成因的学者往往以德国中心范式为参照来选择起始点。多数论述始于德意志击败法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并实现统一的1871年。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设计了一套联盟体系,旨在防止其他国家形成反德同盟,即他所警惕的’联盟噩梦’(nightmare of coalitions)。他宣称新统一的德国在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后已达到’饱和’,不再寻求与邻国发生冲突,并随之通过缔结一系列(时而相互矛盾、时而秘密进行的)盟约来保护德国免受潜在敌人的威胁。1879年,德国和奥地利结成两国同盟,其后在1882年因意大利的加入实际上演变为三国同盟。1887年,俾斯麦又与俄国秘密签订《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承诺在对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这一安排事实上与德奥盟约存在矛盾)。
Vom Fels zum Meer für Deutschlands Ehr!, postcard, 1914
This German postcard from 1914 shows Wilhelm II symbolizing the “rock” and the German Navy in the background. The title reads: “Vom Fels zum Meer für Deutschlands Ehr!” (“From the rock to the sea for the honour of Germany!”).
这张1914年的德国明信片上,德皇威廉二世如岩石般巍然屹立,背景则是德国海军。标题写道:“Vom Fels zum Meer für Deutschlands Ehr!”(“从岩石到海洋,一切为了德国的荣誉!”)
作者不详。来源: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基金会。
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后,俾斯麦精心构建的联盟体系开始走向瓦解。在这位新君主反复无常的领导之下,为了实现成为“世界强国”(Weltmacht)的野心,这个雄踞欧洲中心的德国开始挑战周边邻国,后者则为应对这一威胁纷纷结成防御性同盟。1894年,法国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此举反而给德国施加了被“包围”的压力——此时,德意志帝国的东西两线均面临着潜在敌人。[14]
航行中的英国无畏号战列舰(HMS Dreadnought),约1906-07年
紧接着,英国与法国于1904年签署《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虽未结成正式同盟,但这一松散的安排在1905-1906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得到了显著强化。实际上,通过法国这一共同的盟友,英国和俄国也形成了阵线的联合。1907年,英俄又单独达成协议,使得这一友好关系更为稳固持久。至此,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已形成对峙之势,任何成员国之间的冲突都可能将所有主要的欧洲列强卷入战争旋涡。
1909年的漫画“Puck”展示了五个国家正进行着海军竞赛,凯撒穿着白色服装。
德国通过大规模造船计划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企图打造足以与英国抗衡的海军实力。由此引发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不仅加深了两国政府的相互猜忌,也加剧了两国民众之间的敌意。[15]英德关系的持续恶化,被普遍视为1914年前欧洲战云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柏林与伦敦曾尝试达成友好协议(如1912年’霍尔丹使团’谈判),但最终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16]
英国政府面临着关键抉择:在欧洲大陆强国之中,谁将是更有价值的未来盟友?谁又是更令人担忧的潜在敌人?英国在1914年8月决定参战,实际上是基于多重顾虑。若德国胜利占领法国海峡沿岸,必将对英国构成直接威胁;而若俄国取胜则可能危及大英帝国的利益——尤其是在印度的统治。英国外交部部分官员认为,未来来自法俄联盟的敌意对于帝国的威胁可能远甚于德国。[17]
在这种紧张的外交局势之下,欧洲爆发战争实属意料之中,而巴尔干危机成为冲突的导火索亦不足为奇。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巴尔干地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塞尔维亚急于扩张势力范围,对奥匈帝国构成直接威胁;俄国亦以泛斯拉夫主义保护者自居,为塞尔维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围绕着出海口的争夺、君士坦丁堡海峡(该海峡是通往黑海的要道)的控制以及领土扩张问题,巴尔干地区冲突不断。对奥匈帝国而言,这一威胁尤为严重,因为这个二元君主国本身统治着众多民族,而其中部分民族渴望着独立。民族主义的诉求与领土扩张的欲望使得巴尔干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冲突之中: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吞并危机便是一场几乎引发欧洲大战的严重外交争端。1908年,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政局动荡。[18]奥匈帝国趁机吞并了自1878年《柏林条约》以来实际由其占领、但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宗主权之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19]由此引发的外交危机几乎将欧洲推向战争边缘,德国向奥匈承诺提供无条件支持,而俄国对塞尔维亚的外交调解最终避免了战争的爆发。
德国对盟友公开且无条件的支持,彻底改变了两国联盟的性质。自此,奥匈帝国领导者深信,即便因自身行动引发国际危机,也有德国能够依赖。而俄国与塞尔维亚在此次事件中的被迫让步,使其国际声誉严重受损,因此未来两国再度退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辱的塞尔维亚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谋求其在巴尔干地位的恢复,而俄国也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后决意重整军备。随之而来的欧洲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紧张。[20]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
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26年至1931年间担任自由党领袖,并在1916年至1922年间兼任英国首相,领导战时内阁。
1911年,法国出兵镇压摩洛哥叛乱后,德国出手干预,要求以割让法属刚果作为承认法国在摩洛哥势力扩张的补偿。然而,与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如出一辙的是,法国再次得到了英国支持,英法协约关系由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于1911年7月21日发表著名的“宅邸演说”(Mansion House Speech),明确表示英国在必要时将不惜与法国并肩对德作战,这一强硬态度在德国国内引起强烈愤慨。尽管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德国获得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作为象征性补偿,但事实上这是德国外交的又一次挫败。此外,奥匈帝国在此过程中对德提供的支援含糊而有限,表明这个盟友未必可靠。德国决策层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唯有巴尔干地区的危机,才能让奥匈帝国毫不保留地提供全方位支持。
新一轮的巴尔干危机接踵而至。1912年,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结成巴尔干同盟,并于同年10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奥斯曼军队迅速溃败,但战胜国之间随即因瓜分战利品而反目,并最终在1912-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兵戎相见。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的领土面积扩大一倍,对奥匈帝国构成的威胁更甚。这一认知直接影响了维也纳方面对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据称受到塞尔维亚煽动)所做出的反应。鉴于巴尔干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塞尔维亚崛起所带来的压力,此次刺杀被视为对二元帝国国家威信与国际声誉的严重削弱。弑君行为使维也纳的政治家们在道德上占据高地,并增加了其他大国站在奥匈这边的可能性。若能确保德国盟友的支持,那么这次刺杀事件便可能成为一举解决塞尔维亚威胁的战略良机。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的事件,常被形容为点燃整个欧洲的火星——彼时这片大陆因国际局势的紧张而四处充斥着火药味。事后看来,似乎在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打出致命子弹后,战争已不可避免。然而,这场战争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人为意图的悲剧——刺杀行为本身并未直接导致战争。
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与妻子霍恩贝格公爵夫人苏菲(Sophie),坐在萨拉热窝的敞篷马车里。照片摄于1914年6月28日。
维也纳官方针对这次刺杀事件的反应是惊愕的,尽管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生前并非广受爱戴。奥地利领导人,尤其是奥地利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策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则将其视为对塞尔维亚开战的极佳借口。当奥地利政府向德国征询意见时,德国向其盟友奥匈帝国保证会提供支持,即便对塞尔维亚动手可能会引发欧洲大战。这就是德国给维也纳开的“空头支票”。德皇威廉二世还敦促奥匈帝国’把握当前良机’,他认为此时局势极为有利。[21]
在得到德国的上述保证后,奥匈帝国部长理事会于7月7日决定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被蓄意设计得难以接受,以便让塞尔维亚拒绝,从而为维也纳提供宣战借口。通牒的送达时间也被推迟:一方面是由于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士兵正值收割假期,另一方面是决定等到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访俄行程结束,以免两个盟国就最后通牒进行及时协调。在此期间,维也纳和柏林政府严守秘密,并安排核心决策者照常休假,以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正是凭借这种欺瞒手段,其他主要大国在七月危机中几乎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直到7月23日通牒最终送达了贝尔格莱德。
奥匈帝国, 1914年
塞尔维亚政府虽未全盘接受奥方的所有要求,但做出了显著让步,其妥协程度让奥匈帝国预先决定拒绝贝尔格莱德的答复并排除进一步调解的做法,在其他欧洲列强眼中显得十分可疑。甚至连威廉二世此时也认定已无继续发动战争的理由。7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提议召开一次调解会议,但此倡议再遭奥匈拒绝。同日,沙皇政府批准了对四个军区实施部分动员。与此同时,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押注英国会保持中立。直到英国明确表示将在欧战中援助法国时,他才真正支持调解,但为时已晚。英国内阁对是否介入欧战一事存在分歧,在德国侵犯中立比利时之前,都没有就支持法国作出明确决定。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若更早申明援法意图,或能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有观点认为,如果德国决策层能更早确知英国会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他们本可能支持调解方案并劝谕维也纳保持克制。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英国提早表态是否真能通过制约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改变结果;同时也有可能反过来促使法俄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正是在这一点上,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七月危机期间作出的决策尤为受到抨击。[22]
美国《洛杉矶时报》(The Times Los Angeles )在1914年7月29日的头版
当英国的参战意图明朗化后,德国首相虽试图约束奥匈帝国,然已无力回天。奥匈帝国于7月28日与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并宣战,由此触发了欧洲列强接连动员与宣战的多米诺效应:7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次日实施总动员。该动员导致德国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德法同日启动总动员。8月2日,德军入侵中立国卢森堡并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次日,德军入侵比利时,并向法国宣战。意大利宣布中立。由于德国为执行“施里芬计划”而入侵中立的卢森堡和比利时,英国于8月4日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对俄国宣战,至此完成了所有大国卷入战争的宣战链条。此时,同盟国(不包括意大利——该国直到1915年5月保持中立,之后才加入对立阵营)与协约国之间这场被许多人视为历史必然的’伟大战争’,全面爆发。[23]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某些决策背后的动机仍存在重大分歧,但普遍认同一点:所有主要参战方的决策者都未曾预料这场战争的规模与破坏性会如此之大(即便他们未必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是短暂的)。每一方都相信自己能够取胜。战争甫一爆发,各国政府便动用宣传机器让民众相信,他们是在打一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随着战事拖延与伤亡人数激增,证明本国在战争爆发时的“无辜”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在战火尚未熄灭之前,关于战争起源的论战便已拉开序幕。
海报描绘了一只佩戴红色腿环、身披皇冠绶带的鸡。文字:“招募战时入伍人员”,“为支援伤员在全国征集鸡蛋”。R.G. Praill设计,伦敦W.C.大道出版
战后,追究责任与索取赔偿成为首要关切。对于协约国而言,这是为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争取补偿的必要步骤;而对被迫承担战争罪责的德国来说,这不仅涉及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也关乎国家荣誉。可以说,战争起源问题从未像在战后初期那样具有如此的重要性——魏玛德国因被指控挑起战争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遭受重创,民族自尊受挫,新共和国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若能够证明罪责认定的不公,德国将获得巨大挽回空间。正因如此,我们将首先将目光投向战后初期那些围绕战阵起源所进行的激烈论战。
1 “引言: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Jack S. Levy和John A. Vasquez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构、政治与决策》(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cture,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剑桥2014年版,p. 5。
2 George P. Gooch,《战前外交研究(第二卷):风暴来临》(Before the War. Studies in Diplomacy, vol. II, The Coming of the Storm),伦敦1938年版,p. v。
3 本人关于战争起源的观点已另文发表,但在此史学述评中力求不予突出。当然,鉴于该争论的本质,恐难令所有学者满意。
4 T. G. Otte,《1914年的缓和:威廉·蒂勒尔爵士赴德秘密使命》(Détente 1914: Sir William Tyrrell’s Secret Mission to Germany),载于《历史学刊》(Historical Journal)第56卷第1期(2013年3月),pp. 175–204, 175。
5 Pierre Renouvin,《战争如何降临》(How the War Cam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3卷(1929年4月),5pp. 384– 97, 384。
6 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此处不太可能给出一个全面的综述。未能涵盖所有对这一争论有所贡献的历史学家,亦非所有的研究方法或论证细微之处都得以呈现。若有疏漏,冀望不致造成冒犯。
7 例如“里茨勒日记”(the Riezler diaries)的出版历程漫长曲折,其本身已引发学术争议,第三、五章将作探讨。
9 此术语源自George F. Kennan,《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微:1875-189年法俄关系》(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新泽西普林斯顿1979年版,p. 3。
10 Jack S. Levy和John A. Vasquez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构、政治与决策》(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cture,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剑桥2014年版,p.4。
12 Dominik Geppert,《帝国的多副面孔:倡导历史多元性》(Die vielen Gesichter des Kaiserreichs. Ein Plädoyer für mehr historische Pluralität),载于《自由主义研究年鉴》(Jahrbuch zur Liberalismus‑Forschung)第34卷(2022年),pp. 13–25, 14。类似观点参见其《新民族主义?论德国抹黑帝国的需求》(Neuer Nationalismus? Vom deutschen Bedürfnis, das Kaiserreich schwarzzumalen),《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2021年5月3日。
13 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外交进程的详细论述已超出本书范围——本书重点在于战后的学术论争而非事件本身。以下仅对战前欧洲政治史作简要时序梳理,旨在为后续争论分析提供背景。推荐阅读James Joll与Gordon Martel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第四版,伦敦2022年)作为基础导论。
14 本书后续章节将表明,即便这段概述也存在解释空间:德国是否真正威胁邻国?抑或其他大国只是不愿接纳这个新的崛起者?德国是被包围了,还是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孤立(德语称Auskreisung)?抑或所谓的包围只是某些德国政客过度亢奋的想象?
15 参见Volker R. Berghahn《蒂尔皮茨计划:威廉二世时代国内危机战略的生成与破产》(Der Tirpitz‑Plan. Genesis und Verfall einer innenpolitischen Krisenstrategie unter Wilhelm II,杜塞尔多夫1971年);同作者的《德国与战争的临近》(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第二版,伦敦1993年);Paul M. Kennedy《德国对英海军作战计划的发展(1896-1914)》(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Naval Operations Plans against England, 1896– 1914),载于其主编的《列强战争计划(1880-1914)》(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14,伦敦1979年);同作者的《英德对抗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伦敦1980年);Michael Epkenhans《威廉时代海军军备(1908-1914):世界强权追求、工业进步与社会整合》(Die wilhelminische Flottenrüstung 1908–1914. Weltmachtstreben, industrieller Fortschritt, soziale Integration,慕尼黑1991年)。英文简论可参阅Volker R. Berghahn《德意志帝国(1871-1914):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牛津1994年)。关于历史学家对英德竞争性质的争论见第四章。
16 详情参见R. T. B. Langhorne《英国与德国(1911-1914)》(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911–1914),载于F·H·欣斯利编《格雷爵士时代的英国外交政策》(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rey,伦敦1997年)pp. 288–311;R. J. Crampton《空洞的缓和:巴尔干地区的英德关系(1911-1914)》(The Hollow Detente. Angl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Balkans,伦敦1980年);Kennedy的《英德对抗的兴起》(The 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关于蒂尔皮茨战斗舰队建设参见Berghahn《蒂尔皮茨计划》(Der Tirpitz‑Plan)。
17 例如Keith M. Wilson《协约政策:英国外交政策决定因素文集(1904-1914)》(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 Essay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4–1914,剑桥1985年);Rainer Lahme《不列颠治世的终结:英国与欧洲列强(1890-1914)》(Das Ende der Pax Britannica: England und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1890–1914),《文化史档案》(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第73卷第1期(1991年)pp. 169–92;Andreas Rose《帝国与大陆之间:一战前的英国外交政策》(Zwischen Empire und Kontinent. Britische Außen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 krieg,慕尼黑2011年,英译本为 Between Empire and Continen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纽约与牛津2017年)。关于英国动机的史学分歧详见第四章。
18 ‘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指支持土耳其自由主义改革的运动人士。1908年的革命促成了土耳其建立君主立宪制。详情参见Mustafa Aksakal《奥斯曼帝国走向1914年战争之路》(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 关于波斯尼亚吞并危机详见 Samuel R. Williamson, Jr.《奥匈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伦敦1991年)。
20 军备竞赛方面参见David Stevenson《军备与战争的来临:欧洲(1904-1914)》(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 Europe 1904–1914,牛津1996年);David G. Herrmann《欧洲武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成》(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新泽西普林斯顿1997年)。
21 ‘空头支票’(blank cheque)全文参见Annika Mombauer《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外交与军事文件》(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曼彻斯特2013年)第120号文件。
23 对1914年7月外交事件的简要概述难以体现这场危机的复杂性(相关著述已达数千页)。近年众多研究中,James Joll与Gordon Martel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是绝佳的入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