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背叛》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想请问译者是怎么把《I MARRIED A COMMUNIST》这个题目翻译成《背叛》的,是否因为深陷罗斯所构建的罗网,情不自禁地也想体验一下背叛的乐趣,非但背叛作者,更要背叛和挑衅读者。
本书旧版本的译名曾经是《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很忠实。对于译者的新选择,我们暂且强忍下遭到背叛的不适,逼迫自己遵循那条交流的仿佛亘古有效的原则——同情地理解——站在她的角度想一想。
一种是禁忌。“COMMUNIST”这个词只有在特定的(官方的、宏大的)场景才可说出,它排斥随意性或非官方性,不允许被利用,也不允许被解读;译者深谙有关“COMMUNIST”的生存之道,它不能在一部小说的题目中出现,否则或许不但危及文学的生存,更危及现实中的人的生存。
一种是“善意”。译者或许以为她办了一件大好事,“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只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材料线索,“背叛”却是思想的线索,以后者为题目,读者就算还没有翻过十页,对于本书想要讲什么也仿佛超越了一知半解的水平。
我们说这是对作者的背叛,主要在“禁忌”的意义上。作者拥有对其作品命名百分之百的权利,无论我们怎样质疑题目的艺术性、合理性、思想性,都无法撼动上述权利。如果罗斯想要我们一上来就感受到“背叛”在这个故事中的中心地位,他就绝不会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当作题目。反过来,或许他以为“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冲击性,相比于思想性,读者更容易被冲击性、戏剧性所吸引,这是每一本创意写作指导书都再三强调的,罗斯深谙其理;又或者,这是罗斯的任性,艺术家拥有任性的权利,哪怕将“无题”或“星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题目,我们除了接受以外,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译者唯一的责任莫过于尽量忠实地传达作家的文字,如果说存在不可言说的禁忌,就算是翻译成《我嫁给了⋯⋯》,也比《背叛》要显得不那么“背叛”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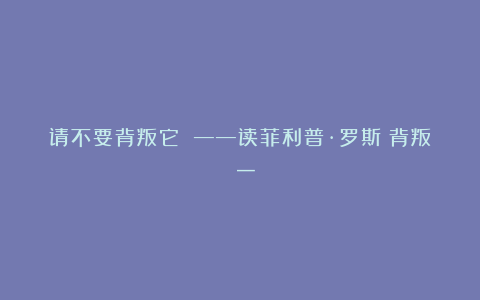
如果说译者同样“背叛”了读者,那就是在“善意”的意义上。这种善意是我们绝不需要的,我们不是小学生,不需要所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东西(甚至小学生也不需要)。这不是简单的好心办坏事,而是借助“善意”仿佛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好像如果没有提醒,我们就会看不懂罗斯,看不懂各种各样的背叛和各色人等在背叛与遭受背叛之后的挣扎或绝望。
仿佛是先知般地意识到了作品会被曲解的危险,仿佛是要警告这样的译者,罗斯在本书中通过利奥之口诉说了文学的本质和它与政治的不同:
“政治最会普遍化,⋯⋯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对于政治,文学是颓废、软弱、离题、枯燥、顽固、无趣的,没有什么意义,还真就不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将事物具体化的冲动正是文学。你怎能作为艺术家却放弃细节呢?可是你又如何作为政治家却允许细节呢?作为艺术家,细节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简单化。即使你选择最简洁的写作风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旧是赋予细节,澄明复杂事物,揭露隐含冲突。不是抹去冲突,否认冲突,而是看到冲突之内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里。为混乱留出空间,让它进来。必须让它进来。不然,你就是制造了宣传品,若不是为一个政党、一项政治运动,那就是为生活自身而产生的愚蠢宣传品——因为也许生活自己较愿出出风头吧。⋯⋯”
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二者都不但在技术上、而且在观念上看不起对方。如果在罗斯的小说中存在政治,那就是被文学所批判、所任意驱使的政治。艺术家专注的是细节,他不提供答案,我们不能强装好像他会提供拯救世界的钥匙,这超出了他被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艺术家不会像政治家那样要拯救这个或那个,这群或那群,甚至仿佛要拯救全人类。这是常识,译者应当明白,而且不应当试图误导(无心之失)或代替作家教导(有心之失)我们,作家不会那样,译者不该那样。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相比于政治,文学更具备观念的永恒性,它的穿透力更强,更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本真的人性。看起来,好像政治的普遍性提供答案或原则,文学的个别化提供无意义;本质上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前者仿佛是矛盾而短命的,后者在拥抱矛盾、无意义的过程中抵至永恒。
政治就像“俄国革命的头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爱,要有自由的爱了!’可他们一旦掌了权,就不能容许了。因为什么是自由的爱呢?混乱。而他们不想要混乱。他们不是为此才去进行光辉革命的。他们要的是有纪律,有组织,从容不迫,如若可能,还是可科学预见的。自由的爱扰乱了组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器。艺术也扰乱组织。文学扰乱组织。不是由于它公然支持或反对,或者由于它哪怕是隐晦地支持或反对。它扰乱了组织是因为它不是普遍的。个别的内在本质是要成为个别的,个别性的内在本质是不从众。将苦难个别化:就是文学了。在一个简单化、具体化的世界里让个别保持生存——这是斗争的焦点。”因此政治视文学为水火不容的大敌,后者虽然没有纲领,却凭靠混乱或表面上的无意义扰乱了人们思想;政治不喜欢混乱,它追求秩序和稳定,尽管生命本质上排斥秩序和稳定。
文学就像罗斯的小说所表达的,正如利奥所说:“你不需以写作来证明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也不需以写作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你两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对两者同等不结盟。是,你看到了不同点,自然也看到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点,或者那垃圾比这垃圾稍好一点。也许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职员。不是好战者。不是信徒。你对这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同。好战者提倡信仰,将改变世界的大信仰,而艺术家则贡献一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产物。没什么用处。艺术家,严肃作家,给世界引入了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译者愿意传递一点罗斯的、严肃文学的文学观——文学不需要证明什么,它给世界引入某种新的东西——她或许可以换个选择,也就是既不背叛作家,又不背叛我们。无论对于那一方,这都是想要畅游文学世界或塑造文学世界之人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忍不住想要善意地对她说:“拜托!请不要背叛它!”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