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时三刻,太皇河畔的天幕仍是浓稠的墨蓝色,几粒残星恹恹地挂着。丘府深宅大院里,唯有后罩房东边那间精巧的耳房,悄然亮起一点如豆的灯火。李银锁悄然起身。
李银锁赤足踩在冰凉光滑的金砖地上,如同踏过寂静的深水,悄无声息地挪到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素净的脸,眉眼间尚存几分未褪尽的睡意。
她手指灵巧地挽好一个家常的圆髻,簪上一支素银簪子,又迅速罩了件半旧的青缎比甲,动作轻捷得没有带起一丝风。
梳洗完毕,李银锁推开房门,一股黎明前特有的清冽寒气扑面而来。天光正挣扎着,将庭院里高大屋宇的轮廓从混沌中一点点剥出来。廊下早已垂手立着七八个人影,杂物管事丘世杰、管采买的丘宜禄、灶上的王妈妈、针线上的赵娘子……皆是府里各处管事儿的头脸人物。他们无声地躬身,齐道:“姨奶奶早!”
李银锁略一点头,算是回礼,脚步不停,径直走向前院倒座房边专用来理事的小厅。厅内早已收拾得齐整,一张花梨木大案上,一册厚厚的蓝皮账簿摊开着,旁边搁着笔墨。李银锁走到案后,没有落座,目光扫过紧随而入、按序站定的众人。
“世杰,”李银锁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拂晓的凉气,清晰地落入每个人耳中,“今儿西边田庄该送新碾的头茬米过来,你带人亲自去接,过完秤,一粒不落,直接入新库东三仓。仓里昨日晒透的旧米,挪出来,预备着这几日府里和长工灶上用!”
邱世杰躬身应道:“是,姨奶奶放心,小的亲自盯着!”
“宜禄,”李银锁转向管采买的丘宜禄,“庄子上报,前日暴雨冲垮了往北地界两处田埂,得赶紧补上。你即刻去寻可靠的泥瓦匠,工料今日备齐,明日一早就动工。银子,”指尖在账簿上某个条目轻轻一点,“从这里支!”
“是,侄儿这就去办。”丘禄应声退下。
“王妈妈,”李银锁的目光落在灶房管事身上,“今日少夫人娘家有客来,午间的席面再加一道’玉带羹’,一道’蜜火方’。昨日庄上送来的鲜藕和莲子,挑顶好的用上。还有,长工灶上,前几日那腌菜齁咸,换些清爽小菜,油水也略厚些!”王妈妈连声应着“记下了”。
“赵娘子,”李银锁看向针线房,“少爷前日换下的那件宝蓝缂丝直裰,袖口脱了线,今日务必收拾好。另外,把少夫人入秋要穿的几件夹袄衬里都拆出来晒晒,去去霉气。天说变就变,等不得!”
一条条指令清晰、利落地分派下去,如同溪流归渠,顺畅无阻。无人质疑,无人拖沓,只有干脆的应诺声和迅速退下办事的身影。偌大丘府,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寂静里,已然筋骨舒展,活络了起来。
待诸事分派停当,窗外天色已褪尽了墨色,转为一种清透的鸭蛋青。李银锁这才在案后坐下,略舒了口气,端起小丫头适时奉上的一盏温温的蜜水,润了润发干的喉咙。
晨光熹微,彻底照亮了庭院。李银锁起身,带着贴身的小丫鬟春杏,开始每日的巡查。沿着抄手游廊,先看了马厩,几匹少爷心爱的骏马毛色光亮,槽头草料干净充足。老马夫马成正仔细地刷着马身。车轿也都被马忠擦拭得锃亮,排列整齐。李银锁略一点头,转向存放粮米布帛的几处大库房。
新库东三仓的门敞开着,刚送来的新稻堆成小山,散发着浓郁的稻谷清香。丘世杰正指挥着几个壮实的长工过秤入仓。李银锁走进去,随手抓起一把稻粒,饱满干燥从指缝间簌簌滑落。她目光扫过靠墙的几个袋子时,脚步却顿住了。那几袋米堆在最底层,紧挨着青砖墙壁,袋子表面摸上去,隐隐透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潮润凉意。
“世杰,”李银锁声音沉了下来,“这几袋,挪出来!
丘世杰忙过来,伸手一探,脸色也变了:“哎哟!这……怕是靠墙受了地气!小的疏忽,小的该死!”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李银锁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立刻!把这受潮的米,一袋不漏,全搬到外面高燥向阳的晒场去摊开!今日日头好,务必给我晒透!其余的米,重新码放,离墙至少一尺远,底下垫上厚木板!库房四角,再增放些生石灰吸潮!”
话音不高,却字字斩钉截铁。丘世杰额上冒汗,连声应着,立刻吆喝人手忙碌起来。看着那些受潮的米袋被迅速搬出,李银锁才转身离开,留下库房里一片加紧忙碌的声响。
刚走到连接内院和外院的垂花门附近,一阵刻意压低的争执声便飘了过来,带着乡下妇人特有的粗砺和怨气。
“……凭啥她就能拿那匹细棉?我上回做活计磨破了手,少夫人还夸我来着!”浆洗上的张婆子声音又尖又利。
“呸!你那点破活计也好意思提?我管着花园子,哪日不是起早贪黑?那细棉合该是我的!”专管洒扫庭院的李婆子声音更冲。
两个粗壮的仆妇在月洞门边的角落里拉扯着一匹质地稍好的细棉布,脸红脖子粗。周围几个小丫头缩着脖子,想劝又不敢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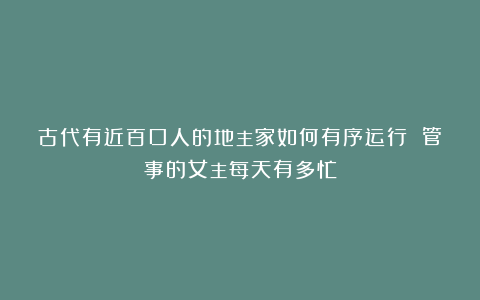
李银锁停住脚步,春杏立刻扬声:“姨奶奶在此!”
争执声戛然而止。张婆子和李婆子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猛地松开手里的布匹,慌忙转过身,看见李银锁平静无波的脸,吓得脸色发白,扑通跪下了,头埋得低低的,身子微微发抖。
“府里的规矩,都忘了?”李银锁的目光扫过她们低垂的发顶,声音不高,却像冰水浇头,“东西是府里的,自有分派。争抢拉扯,成何体统?这匹布,”指了指地上那卷细棉,“即刻交回针线房赵娘子处,入库登记。你们两个,今日的工钱,各扣一半!”
两人浑身一颤,却不敢有丝毫辩驳,只连连磕头:“谢姨奶奶开恩!谢姨奶奶开恩!奴婢再不敢了!”
“起来吧,”李银锁淡淡道,“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再有下次,丘府也留不得这等不晓事的人!”
两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起来,连地上的布匹都忘了捡,就被春杏使眼色的小丫头催促着,惶惶然退下了。那卷惹祸的细棉布被一个小丫头拾起。
午后,丘府一片宁静,只有蝉鸣在浓荫里嘶叫。李银锁刚在账房核完上午几笔采买的支出,窗外忽然传来一阵短促惊慌的呼喊,紧接着是铜盆哐当落地的刺耳声响!
“走水了!灶房走水了!”
李银锁心头一紧,扔下账册疾步冲出房门。只见西北角灶房方向,一股浓黑的烟柱已腾空而起,夹杂着火星子,在澄澈的蓝天映衬下分外骇人。仆人们乱作一团,惊呼四起,端水桶的、拿盆的,脚步杂乱无章,水泼得到处都是,却难以靠近那越来越猛的火头和浓烟。
“慌什么!”李银锁清叱一声,声音不大,却奇异地压住了场中的混乱。她几步冲到人前,提起身前碍事的裙裾往腰带里一掖,露出下面利落的撒腿裤,径直冲向浓烟翻滚的灶房门口。浓烟呛得人直流泪,火舌在灶膛口和堆放的柴草上跳跃。
“王妈妈!”李银锁掩住口鼻,声音在烟火气里依旧清晰,“带人把门口这几捆柴禾全搬开!隔断火路!”
“宜禄!带人再去后院井里打水!用桶接龙传进来!泼门口地面和柴堆,别对着火头乱泼!”李银锁又指向几个慌乱的小厮,“你们几个,去把晾在院子里的湿被褥拿来!快!”
她的指令清晰、准确、不容置疑。混乱的人群像是瞬间找到了主心骨,王妈妈立刻吆喝着几个粗壮仆妇去拖拽柴禾;丘宜禄带着人奔向水井;小厮们飞奔去抱湿被褥。李银锁自己则站在浓烟边缘,不断观察火势,调整着指令。
“水!递水进来!”她伸手接过一桶水,毫不犹豫地泼向门口蔓延到干草堆上的火苗。嗤啦一声,白气蒸腾,火势被压下去一小片。湿漉漉的厚重被褥也很快被递到,李银锁指挥人用它覆盖住旁边极易引燃的干柴垛。
众人齐心协力,火势终于被控制住,渐渐熄灭,只剩下呛人的浓烟和一片狼藉。李银锁脸上沾了烟灰,鬓发散乱,青缎比甲上溅了不少水渍,站在焦黑的灶房门口,看着惊魂未定的仆人们清理现场。
“查清起火缘由,报给我!损失也尽快清点出来!”李银锁对赶过来的二管家吩咐道,声音带着烟熏后的微哑,却沉稳依旧。二管家忙不迭地应下。
夕阳熔金,将丘府高耸的马头墙镀上一层温暖的橙红。前院传来车马停驻的声响,少爷丘世裕回来了。他大步穿过庭院,一眼便看见站在廊下、衣袍微皱、发间还沾着点灰痕的李银锁。
“银锁,”丘世裕走近,带着一丝外面的风尘气,目光在她略显狼狈却依旧沉静的面上停留片刻,随即示意身后小厮捧上一个锦盒,“喏,苏杭新到的花样子,给少夫人和你,各裁件新衣!”
锦盒打开,里面是两匹流光溢彩的绸缎,一匹是稳重的宝蓝,一匹是娇艳的杏子红。丘世裕指了指那匹杏子红:“这匹颜色鲜亮,给你正好!” 说完便转身往内院去了。
李银锁微微屈膝:“谢少爷!” 看着那匹在暮色中依旧光华流转的杏红绸缎,她面上并无太多波澜,只示意春杏仔细收好。
夜幕低垂,丘府各处的灯火次第亮起。李银锁在灯下细细翻阅着二管家报上来的灶房损失清单,一一核对。门帘轻响,一阵温和的香气伴着脚步声传来,李银锁忙起身。
少夫人祝小芝走了进来,她穿着家常的藕荷色衫裙,发髻松松挽着,脸上带着一贯的温婉笑意。她目光落在李银锁脸上,又扫过桌上摊开的账册和清单,最后落到那匹放在一旁、光华内蕴的杏红绸缎上。
“今日辛苦了,我都听说了!”祝小芝的声音柔和似水,她轻轻拉起李银锁的手,那手并不十分细腻,指节甚至有些微的薄茧,是常年劳碌的印记。
“灶房的事,处置得极好!这个家……”祝小芝的手在李银锁的手背上安抚地轻轻拍了拍,语气里是毫无保留的信赖,“是离不得你的!好妹妹!”
灯花哔剥一声,轻轻爆开。李银锁垂着眼帘,低声道:“少夫人言重了,都是奴婢分内的事!”
祝小芝又嘱咐了几句早些歇息的话,便离去了。室内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灯芯燃烧的细微声响。李银锁的目光再次落回那匹杏红绸缎上,指尖轻轻地抚过冰凉的缎面,那光滑的触感下,仿佛还残留着少夫人掌心传递过来的、滚烫的暖意。
她静静坐着,良久,才轻轻吹熄了灯。一室黑暗中,那份沉甸甸的信任,如同无形的锁,将她与这个深宅大院,更紧地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