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年间,海宁县。
时值盛夏,烈日如火。新上任的张县令轻车简从,深入乡间体察民情。
行至胡家村外,但见田野荒芜,村舍萧索,张县令不由得眉头微锁。
突然,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变脸!一阵狂风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卷起地上沙石枯草,天地间一片昏黄。更令人骇然的是,那股旋风竟如一条扭动的黑龙,不偏不倚,直扑路边一座黄土新坟!
“呼——咔嚓!”
众人惊骇目光中,那龙卷风竟将坟头的封土硬生生卷走大半,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棺木一角!
张县令心中大惊!
“天降异象,必应人事。” 这旋风为何独独掀翻此坟?其中必有蹊跷!
他立刻下马,快步走向坟茔。只见坟前坐着一位抽着旱烟的老者,面色惊疑不定。
“老人家,请问这坟中所葬何人?何时下葬?”
老者见其气度不凡,连忙起身回礼:“回官人话,这里面埋的是我们村的胡兵飞,唉,才三十出头,正是壮年,可惜啊……前几日得急病没了,这才刚过’头七’。”
“急病?”张县令追问,“何等急病能夺去壮年性命?”
“听他家娘子说,是害了’寒热症’,没熬过去。”
正说着,一阵似哭非哭的哀音由远及近。众人抬头,只见一名女子身着缟素,手提祭品,袅袅娜娜而来。
那女子生得极美,即便一身素缟,亦难掩其风流体态。柳眉杏眼,肤白如雪,行走间自有一股媚态流转。然而,她口中虽发出哭泣之声,那张俏脸上却不见半分悲戚,眼角眉梢甚至隐隐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
老者低声道:“官人,这就是胡兵飞的遗孀,郭昭筠。”
郭昭筠走到坟前,放下祭品,便开始“哀哀切切”地烧纸钱。
张县令走上前,沉声问道:“胡郭氏,本官问你,你丈夫所患何症?请了哪位郎中?所服何药?”
郭昭筠抬起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张县令脸上转了一圈,才哽咽道:“回大人,民妇夫君确是染了寒热症,请的是邻村的王郎中,也开了方子吃了药,谁知……谁知还是没能救回来……”她说着,又拿起手帕拭泪,姿态柔弱,我见犹怜。
但张县令心细如发,敏锐地捕捉到她眼神那一瞬间的闪烁与慌乱。
“寒热症虽凶,但壮年男子猝死,实属罕见。本官欲开棺验尸,查明死因,你可同意?”
“什么?开棺?”
郭昭筠猛地跳了起来,脸上的柔弱瞬间被尖厉取代:“不行!绝对不行!我夫君刚刚入土为安,尸骨未寒!你们这些当官的,为何非要惊扰亡魂,让他死后都不得安宁?你这是要让我夫君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
她声音凄厉,扑到坟上,双臂张开,仿佛要用身体护住坟墓:“夫君啊!你死得好惨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啊,你刚走,就有人要来掘你的坟,刨你的尸啊!这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啊!”
她哭嚎得声嘶力竭,引得远处一些村民驻足观望,指指点点。
张县令见她反应如此过激,心中疑云更甚。但他深知,若无苦主首肯或确凿证据,强行开棺于礼法不合,反而可能打草惊蛇。
他按下心头疑虑,不动声色道:“既然你执意不肯,本官也不便强求。你好自为之。”说罢,转身便带着随从离开了。
回到县衙,张县令心绪难平。
“明察不行,唯有暗访!”
次日,张县令换上一身半旧道袍,手持“铁口直断”的布幡,乔装成游方算命先生,再次来到了胡家村附近。
一连两日,他走街串巷,旁敲侧击打听胡家之事。村民大多讳莫如深,只言片语间,仅知胡兵飞家境殷实,为人本分,与郭昭筠成婚不足两年,并无子嗣。关于其死因,众人皆说是急病,但眼神躲闪,似乎另有隐情。
这日傍晚,天色突变,乌云压顶,顷刻间便下起了瓢泼大雨。张县令见前方有处简陋院落,忙快步上前叩门避雨。
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开了门,见他浑身湿透,连忙热情地将他让进屋内:“先生快请进,这雨大的,可别淋病了。”
“多谢大娘收留。”张县令拱手道谢,环顾四周,只见家徒四壁,但收拾得颇为整洁,“大娘家中尚有何人?”
老太太叹了口气,脸上浮现愁容:“还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三十多了,不成器,整日在外游手好闲,他爹走得早,是我没管教好啊……”
正说着,院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裹着风雨闯了进来,声如洪钟:“娘!你看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今天咱娘俩打牙祭!”
来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身材魁梧,手里拎着一壶酒和几包用油纸包着的熟食。
“勇儿!有客人在,不得无礼!”老太太连忙呵斥。
那汉子这才注意到屋内的张县令,愣了一下,随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嘿,有客人?娘,咱家可是难得有客上门!先生别见怪,我荆大勇是个粗人!”
段母向张县令介绍道:“先生,这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荆大勇。”
张县令心中一动,面上却不动声色,微笑道:“荆兄弟性情豪爽,乃是真性情。在下姓张,游方卜算之人,承蒙大娘收留避雨。”
荆大勇见张县令谈吐不凡,心生好感,将酒菜往桌上一放:“相逢就是缘分!张先生,一起来喝两碗,驱驱寒气!”
三人围坐桌边,荆大勇热情地给张县令倒酒。几碗村酿下肚,荆大勇话也多了起来。张县令学识渊博,引经据典,听得荆大勇啧啧称奇,佩服不已。
“张先生!”荆大勇猛地一拍大腿,酒意上涌,“我荆大勇虽然是个粗人,但也敬重有学问的好汉!先生若是不嫌弃,我愿与先生结为异性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看如何?”
张县令正愁如何深入结交,闻言顺势道:“荆兄弟快人快语,豪气干云,正合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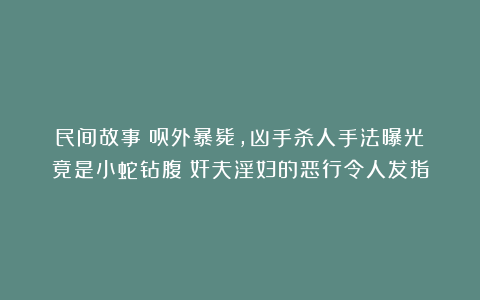
“哥哥!”荆大勇大喜,重重抱拳。
结拜之后,气氛更为热络。张县令看着荆大勇,语重心长道:“贤弟,你仪表堂堂,气概不凡,为何不寻个正经营生?男子汉大丈夫,当建功立业,娶妻生子,奉养母亲,光耀门楣啊。”
荆大勇闻言,脸上兴奋之色褪去,叹了口气,又灌了一口酒:“哥哥,你说的这些,弟弟我何尝不懂?我荆大勇虽然混账,但孝敬老娘的心从来没变过!之所以至今未娶,一来是家贫无人肯嫁,二来……二来也是怕娶个不贤惠的,反而气坏了老娘!”
他顿了顿,脸上露出鄙夷之色:“再说,这世道,坏女人太多了!就像邻村那个胡员外,够有钱了吧?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结果怎么样?成亲不到一年,就被那毒妇伙同奸夫给害死了!自己辛辛苦苦挣下的万贯家财,全便宜了奸夫淫妇!”
张县令心中剧震!胡员外?莫非就是胡兵飞?!他强压住内心翻腾,故作惊讶:“哦?竟有此事?贤弟莫不是听闻了讹传?胡员外不是病故的吗?”
“病故?屁!”荆大勇酒意上头,口无遮拦,“那是他们做给人看的!哥哥,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张县令心脏砰砰直跳,表面却愈发平静,为他斟满酒,“贤弟慢慢说,莫不是看错了?”
“千真万确!”荆大勇一拍桌子,压低声音,脸上带着后怕与神秘,“不瞒哥哥,前阵子手头紧,我就想……就去胡家‘借’点银子花花。那天晚上,我翻墙进了胡家院子,摸到他们卧房窗外,舔破窗纸往里瞧……这一瞧,可把我魂都吓飞了!”
他灌了口酒,压压惊,才继续道:“我看见胡员外直接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青黑。他那个漂亮媳妇郭昭筠,和一个长得油头粉脸的小白脸站在床边!那小白脸手里……手里竟然拿着一条小蛇!花花绿绿的,看着就瘆人!”
张县令屏住呼吸,眼神锐利如鹰。
“然后呢?”
“然后?”荆大勇声音发颤,“然后那毒妇郭昭筠,就上前用力掰开了胡员外的嘴巴!那小白脸眼疾手快,直接把那条扭动的小蛇塞进了胡员外嘴里!那蛇……那蛇直接就钻进去了!我的亲娘哎!胡员外当时浑身一抽,大叫了一声,就没动静了!肯定死了!”
即便是张县令,听闻如此诡异的杀人手法,也不禁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
荆大勇显然还沉浸在那晚的恐怖回忆中:“这还没完!那对狗男女,见胡员外断气了,竟然……竟然就在尸体旁边……行了那苟且之事!简直禽兽不如!我当时腿都软了,连滚带爬就跑了,后来就听说胡员外‘病故’了。这事我只告诉过哥哥你,别人我都不敢说,怕惹祸上身!”
张县令心中已然明了,他深吸一口气,按住荆大勇的肩膀:“贤弟,此事关系重大,你切记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可再提!为兄刚为你卜了一卦,你三日内恐有牢狱之灾,切记待在家中,万不可出门!只要渡过此劫,日后必有大运,富贵可期!”
荆大勇对这位“神机妙算”的结义大哥已是深信不疑,连忙点头:“哥哥放心,我绝不出门!”
雨势渐歇,张县令起身告辞,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收网的时候,到了!
翌日清晨,县衙鼓声大作。
张县令升坐正堂,面色肃穆,惊堂木一拍:“来人!持本县签票,速去胡家村,将寡妇郭昭筠,及其邻村奸夫周云龙,并村民荆大勇,一并锁拿归案!”
“威武——”
衙役们离立刻分头行动。荆大勇正在家中吃着早饭,见衙役上门,想起哥哥所言,暗道“算得真准”,虽不明所以,倒也配合。而郭昭筠与周云龙则是在惊慌失措中被从床上拖起,锁链加身。
公堂之上,三人跪倒。荆大勇抬头,看见端坐堂上、官威凛凛的张县令,惊得目瞪口呆!
“荆大勇!”张县令声音沉稳,“今日本官传你到此,是为胡兵飞被害一案。你将那晚所见,从实招来,不得有半句虚言!若助本官查明真相,便是首功,本官自有重赏!”
荆大勇此刻方知结义大哥竟是县太爷,又惊又喜,再无顾虑,便将那晚所见所闻,原原本本,高声陈述了一遍。书吏在一旁奋笔疾书,记录口供。
堂下跪着的郭昭筠与周云龙,听着荆大勇的叙述,早已面无人色,浑身抖如筛糠。尤其是听到“小蛇钻腹”的细节时,郭昭筠尖叫一声,几乎晕厥,周云龙则瘫软在地,裤裆一片湿漉。
“犯妇郭昭筠!奸夫周云龙!荆大勇所言,可是实情?!”张县令厉声喝问。
“大人!冤枉!民妇冤枉啊!是那荆大勇血口喷人!”郭昭筠还想做最后挣扎。
周云龙也磕头如捣蒜:“大人明鉴!小人与这妇人只是……只是相识,绝无杀害胡员外之事啊!”
“冥顽不灵!”张县令冷哼一声,“既然你二人不肯招认,那便让死者自己开口说话!来人!押解一干人犯,前往胡兵飞坟前,开棺验尸!”
胡家村外,胡兵飞坟前。
得到消息的村民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衙役们挥动铁锹,掘开坟土,撬开棺盖。
一股异味弥漫开来。作作上前,仔细查验。虽然尸体已有些腐败,但作作还是在胡兵飞的喉管及胸腔部位,发现了明显的异常损伤,并最终从其胃袋附近,找到了一条已然僵死的、色彩斑斓的小蛇尸体!
“回禀大人!尸身喉管有异物刮擦损伤,体内确有毒蛇一条!胡兵飞确系被活物入体残害致死!”作作高声禀报。
“嗡——”人群瞬间炸开了锅!
“天啊!真是被蛇钻死的!”
“太狠毒了!果然是这对奸夫淫妇!”
“青天大老爷明察秋毫啊!”
铁证如山!
郭昭筠见到那條小蛇,双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周云龙面如死灰,磕头砰砰作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是郭昭筠那淫妇先勾引我的!是她逼我这么做的啊!”
张县令目光冰冷,扫过这对罪恶的男女,声震四野:“天道昭昭,报应不爽!今有犯妇郭昭筠,不守妇道,与人通奸,更兼心肠歹毒,谋杀亲夫,罪大恶极!依《大明律》,判浸猪笼之刑,即刻执行!”
“奸夫周云龙,罔顾人伦,与有夫之妇通奸,并行此骇人听闻之手段谋害人命,其行可诛,其心可灭!判阉割之后,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判决一下,百姓欢声雷动,直呼“青天”!
随后,张县令又对荆大勇道:“荆大勇,你虽行为不端,但此次揭发命案有功,本官赏你白银五十两,助你安家立业。望你自此改过自新,孝顺母亲,莫负本官期望!”
荆大勇感激涕零,重重磕头:“多谢青天大老爷!荆大勇定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