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朗润园的晨光里,曾有一位穿中山装、戴旧帽的老者,静静走过洋槐树下。新生们常误将他当作校园清洁工,托付行李便匆匆离去,直到开学典礼上望见主席台上“副校长季羡林”的铭牌,才惊觉这位“老工友”竟是精通梵语、巴利语的学术巨擘,更是“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的集大成者。季羡林自评“写作水平不高”,却用《赋得永久的悔》《神奇的丝瓜》等名篇跨越了时代,其散文的魅力,正在于“真情为脉、平淡见奇”的创作智慧,为后世写作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真情是散文的生命线,这是季羡林散文最动人的密码。他从不回避“小我”的喜怒哀乐,却能让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共通的共情。六岁离家求学的他,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写下的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直击人心的细节:母亲用卖鸡蛋的钱缝制的棉衣,村口老树下模糊的眺望身影,三次归家却未能尽孝的遗憾,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成为穿透岁月的情感符号。对老友的追忆同样质朴动人,清华“四剑客”蹲在街边吃豆花争论学术,德国留学时与恩师瓦尔德施米特的相知相守,文字里没有刻意抒情,却让纯粹的情谊跃然纸上。正如他所言:“没有新鲜的印象,没有真实的感动,写出来的东西只会害己害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这份真情并未止步于个人悲欢,而是延伸为对天地万物的博爱。在《三个小女孩》中,两岁孩童的依恋、五六岁娃娃的笑靥、十二岁少女的关切,偶然的相遇被他视作“平生乐事”,这份对弱者的同情让两颗童心自然相连。《咪咪》一文中,猫咪打翻墨水瓶弄脏手稿,他非但不怒,反而笑问“你也想改文章?”,这份对小动物的包容,正是博爱最生动的注脚。更难得的是,他将爱国赤诚与人类关怀融为一体,“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爱国”的深情,与“请春雨分润非洲大地”的悲悯交织,让散文既有故土的温度,又有苍穹的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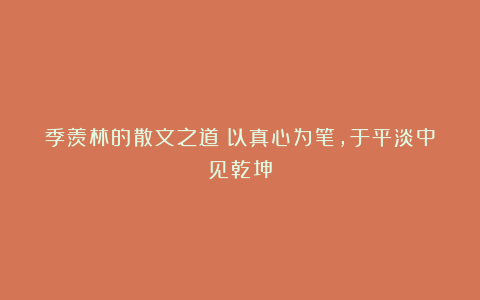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季羡林的文风,是“平淡”与“神奇”的辩证统一。他的“平淡”绝非浅白寡淡,而是洗尽铅华后的凝练通透。他主张散文“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这份境界源于对文字的极致锤炼。《槐花》中,他写北大朗润园的洋槐:“每天走过,从未觉其美;外国朋友却为花香惊叹”,看似平铺直叙,却引出“习焉不察的东西,需保持距离才能看见美”的哲学思考,用生活场景讲透审美本质,正是“炼篇”的功力。而他的“神奇”,则藏在对寻常事物的独特观照中。《神奇的丝瓜》里,他将丝瓜塑造成“有思想的生命”:“能让弱瓜停止生长,给壮瓜找支撑,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种拟人化的观察,源于对植物生长的细致凝视,让平淡的日常焕发出生命智慧的光芒。《红》中,卖绿豆的前土匪被处决时,“血光闪过,西天晚霞结成红花”,“红”既指血色,又暗喻生命的复杂,平淡叙事中骤然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作为写作者,季羡林的“三重修炼”更具实践意义。其一,灵感源于“情感触发”,拒绝无病呻吟。他从不强迫自己写作,认为“三点一线的平淡生活,写不出好文章”。留学德国时教授夫人的苦咖啡带来的文化触动,晚年住院时病痛中的思考,都成为创作的火种。这启示我们,要做生活的观察者,地铁里陌生人的微笑、菜市场摊主的吆喝、窗外丝瓜的生长,都可能成为灵感的源泉,关键在于以感知的心去发现。其二,真诚是写作的底色,坚守独立见解。面对文坛对散文的轻视,他直言“’五四’以来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新诗反而失败了”;反对堆砌辞藻,主张“真情实感是根本”。这种不迎合、不盲从的态度,让文字既有温度,又有筋骨。其三,节奏是散文的灵魂,在自由与章法间平衡。《神奇的丝瓜》从发现丝瓜到观察生长,再到思考生命智慧,层层递进;《赋得永久的悔》以“悔”为线索,穿插回忆与现实,情感张弛有度。正如他所说:“要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这种节奏意识,正是散文艺术性的核心。
季羡林的散文里,藏着两个交融的世界:一个是“布衣学者”的日常,喂猫、看槐、忆旧友,满是烟火气;另一个是“国学大师”的精神疆域,爱故乡、爱国家、爱人类,自有书卷气。对今天的写作者而言,他的启示或许很简单:不必执着于华丽的技巧,先修炼真诚的心灵;不必焦虑灵感的缺失,先培养观察的眼睛。正如朗润园的洋槐,越是习以为常,越藏着生命的奥秘。写作亦然,最动人的力量,永远源于对生活最真切的热爱与思考。季羡林用一生证明,散文的至高境界,不过是“以真心写真情,于平淡见神奇”。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