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
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
6月8日,本报11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人广泛关注,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热烈,持论各异。本报特就此话题继续征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观点迥异,均十分欢迎。
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随着“昆仑石刻”争鸣持续,有不少学者主张应在历史语境中讨论石刻真伪及断代问题。本期“学术争鸣”两篇文章均从秦汉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郭涛撰文《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认为秦代中原使者前往扎陵湖地区采药既有地理基础,也有历史延续性;葛承雍撰文《在秦汉视野下凝视扎陵湖石刻》,认为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更符合王莽时期派使采药和巡狩宣威的历史特征。
我们提倡各种观点争鸣,哪怕持论迥异,本报均提供充分阐发的平台。
来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
作者:郭涛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青海扎陵湖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石刻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一个月来大家在文字、文本、历日和石刻的地质、地理、气候环境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争鸣可谓异彩纷呈。对于秦朝的官方使者及车马交通能力能否到达高寒遥远的扎陵湖地区,一些人始终持怀疑态度,我尝试从交通地理角度做进一步的讨论。
仝涛研究员在6月8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和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专访中都特意强调,石刻的发现“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仝先生说明的对象是秦代石刻,却提及“唐蕃古道”,难免让人觉得突兀。实际上,具体到先秦秦汉时期该地的族群活动和青海地区的交通状况,石刻所反映的是张骞通西域开辟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以前“羌中道”的交通意义。
青海西宁市彭家寨汉墓出土的木轺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时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显示秦帝国的西部疆域抵达了临洮秦长城,接近羌中地区。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临洮县条,班固注“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临洮以西就进入了羌中。
羌中指西部羌人等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羌人的活动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南边与蜀郡、汉中郡的徼外蛮夷相连,西北与西域的鄯善、车师诸国相邻。《汉书·地理志》中郡县的注记,多见“水出羌中”“水行羌中”“山在羌中”,所涉地域由蜀郡往西北依次是陇西郡临洮县、金城郡河关县、金城郡临羌县,再西北进入河西走廊依次是张掖郡觻得县、酒泉郡禄福县、敦煌郡冥安县和龙勒县,这一线构成了武帝时期汉帝国的西部边塞,也符合《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地域的界定。羌中地域范围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羌人本身“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半游牧状态和“不立君臣”的部落体制;另一方面,有学者也指出羌人的命名是中原华夏族群所赋予的,随着华夏领域的扩大而西移南移,羌人是一个概念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总体上,羌中属于徼外,羌人属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徼外蛮夷”范畴,大体分布在今甘肃岷县夏河以西和河西走廊以南今青海的广大地区。
纵观目前所见关于秦代疆域的描述和相关秦代历史地图,西部边界大都沿着临洮秦长城,靠近而没有深入羌中地区,更不要说抵达发现“昆仑石刻”的青海扎陵湖地区,这是非常严谨的做法。但是《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通过天水、陇西已经与羌中建立了相当程度的交往,秦长城的修建并不妨碍这种交往的延续,也不会影响秦始皇遣使采药的进行。《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当然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故事背后的交通史背景值得关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也有不少涉及与徼外蛮夷交往的律令,如“道塞徼外蛮夷来为间及来盗略人”“禁黔首毋得买故徼外蛮夷筋角皮革”,这些禁而不绝的活动,以及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都说明秦人的交往突破了帝国的疆域范围。
同时,由于羌中在东周秦代和西汉前期一直是一个社会组织相对松散、没有受到成熟政治体控制的地区,从而为“羌中道”的形成和长期维持提供了条件,承担着中原和西域沟通的桥梁作用。远在秦汉疆域之外,可远望而不易抵达的昆仑山,其神圣地位的确立或也与“羌中道”的兴盛有关。与之相对的是,河西走廊被匈奴政权控制,导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不得已谋划辅路“欲从羌中归”,结果再次沦为俘虏。等到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之后才打通丝绸之路,完成凿空之旅。张骞“欲从羌中归”,也正说明“羌中道”是使者出行、回归比较畅通的一条路。“昆仑石刻”中的五大夫翳就是使者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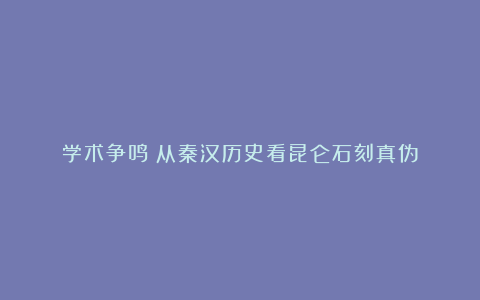
历史上“羌中道”以及后来习称的“青海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与北面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是并行于世、此起彼伏的关系。前者在不同时期,主线或偏北或偏南,成为中原、巴蜀、南方与西域进行使者往来、商旅贸易、僧侣求经布道的通道,交流形式多样,内部呈现交通网格局而非单一路线。“羌中道”的形成一般认为在东周时期,出土于战国魏襄王墓中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曾西巡至昆仑。《尚书·禹贡》记“织皮昆仑”“导河积石”,而《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条,班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金城郡临羌县条,班固注“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黄河源和昆仑山都在羌中的范围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山海经》也记“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经典大都揭示出中原人对于羌中地区尤其是其地理标志昆仑山、黄河源的认识与探索至迟不会晚于战国。那么秦代中原使者前往此地采药既有地理基础,也有历史的延续性。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在长城徼外的路线可以视为“羌中道”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比河湟道和婼羌道位置要更偏南、海拔更高,人员的流动也更少,因此鲜为人知。
“羌中道”可与秦帝国的主干交通网相连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尤为突出,建成了纵横交错的全国陆路交通网,包括陇西北地道在内,一共有八条主干道。驰道是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当的大型基建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修治驰道;《汉书·贾山传》记其规模“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根据《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记载来看,除驰道之外,包括南郡江水以南在内的全国每个县都有一定的亭邮设置,以及定期和临时的除道事务,可以想见秦的道路交通体系是遍布全国各个郡县的,并具备向外延伸的条件。而在同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一次西巡被称为“祭祖之旅”,或许最终抵达了秦人始居地西犬丘附近。这条陇西北地道是秦关中核心区交通路网的延伸,基础较好,由咸阳西行可抵达陇西郡临洮边地,继续向西延伸则与徼外之“羌中道”相连接。
石刻提到使者五大夫翳率领众方技(士)乘“车到此”,表明这次活动的车马仪仗,以昭示皇帝威仪。至于车马是否能到此地,质疑者认为气候地形等地理条件过于恶劣恐难成行,仝涛研究员则认为“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仝说有一定的道理,当今黄河上游的结冰期主要在每年12月到次年3月,越靠近源头,结冰期越长,若当年十月从咸阳出发一路西行,地表环境的变化大体都能满足车马出行。史载最早到达此地的周穆王,《左传》称其“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的车马依仗规格自然更高。那么使者五大夫翳随行之车的形制如何,或许可以参考出土于青海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汉墓的汉代木轺车。据介绍,其车高85厘米,长92厘米;马高105厘米,长90厘米;伞直径90厘米。拥有木轺车陪葬,墓主人的级别并不低。秦始皇的使者五大夫翳或也乘着类似的车马前往昆仑采药,抵达扎陵湖北岸石刻所在地后勒铭记事。
石刻所在地虽远在秦国疆域千里之外,但并非可望不可即。与张骞出使西域道路被匈奴隔绝不同的是,由于“羌中道”的畅通,五大夫翳等面临的最大困难主要来自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皇帝使命、故事和知识的引导,以及使者们的探索精神,最终保证了出使任务的完成,《里耶秦简》中“琅琊献昆仑五杏药”不知是否为这一事件的后续。总之,该石刻的发现丰富了羌中道的历史与路线,突显了其在早期中西交流中的意义。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陈雪、郭超)
作者:葛承雍
陕西师范大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教授
仝涛研究员调查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摩崖石刻、发现石刻题记无疑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现,我说仝涛功莫大焉,实为赞扬他田野调查的辛苦,亲手触摸岩壁上的雕琢遗痕,风餐露宿,寻找新知。但我并不同意他对石刻文字的解读,因为石刻时代判断差之甚远。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
石刻存在着残破不完整的缺憾,究竟是用“昆仑石刻”还是“采药昆仑”来命名,究竟是镌刻实证还是臆想伪造,引起学界和超出学术圈的社会讨论,包括治秦汉史学者的怀疑,这场讨论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争议,似乎要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讨论。我看后提一点点建议,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
1995年7月笔者受国家文物局委派考察青海的丝绸之路申遗点,青海省文物局安排考古所几位领导先后带领我们考察申报遗址地,重点之一就是考察汉文化与羌、胡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我们进入丝路南道通向西域的重镇海晏县西海郡故城,这里是湟水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汉代城址。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大泉五十陶范
西汉中叶以前,青海绝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是羌人聚居之地,当时汉军活动地域仅限于湟水下游地段,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将率兵十万深入河湟地区,迫使羌人西走,汉王朝始设护羌校尉,专事管理羌人事宜,并成为定制。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加强监控河湟地区,先后设立金城郡管辖七县,正式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制之内。王莽当权后为炫耀威德,招抚羌人献地称臣,于青海湖环湖地区建立西海郡。由于西海郡地处偏远牧区,遗存保存较好,西海郡及下隶属五城在1983年被发现,西海郡城规模最大并设驿站及烽火台,城内多次发现王莽时期钱币和钱范。在20世纪40年代,海晏县“三角城”古城就发现了“西海郡,始建国,共河南”篆刻九字虎形石刻,1987年又发现著名的“始建国虎符石匮”,高约2米,匮盖上雕刻伏虎,篆刻“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铭文,据说原内置“符命四十二篇”。这是王莽假托天命大造舆论的产物,这么大的石刻少说也有几吨重,王莽时期符匮祥瑞氛围下的庞然大物确为全国首见。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内出土的虎符石匮(博物馆复制品)
这都提示我们,研究古迹文物一定要明白这个地域的历史风貌、历史背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些“历史肌理”,作为不可磨灭的具象印记,需要慢慢揣摩、理性分析,不可轻易说“伪”言“假”。要深入历史细部,不能借虚构之桨,驾想象之舟,去还原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场景,或是把现代个体生命体验强加到古人身上。
如此,我们再来看看“昆仑石刻”的30余字记载。
一、首先从秦汉历史背景考虑,秦代文献没有关于青海官方活动的记载,汉代历史文献才开始涉及西戎,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以财物利诱羌人首领良愿,使其率部迁出青海湖(鲜水海)、允谷(今共和县)、盐池(今茶卡盐湖)等水草丰美之地,献地归汉。西汉末年王莽当了新朝皇帝后,构建“四海归一”的政治象征,曾对青海羌人展开归降活动,派员赴青海大肆宣威,并于元始四年建立了西海郡,这是中原新朝中央政权第一次对青海的统治管理。据史书说是为凑齐“东海、南海、北海、西海”四郡体系,标榜“四海归一”,于环湖地区设西海郡,郡治龙夷城(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遗址)。青海海晏县出土新莽时期“西海安定”瓦当和“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的瓦当,应该是西汉王莽时期延续到东汉初年的证据链。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汉代“西海安定”瓦当
二、石刻上这个“皇帝”,可能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西汉末年建立新朝的王莽。王莽元始四年(公元4年)加号“宰衡”后第二年就称摄皇帝,居摄三年宣布建立新朝,国号新,始建国元年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真皇帝”。王莽派遣朝廷要员分赴全国各地,宣传新朝“皇帝”的皇威。史载“遣使者赴各地及匈奴、西域,收汉印绶,颁发新室印绶”。新朝建立前后歌颂王莽的风潮曾席卷各地,既有儒生“追随者”也有官吏“引领者”,似乎是西汉末年出现的特殊政治新样态,标榜王莽开辟新纪元。
三、王莽沿袭秦汉制度设立“五大夫”这个官职。秦代有五大夫,而王莽又依据《周礼·王制》在居摄三年和始建国四年,两次建立五等爵封制,但是王莽新朝时期“五大夫”是五个特定监察官职,这“五大夫”并非指五位官员姓氏或个人,而是依《周礼》“五事”(貌、言、视、听、思)设立五大夫,分别定名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形成专职监察系统,覆盖君主德行、君臣规范、政策透明、舆情监督、决策分析等职能。石刻上“五大夫”可能就是王莽巡狩活动派出的“臣”下“翳”,应有督查职责,并不是采药的太医或医官。王莽时期官制依据《周礼》改名换名,烦琐不堪,细节凌乱,史书有记载,不再啰唆。
四、王莽当皇帝后在儒生出谋划策下迷信谶纬,又追求长生不老,频频派人采药。王莽与秦皇汉武一样,对口服丹药、神药道术眷恋不厌,喜听方士苏乐的游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开始大搞神仙事,起八风台,种五粱禾,尤其对养性延命的情趣兴奋不已,打发宫中之人分赴各地采药养生。其实,汉成帝时期燕齐之间方士言神仙之术者以万数,汉成帝因其无子,耗费巨资寻求不终之药(长生药),方士声称可“入海求神采药”。正直敢谏言的谷永痛批采药求仙的荒谬。汉代皇室派人求药之事多次出现,因而王莽朝中方士也不少,例如史书记载的涿郡方士昭君等专给他讲道术。因而,携带方士随车队“西巡”是堂皇亮相的皇命,下车“采药”则是隐性实在的差遣。青海高海拔地区是冬虫夏草采药之乡,以玉树、果洛为核心,辐射三江源及省内多州市高海拔草甸,本土药物资源丰富,“采药”的摩崖石刻出现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了。
五、石刻每列的首字几乎都有石层破损笔画缺失,细辨“廿六年”,由于残破断缺,不能肯定地说就是秦始皇廿六年。“六”很像“元”字,疑为“元年”,王莽有“天凤元年”“始建国元年”年号。“廿”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曾令太史令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自言“己如黄帝仙升天”,以此诳哄百姓。这一时期历法变动搞得人们不知所措,但是现在发现的石刻具有王莽新朝时期的鲜明特征,一些字呈扁平形,有的呈竖条状,与“虎符石匮”字体相比非常接近,王莽时期就是常用这类字体做复古表意,不少“新莽”文物留下复古周礼的痕迹。有人说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恐是因不了解篆书发展的误判。
六、残破的“翳”字,很可能是“王翳”。《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初因功封臣有一个王翳,但是几百年过去了,这个石刻的“翳”或许是王莽委派的一个王姓宗室官员,汉成帝时王家就有五人担任大司马,九人封侯,当时王莽封了一大堆王姓宗族官员王舜、王寻、王邑、王兴、王盛等,分遣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驰传天下,颁行符命,到各地宣称他的“皇威”,刻石树标,表示立新代汉是顺乎天意,求得人心安定与世间太平。王莽新朝被授予王姓宗族至少有几百人,史料有限无法精确统计所有被封官人数,所以石刻上王翳究竟来自何处只能待查了。
七、王莽派出的十二支宣威小分队,东西南北都有“车”以示雷厉风行,有时以四马大车“建虎旗”示威天下,有时命五威将坐着绘有天文图像的车子“驰传天命”。原来从汉武帝到王莽时期就有各式各样的“车”纷纷亮相,青海省博物馆曾展出考古出土的汉代木轺车马,文物比比皆是,不再多说。王莽时期五威使者乘车“驰传天命”安抚人心是当时一项政治任务,王莽“变法改制”其中一项就是按照《周礼》行巡狩礼,天凤元年二月建寅之节开始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依次巡劝各地,督民农作,获粟藏粮。从石刻上有“一百五十里”来看,刻工粗糙欠规范,只是在沿途岩壁局促的空间做局促留刻文字,可能在此场合做一个简单的题铭仪式,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难以携带巡劝成果返回长安复命。
八、关于“昆仑”一词,史书作“崑崙”或“昆侖”,多年来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是外国文字对音或匈奴阿尔泰语的音译,2000多年来中国人都认为昆仑是一座名山或仙山,因此有“神的昆仑”和实际的昆仑、中古境内昆仑和异域昆仑之分,很难有人能面面俱到解释“崑崙”之义,究竟是颜色之意还是种族族名,《竹书纪年》《尚书·禹贡》《逸周书·王会解》《史记·夏本纪》《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都有著录,不拟重复引书论述,但昆仑一语与西北民族、地理有密切关系则是无疑,王莽派人求药的“昆仑”,也是一个远不可及的、笼统的地域代名词罢了。秦人寻药与汉末采药都是方位不清的“昆仑”,至于说“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恐怕还“实证”不了,见仁见智,不再赘述。
总之,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而是后来王莽时期派使采药和巡视宣威的石刻。时代不一样,中间隔了200多年,正因为时代相距不同,所以文字书法、干支历法、词语辨识、砂岩风化,所有的证据法都靠不上、挂不住,用前代逝去的历史去释读后代产生的石刻文物,怎么能不疑点重重,怎么能有说服力。出土文物必须和历史文献相印证,既要“眼界高”还要“细节控”,凭空猜想只会误入歧途,信口开河说“这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更是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辩驳。西北大学已故老先生陈直教授生前曾教育我们学生说,要能懂秦汉史必须读懂《汉书·王莽传》,几十年前我写过《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儒生、儒臣、儒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对王莽时代种种复古历史现象做过一些探讨,后来研究领域转行不再专业钻研秦汉,但对新莽时期出土钱币、度量衡、简牍、金属实物等文物仍怀有热情关注,所以提出一点点建议供学界参考。
石刻横空出世,穿透秦汉历史,七旬老人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听凭历史慢慢考释落实,直到最终能还原本真面貌。历史中很多真实故事都会因为年代久远、磨损、破碎,消失在时间的长廊,考古文物只有借助同时代语境的社会历史文献,才能将历史可靠地真正复活。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陈雪、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