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玉友对玉石市场观察仔细,就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无论什么料子,最便宜的都是珠子——边角碎料皆可成珠,机器量产,成本低廉;可最难得、最稀罕的,却是器皿、玉瓶、印章这些“成器”之物。为何?全在“舍”与“得”。
何谓“成器”?
并非所有玉雕作品都能“成器”。它特指对材质、工艺、气韵要求臻于极致的作品。
成器首推器皿。无论是炉、壶还是其他器皿,都必须取料方正,体量规整,容不得半点绺裂瑕疵。一块成器料,必能出顶级手镯,反之则未必。
玉瓶更进一层。因瓶身大面积素面,对玉色的白度、均匀度近乎苛刻。传统制作需匠人以运笔般的腕力雕琢线条虚实,纯净白玉大瓶如今已是凤毛麟角。
印章则重“老味”。”尤指体量规整、钮饰精雅的大印或玉玺,既要材质纯净能取方正,更需印钮雕刻蕴含古意,线条挺拔而气韵沉稳。
成器之贵,贵在“舍得”
成器之所以能立于和田玉价值体系的顶端,其“贵”绝非偶然。它贵在一种贯穿始终的“舍得”精神——这既是对珍贵材料的果敢取舍,也是对繁复工艺的极致克制,更是时代变迁下敢于坚守的孤勇。这份“舍”与“得”的辩证,构成了成器最核心的价值密码。
材质之舍:大刀阔斧的勇气
成器的第一步成器始于“舍”。”欲得器皿之方正、玉瓶之大气,必先狠心削去多余玉肉,只留最规整的核心。同样一块料,切珠子、做挂件可能绰绰有余,但要成就一个方正规矩的瓶、炉、印,就得大刀阔斧地“舍”去大量好肉!不舍,就得不到堂堂正正的器型。这一步,是勇气与决断的起点。
“舍”的代价,是高昂的成本与极度的稀缺。米达料打珠子细腻油润,但用它做器皿者寥寥无几。我倾尽矿山之力,三年积累的好料,最终成器的不到十件。能做器皿的料,本就稀少金贵,每一刀下去,“舍”掉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器皿之道,容不得半点侥幸,唯有一刀下去,舍掉“钱”,方得“器”。
工艺之舍:极简背后的真功夫
成器的工艺精髓,恰恰在于“做减法”。不同于人物开脸、动物镂空等显性炫技,一件素面器皿或规矩玉印的美感,仅靠几道精准的线条与流畅的弧面来呈现。极简意味着无处藏拙——线条是否挺拔?弧面是否饱满?比例是否协调?稍有差池,瑕疵便暴露无遗。这要求匠人拥有绝对的“创作自信”,敢于舍弃繁复雕饰,以最凝练的功力呈现造型本质。
这“舍”,是舍掉炫技的浮华,回归最本质也最艰难的“型”与“韵”。它要求匠人不仅手艺精湛,更需具备极高的审美素养,才能把握那“多一分则赘,少一分则亏”的微妙平衡。
放眼当下市场,珠子手串、花鸟小件俯拾皆是,但体量规整、材质上乘的大器(器皿、玉瓶、大印),却踪迹难觅。尤其白玉成器几成绝响,这困局,是多重“难得”叠加的苦果。
材料难得:成本与风险的重压
成器首关,便是良材难求。无论籽料、山料,欲成大器,料子必须体量充足、纯净无瑕、规整完美。这些顶级白玉料,如今价已堪比黄金,是成器的第一道高门槛。动刀取其方正规矩,意味着大刀阔斧削去大量玉肉,损耗惊人。每一刀下去,投入的都是真金白银,风险如山压顶。
市面存世的成器,大都成于国营玉雕厂时期,只因那时材料国有,损失由国家兜底,匠人可心无旁骛,放手施为。而今私营工作室自负盈亏,面对顶级原料动辄过半的损耗风险,敢于下此重注者,寥寥无几。成本与风险的双重重压,让良材难觅亦难用。我曾遍寻韩料、迪拜料、青海青乃至罗甸料,试图降低成本,却皆因价高或质次难成器。
工艺难得:断层与门槛的双重困境
成器工艺的传承,几近断层。昔日国营玉雕厂,匠人必经严格进阶:从杂件(花鸟鱼虫)起步,功底扎实后涉足人物、山水,最终唯有刀最稳、心思最缜密的顶尖好手,方能进入炉瓶车间承制重器。如黄永顺、刘小华、焦一鸣等大师,都是出自玉器厂。如今,这套培养路径早已消失,当世能担此任的顶流大师,屈指可数,不过樊军民、高毅进、杨光、王金高等为数不多的几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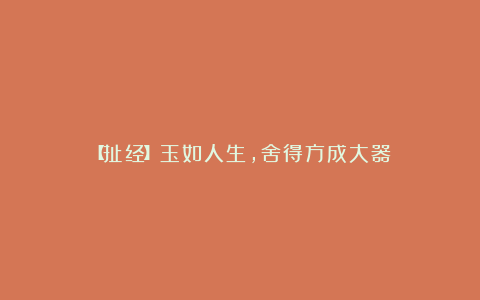
玉瓶之难,尤甚于寻常器皿。其传统制作需依赖吊机或角磨机,匠人需如运笔作画般凭腕力操控,对“笔触”的力道、节奏要求极高。这种操作方式,要求匠人不仅懂玉雕,更需具备深厚的书画功底与整体布局能力,方能在瓶身的大开面上驾驭线条的虚实流转与气韵贯通。
更令人忧心的是配套技艺的衰微。老一辈匠人以毛笔勾画设计稿,其线条的虚实变化与气韵是硬笔设计难以企及的,如今只有樊军民、顾铭、杨光等寥寥几位大师掌握此法。而器物上阴刻大气古雅文字,更是一门濒临失传的绝艺。技艺、工具、审美素养的多重断层,让成器之路举步维艰。
曾有玉友参观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后问我:为何馆藏尽是器皿大件,而市面流通多为手把件、挂件?表面看,是国家收藏重文化传承,民间偏好尚佩玩之趣。但更深层的真相是:真正的成器,在市场上已近乎绝迹。今年春拍,我们倾尽全力,仅征得三件成器。市场上白玉重器已成绝响,即便是樊军民、高毅进等顶流大家,近年也多在青玉、碧玉间耕耘。
这困境,恰是“成器之道”最深刻的映照——敢“舍”,方“得”大器。舍去的是冗余的玉肉、浮夸的炫技、稳赚的捷径;得到的,是器型的永恒、线条的张力、文化的重量。这取舍间的勇气与智慧,正是华夏造物精神最凝练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