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10日,南京城外江面上三艘巨舰近在咫尺,大舰“康沃利斯”号的炮口距离静海寺山门只有500米,妥妥的武装威慑,带来沉重的压迫感。城内大小官员心里估计只想一件事:今天英军是否会开炮攻城?根据《复仇女神号作战记》记载:“各艘战舰都被分配到了适当的位置,以备对这座城市(南京)实施必要的轰击。城墙距离江面最近的点有约700码,最近的城门(仪凤门)约1000码。’康沃利斯’号、’布朗底’号和重型蒸汽船(复仇女神号)已经布置妥当,以便在需要时攻击城墙。”
半个月后,和谈终于结束。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沃利斯”号上正式签署,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当天签约之时,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普拉特绘有《南京条约签订图》草稿,之后回到伦敦由英国官方制版印刷。
此画之中,绘有英军51人、大清5人。各位的相貌、服饰还是相当精确的。正中围绕圆桌坐的,是大清帝国的4位谈判参与者和英国翻译罗伯聃。从左起: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赏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还有一位四等侍卫咸龄,穿红衣坐在右侧前排。
虽然画面以钦差大臣耆英为C位主角,但他脑门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显然是带有宣传胜利的意义。
耆英
画面中的耆英红光满面,此时他在英军的评价中还算不错。
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的副官洛赫在回忆录中评价说:“钦差大臣耆英,非常应当得到他的国家的感激以及我们的善意和尊重……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步履稳健,身姿挺拔。起初我们对他的智慧禀赋存有偏见,但当开始处理事务时,他摆脱了表面上的沉闷,变得十分活跃,并表现出相当的城府和观察力。”
一路积极推进了战争的传教士郭士立(居茨拉夫)认为耆英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
伊里布
至于从很久之前就主张“抚夷”的伊里布,英军上下对他颇有好感。
郭士立在信件中聊起《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的伊里布说:“伊里布年老体衰,他曾长期担任各省长官。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阳寿无多,所以显得非常迷信,成天攥着念珠在他的喇嘛像面前祈祷……我非常热爱这位老者,他是和平的使者,已经为这个帝国做了那么多。”
在之前打打谈谈以及开始南京谈判的过程中,伊里布被英军认为相比其他清朝大员更加靠谱。他没有狡诈的反复摇摆,并且批准释放了被俘的英军少校安突德等人,所以在英军那里评价颇高。英军知道伊里布身体不好,璞鼎查的医官吴士南还拿了药,通过幕客张喜送给伊里布。结果呢,据记载,张喜贪杯好酒,弄丢了药品的说明书,导致伊里布把原本应该分几天服用的西药一次性吃了。于是后果挺严重,签约当天的伊里布甚至差点站不起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巴夏礼,此时仅仅14岁,是璞鼎查的少年仆从。他因为身份太低,还是远征军中的一个小角色,没能进入画面。他的笔记说:“(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这个可怜的老人(伊里布)病得很重,他是坐在椅子里被抬上来的。璞鼎查、司令和将军都去帮忙把他抬到船舱的后部,安置到沙发上。程序进行得很快,我们不希望伊里布被累着。”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画家特意给了伊里布一个“阴影待遇”,不但脸色灰暗,而且处于黯淡光影之中。
黄恩彤
在几周的谈判过程中,大吏们是不屑于(或不敢)上舰谈判的,所以耆英、牛鉴等人是高坐城里端着架子,指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带着四等侍卫咸龄去跑前跑后搞夷务的。对于黄恩彤,英军对他评价也不错。
洛赫记载说:“财政大臣黄(恩彤),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由钦差们派来交涉条约初步准备工作的人,他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
郭士立认为黄恩彤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友好又开朗,他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渴望倾听并提升自己的观念”。
翻译马儒翰对黄恩彤的印象也非常好。他发现“在谈判时随员越少,黄恩彤在讨论问题时的态度便越开放。”
牛鉴
在当时实际的大清帝国官场排序中,牛鉴牛大人本应该是仅次于钦差大臣耆英的2号人物,但英方对于牛鉴的评价极低:
“总督牛(鉴)将军是一个老派的汉族官员,对官场生活中的所有阴谋都了如指掌,但却无法触及更高的真理。”
“牛鉴坐着,没有任何明显的或是值得注意的动作,他一杯杯地喝着樱桃白兰地,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满意的吧嗒声。”
“牛(鉴),据说是皇帝的近亲,他的名字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阉牛’,而且看起来也像是和那种动物差不多的大块头。”
“(故意用外号称呼)牛羚,那位江苏和江西两省的总督……”
所以在画面中,画家不但给了牛鉴一个侧跪沙发之上的待遇,还特意画了一根细细的金钱鼠尾辫子。
英军之所以对牛大人评价这么低,在于他确实是一个不讨喜也无作为的“老派大吏”——战争打了两年多,已经打到南京了,可牛鉴作为一直在江苏主事的大吏,又才接了两江总督,但他却连敌人的头目是谁都不知道。1842年7月27日,英国舰队出现在南京江面上,吓得牛鉴连发两道照会,送去英国人那里试图乞和。他的第一道照会给了璞鼎查,第二道照会竟然发给了远征军中的翻译郭士立和马儒翰,称呼人家“统兵大宪郭、马”。在此之前,英军各种行文给大清江苏当局,落款都是“大英统领水陆军师大宪巴、郭”,即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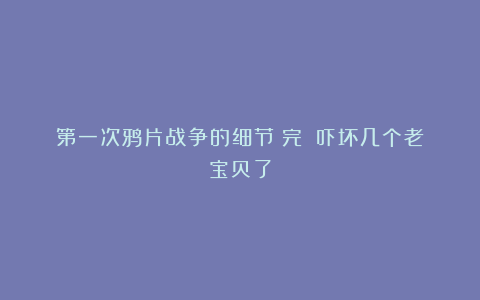
于是乎,只对道光大皇帝负责的牛鉴,他这种缩在南京城里官气十足、颐指气使,上了军舰颤颤巍巍、一言不发、闷头喝酒的形态,也难怪英军对他没有什么好评价,文中讥讽,画中丑化,属实也是活该了。
咸龄
对于整个签约的过程,巴夏礼记录说:“首先,(翻译)马儒翰代表(全权代表)璞鼎查在条约上盖章,耆英的秘书(黄恩彤)则在另一边盖章。他们所盖的分别是璞鼎查的印章和帝国钦差大臣的印章。这一项完成之后,桌子被移到沙发旁边,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分别签名……然后亨利爵士(璞鼎查)签了名。他们在四份合约的复本上盖章、签名。每份复本包括一份英文条约和一份中文条约,用黄色的绸带绑在一起。这些程序结束之后,他们离开了后舱,坐下来一起吃点东西。”
一起跟随大吏们上船的另外几位大清随员,比如张喜、舒恭受、颜崇礼,因为画面容不下了,所以就没有出现在这幅宏大叙事之中。
其中张喜字小沧,北直隶天津县人,先在舒炘幕府,然后又侍奉伊里布。他是这次谈判中伊里布所倚重的跑夷务的幕客。张喜留有一部《抚夷日记》,读起来相当有意思。比如他记载壮烈殉国的裕谦之死,实际是“裕大臣投塘未死,逃至余姚,吞烟自尽”,记载1841年底的北方官场“南北各省人心慌慌,天津等处海口戒严而京城内外慌惧尤甚”——实际上他记载的“人心”是官场的“官心”,真正底层大清百姓根本不太知道或不太关心这场鸦片战争,倒是大清官场上那些官员们,确实在那年前后被吓坏了。张喜当时抱病也不想去,但伊里布最后还是把他叫去了江苏,跟着帮办夷务。
他记录了签约完毕的情况,大意是说:当双方盖章签字完成,众人表情或轻松或欣喜(包括清朝几位大吏,因为麻烦事终于结束了)。英夷在大舰中桅上升起了一面黄旗,该舰还连续放炮二十一响,据说是英夷国王寿辰(实际是礼节)。耆英和牛鉴听了炮响,吓得面容失色。
这一点呢,在巴夏礼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条约签订后,中国的黄色旗和英国国旗在船的后桅升起,同时有21发皇家礼炮升空。一些满人去看,但是他们很快就吓得退了回来。”
这时的耆英和牛鉴,估计心里在想:英夷不会才签字就翻脸要攻城吧?!
为什么我猜他们会这么想?因为大官们一直以来在日常中、在官场上、在战争里,都是惯常使用炸术的,他们以己度人,估计会有这种想法。
耆英在签约之前“唯恐英夷将其扣留”,在签约之后又听见礼炮声而“面容失色”,原因都在于此。不过到了1843年,耆英、黄恩彤继续去广州办理后续事务之时,耆英就显得见过世面了,举止轻松多了,也优雅多了。他在香港的排场极为宏大,表现相对优秀。
至于黄恩彤后来历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一直在办夷务,直到后来面对英国人要进广州城的要求,他终于没有搞定,被参劾降级使用。
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战争,留下的伏笔,终于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才逐一解决。这种感觉,就和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一样。
签约完毕,宴会结束,在“康沃利斯”号发射礼炮之时,一旁的“布朗底”号战舰舰长沃森将这个瞬间绘制成画。可以看到“康沃利斯”号主桅上的大清帝国黄旗,礼炮产生的烟雾,以及英舰上船员正在行“站坡礼”。
74门炮的三级战列舰“康沃利斯”号其实是一艘“英属印度造”,于1813年在孟买的英军船坞下水,造价5万多英镑。参战的不少军舰其实都是在孟买船坞下水的军舰,5级舰大概2.5万英镑,6级舰大概1.5万英镑,相比清朝大吏们的家底,其实真的不贵。
在《抚夷日记》中,张喜还对照大清帝国官职系统,给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们都编制了大清式名称,读着很有意思:
英吉利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世袭男爵、三等将军,璞鼎查;
英吉利国提督陆路军务、二等将军、头等尊烈巴图鲁,郭富;
英吉利国提督水师军务、二等将军、二等尊烈巴图鲁,巴加;
又比如英国马德拉斯炮兵团的上校Montgomery,张喜翻译成:英吉利国护理总兵火器营参将、三等巴图鲁,文珂美;
马儒翰,他翻译成:领事署经历、汉文知事译官,马礼训。
总之,大清帝国基层办差的人员,已经比1839年开战之前对英国人有了更多了解。英国海、陆军各级将、校依次被对译为清军的将军(从一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都司(正四品),尉级军官被称为守备(正五品)或千总(正六品)。对于更特别、更复杂的勋爵名,如“G.C.B.”“K.C.B.”和“C.B.”三个等级的巴斯勋章,《抚夷日记》巧妙地将之与清代传统封号“巴图鲁”进行系统性对应,分别记为“头等尊烈巴图鲁”“二等尊烈巴图鲁”和“三等巴图鲁”。虽然张喜将璞鼎查不能世袭的“从男爵”爵位记作世袭男爵,但是瑕不掩瑜,不懂英文的张喜可以总结成这样,很难得了。
至于《南京条约》本身,它签了什么,不平等在哪里,不赘述了。
额外补充一条:
1842年7月16日,在英军经过镇江附近的焦山时,璞鼎查的随员麻恭和医官吴士南一同在“女王”号轮船上进行了一次照相实验。麻恭、吴士南虽然事务繁忙,但却耗费了大量时间来进行相机试验,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记录即将到来的盛大签约场景。他们用的当时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照相法。但该技术并未成熟,步骤又过于烦琐,二人的实验很可能没有成功,因此也未见有照片流传下来。最终,英国人还是选择以绘画的方式记录签约场景。
巴夏礼记载说:“麻恭少校和吴士南医生今天用他们的银版照相机拍摄了这个地方的剪影。我完全搞不懂它的原理:只是在借助一些玻璃将一块高度抛光的钢板暴晒在太阳下时,它会将你面前的景象传到钢板上,拍下的影像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在板上留存数年之久!我没有办法描述它,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谜。”
很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相机已经有了,所以那次战争留下了很多真实的摄影画面。
这场战争打完,其实绝大多数帝国子民,包括大多数士大夫们,他们都没有任何感觉,甚至不知道有过这么一场战争。除了朝廷捂的好,也是当时信息不发达的原因。至于统治者本身,没有学到任何一点经验或教训,属实是学费白交了。所以后来又反复折腾很多次。
1848年大皇帝道光与老四、老六的阖家欢乐
如今距离《南京条约》的签订已经183年,有些事变了,有些事似乎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