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hinking Robert Hans van Gulik and the Scepticism of the Literati Tradition of Guqin
欧阳霄 /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琴道》是当代琴学研究的里程碑,书中针对“古琴的文人传统的真相”的怀疑立场及其相关论述尚待商榷。高罗佩强调道家和佛教在古琴艺术史上具有实际的主导地位,这为其文人琴怀疑论调提供了重要的内在依据,然笔者认为相应观点并未建立在可靠的论证基础之上。高罗佩对古琴文人传统的批评不乏真知灼见,也的确揭示出古琴在独特的文人琴学观念与琴乐实践影响下的命运悖论。然而,高罗佩对复杂的琴史加以简单概括或者过度推论,尤其是忽视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对中国文人琴乐传统生成的重大影响。本文最后结合文人画研究,阐发中国文人艺术与文人琴的特质。中国文人艺术倾向于超越具体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实践中探索意义与价值。笔者认为丹托对艺术性来源的申索及其去审“美”化主张与文人艺术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文人生活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弹琴“为己”而非“为人”,琴乐“自况”“自适”“应心”的诉求拒绝表演心态。从自我需要出发,致力于超越具体音乐形式而在音乐实践中涵养性情、探索更为深刻的体验与意义的旨趣,正是文人琴的本质特征。区分文人琴与其他琴乐实践的并非表面的审美标准或音风格的差异,而是“艺术意图”的不同。
关键词:文人琴、高罗佩、《琴道》、音乐风格
荷兰职业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其所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是古琴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专著,被视为海外琴学研究的里程碑。该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为中外琴学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性的参考文献。然而,笔者认为,由于一些文献的缺漏、错误以及其他历史局限性,《琴道》一书针对“古琴的文人传统的真相”所持有的怀疑立场及其相关论述尚待商榷。本文尝试从高罗佩自身论述出发,结合其他琴学文献,反思高罗佩对文人琴传统的质疑,检视其相关论点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古琴以及中国文人音乐进行初步的界定与澄清。
一、高罗佩对古琴文人传统的质疑
高罗佩曾在 1938 年写道:“……尽管我对文人琴乐传统有所质疑,但这丝毫没有阻碍我对琴乐的热情。”这段话后来在 1940 年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琴道》中被删除。深受当时中日两国学界盛行的疑古思潮的影响,高罗佩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可信度往往存疑。在论及“古琴的起源”时,他断言不仅“文献材料是不充分的”,而且“这些材料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是为了与儒家思想的文人传统相一致而人为制造的”。高罗佩甚至颇为激进地认为,获取“古琴古老历史的模糊信息”的唯一方法,是“将文人传统放在一边,而集中于对与琴相关的古文字学的研究”。比如,通过考察汉字“琴”和“瑟”的古字形,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大胆的假设——“琴”“瑟”二字源于同一古文字,而此古文字则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弦乐器的象形。
高罗佩认为,问题重重的“琴的文人传统的真相”除了包含大量有待证实的表述之外,还具有排他性的精英主义及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特征。他写道:“琴从来不是一种大众乐器,无论是理论因素还是实践因素,都阻碍琴的普及化。”“琴依旧只为少数幸运的小圈子文人所享,被文人当作珍宝嫉妒猜疑地守卫着。”他引用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J.M. Amiot,1718—1793)的观察来论证琴的排他性精英主义——“琴被少数阶级所有,古琴的学习’天经地义地属于那些致力于文学和智慧的少数人’,也就是文人”。高罗佩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形)不仅出现于乾隆年间,也就是饱学的钱德明神父在华的写作期间,还贯穿在这之前的整个两千年间”。在书中另一处,高罗佩同样指出“独奏形式的古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文人阶层的特殊乐器。从上古时起,它就占有特权地位”。
对于文人传统中饱受诟病的形式主义做派,《琴道》也进行了较为强烈的批评。被视为“文人生活的象征”的琴,是“中国文人书房中不可缺少的一样器物”。然而,与琴在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形成对比的是,真正拥有精湛琴艺的文人却十分罕见。高罗佩写道:
所谓文人的“必备之物”,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成了个传统:正如书斋中陈设有棋盘,并不意味着它的主人热衷于这种高雅的游戏;古琴的陈设也不一定意味着书斋的主人真能演奏古琴。理解琴的独特的思想体系,是每一个士人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少数的士人精通琴乐。即便如此,倘若能够以崭新的形式诠释某些已为人熟知的琴学之道,或者能够赋诗咏赞一张偶得的琴的独到之处——哪怕主人并不擅弹奏,亦可被认为具有高雅的趣味。
高罗佩认为这种现象在清末更甚,只有“众多文人中屈指可数的少数人”能够实际上地演奏。高罗佩认为正是文人“众多高雅的借口”,尽管“在哲学上有一定意义,但却挫伤了文人在成为出色琴家上的积极性”,并导致了古琴艺术走向衰落。与高罗佩从历史文献和琴乐实践两方面对古琴的文人传统进行质疑密切相关的,是高罗佩对于道家和佛教在中国古琴艺术史上实际的主导地位的强调。事实上,《琴道》所主张的佛、道两家在古琴艺术上有着实质或根本性影响的观点,为高罗佩对古琴的文人传统(亦可简称为“文人琴”)怀疑论提供了重要的内在依据。然而,笔者认为,高罗佩的相应观点并未建立在可靠的论证基础上,下文将梳理并反驳之。
二、高罗佩论道佛两家对古琴艺术的影响
(一)古琴与道家
高罗佩明确提出道家思想是琴道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
以上提到的两种思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哪一个对琴的思想影响更深呢?在我看来,答案必定是道家思想是琴道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也许有人会说琴学基本思想的宣讲形式是儒家的,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典型的道家的。
这一论点是高罗佩在分析晚明文献中关于琴乐审美标准的探讨时提出的,但显然他将其泛化成了对古琴艺术史的一般性观察。毋庸置疑,古琴艺术的发展深受道家思想及其审美旨趣的影响,琴史上亦不乏以琴闻名的道家人士,但道家是否如高罗佩认为的“主导”琴道发展,却值得商榷。
由于《琴道》对宋明儒学发展的整体性忽视,高罗佩倾向于将其所用文献中频繁出现的“道”字视为道家的专用术语,而未曾将“道”与当时兴盛的理学思潮相联系。严格来讲,高罗佩所认同的儒道思想分野只符合先秦的特定语境——这也是许多海外汉学研究的通病。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史上儒道思想早已不断交融互鉴,直接援引佛老思想来解释宋明古琴艺术实践的某些具体现象,往往似是而非,甚至张冠李戴。基于其思想坐标的错置,高罗佩在界定儒道思想各自对文人琴传统产生的影响方面就显得生搬硬套,而为符合其概念框架所作的论证也不免牵强附会。
很 可 能 受 到 杨 宗 稷(1863—1932)“ 琴与道家为最近”一语的影响,并且出于对“道”的狭义化理解,高罗佩在翻译和阐释杨表正(1520—1590)《重修真传琴谱》中《琴有十四宜弹》(即十四种值得弹琴的情景)这一文本之时,似乎刻意将之解读为道家在琴乐文化中地位卓著的证明。比如,高罗佩将《琴有十四宜弹》中“对道士”一条翻译为“For a Taoist recluse”,即对道家的隐士弹奏。在杨表正的时代,“道”是中国不同思想流派共享的核心术语,“道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儒学正统的、官方的名字,一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在其年谱中便被称为“学道之人”。17 世纪中叶的琴乐美学著作《溪山琴况》在评论“道人弹琴”时,引用了朱熹“诚实人弹琴,便雍容平淡”作阐发,可合理推断“道人”是指以理学功夫(如“诚敬”)修身涵养者。尽管“道士”这个名称往往专指道教修行者,但结合历史语境,笔者认为将此处的“道士”理解为“有道之士”这一更为广泛的指称或许更加妥当。“有道之士”的“道”可以是理学之道、老庄之道。琴被誉为“有道之器”,且有时简称为“道器”,但这并非在标榜琴乃道家或者道教之专属乐器。《重修真传琴谱》卷三所录《琴有十四宜弹》具体为:
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峰、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明,当清风明月。
这一文本分别规定了理想的欣赏者(前三条)、演奏地点(中九条)和时机(后两条)。在前三条中,“知音”“可人”的重点都不在于界定听琴者的具体身份背景,而在于对听琴者的品性特质及其与弹琴者关系的要求。相应地,不将“道士”作具体宗教身份理解而释为博学有道之人,似乎更符合文本的内在逻辑。此外,除最后两条为五言外,其余均是三字短语,或可合理推测,创作者将对“有道之士”一意缩写成“对道士”以求行文的对称与连贯;而不用“对道人”或为避免重用“人”字。
事实上,弹琴的“忌宜”在明代以来刊印的琴谱琴论中并不鲜见,除了对演奏和欣赏语境的规范之外,“忌宜”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对弹琴之人身份的规定。自南宋田芝翁《太古遗音》及其衍生曲谱集问世以来,宜弹琴的“五士”(黄门士、隐士、儒士、羽士、德士)和不宜弹琴者如“武士”“商贾”“优伶”“番语者”“百工技艺”及“丧门”(即沙门,指佛家)等几成琴学常识,被不同谱论辗转抄录。其中,操琴“五士”之一的“羽士”的确专指道教修行者,而以广为流传的《五士操图》所举的“五士”(东方朔、许由、孔子、黄帝、伏羲)来看,选取的也均是儒家同时尊崇的圣贤;根据“五士”与五行、五音的对应关系,居于黄钟之宫、对应中心土相的是“德士”,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与宋明之际儒家背景的士人逐渐巩固的对琴的文化专属密切相关。
依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琴有十四宜弹》这一文本确乎首见于杨表正的《重修真传琴谱》,其中所录《弹琴杂说》中的一段文字可供比较研究:
……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观宇中,值二气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静室坐定,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与神合灵,与道合妙……
对比《琴有十四宜弹》,可见二者内容的高度相似。然而,《弹琴杂说》通篇则没有明显的对道家的强调,相反,其中清晰可见的是宋明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琴者,禁邪归正,以和人心,是故圣人之制,将以治身,育其情性……抑乎淫荡,去乎奢侈。要鼓琴,要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之像表,方可称圣人之器。德不在手而在心,乐不在声而在道,兴不在音而自然可以感天地之和,可以合神明之德。又曰:左手吟猱绰注,右手轻重疾徐,更有一般难说,其人须要读书。
这些论述将琴乐实践与儒家修身工夫相联系,也与《乐记》中的音乐理论高度契合。当然,《琴有十四宜弹》和《弹琴杂说》传递出最明显的观念是强调琴乐审美当与自然环境相结合,这在《琴学须知》一则中也有所呼应:“必欲知其所忌,尘中遇俗不遇知音,勿妄动圣贤大乐,宜对清风明月、苍松老石为佳。”然而,在宋明理学所濡染的生活世界,很难说强调鼓琴的自然环境便是道家主导,从理学格物穷理、涵养功夫的思想背景出发,亦可获得丰富的直接印证。
此外,《弹琴杂说》中的“观宇中”似对应《琴有十四宜弹》中的“在宫观”一条高罗佩将“在宫观”理解成“在道观”,译为“In a Taoist cloister”,也将内容狭义化以凸显道教与古琴艺术的关联。然而,“观”的本义指的是宫殿入口处类似望楼的建筑——“观谓之阙”,后来用于宫殿(尤其是大型宫殿)的命名。著名的如位于未央宫中的“白虎观”,因建初四年(79)举办了讲论儒家经典的盛会“白虎观会议”而青史留名;又如《太平御览》中列举了数十个包含有“观”字的宫殿名。无论是“观宇”还是“宫观”,其实都不必然特指道观,而可指广义上的宏伟建筑。
综上,笔者认为,高罗佩并不能借助杨宗稷“琴近于道也”的观点以及杨表正《琴有十四宜弹》中似是而非的“道家”色彩来佐证“道家思想是琴道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的观点。事实上,《重修真传琴谱》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杨表正将其时流传已广的源自《太古遗音》系统的“五士”顺序重新排列,明确将“儒士”提至首位,联想到《重修真传琴谱》中收录“莆田梅里山人”所题《赞杨君表正小影》中透露出的杨氏乃大儒龟山先生杨时后裔的信息,这或许并非无心之举。当然,考虑到杨表正引以为傲的自创琴曲《遇仙吟》的相关事迹,其人确对道教修仙颇具兴趣,但这在“出入佛道”的宋明士人中并不特别,无法支持高罗佩“道家思想是琴道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的观点。最后,即便我们可以接受高罗佩对《重修真传琴谱》中琴论的所有释读和判断为真,鉴于该琴谱的代表性颇为局限,并不能支持他对明代琴乐艺术做整体判断,更遑论整个古琴艺术史。
(二)古琴与佛教
为了证明古琴受到了佛教的直接影响,高罗佩援引了颖师、义海等著名琴僧的事迹,并声称:
一些印度僧人在来中国传教时,也带来了和古琴类似的乐器,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这些异域乐器。像宋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欧阳修(1007—1072),就在一首诗中赞赏了和白(知白)和尚对印度乐器(可能是印度弦乐器 vīnā)的演奏。
高罗佩在此处的注释中标出了其中所引欧阳修的著名诗篇《送琴僧知白》,却没有附上原诗全文。需要澄清的是:第一,此处以琴艺闻名的和尚的名字是“知白”而非“和白”,“知”“和”二字字形相近,《琴道》一书写为“和白”当是笔误;第二,高罗佩认为知白演奏的是印度乐器并称其可能是 vīnā 琴的观点明显经不起推敲。欧阳修《送琴僧知白》诗云:
吾闻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无其传。
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
…………
负琴北走乞其赠,持我此句为之先。
诗中提到的“夷中”是知白的师父、另一位著名琴僧的名字。虽然“夷”字确有“外国的”之意——高罗佩很有可能正是被这一含义误导而判定知白和尚向欧阳修演奏的是印度乐器,但诗中的“夷中琴”意为琴僧夷中之琴艺。知白弹的就是被誉为“圣人之器”“有道之器”的古琴,不会是什么印度乐器。其实,在欧阳修好友梅尧臣《赠琴僧知白》一诗中就有清楚的佐证——梅诗云“上人南方来,手抱伏牺器”,而“伏牺器”正是琴的专有别称,这与古琴起源的圣人制器论有关,一般认为三皇之一的伏羲(也写作“伏牺”)是琴的创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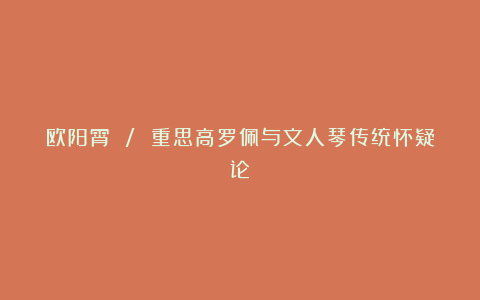
第三,仅仅依凭部分著名琴家是僧人,就断定中国琴乐及其实践直接受到印度音乐和佛教的影响,这未免草率,且在史实上、逻辑上均难以成立。无论是琴僧夷中还是其弟子知白、义海都不是印度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已约一千年,早已和中国思想与文化充分融合,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事实上,传授夷中琴艺的是被誉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鼓琴为天下第一”的宫廷琴师朱文济,据说夷中“尽得其法”。
简言之,高罗佩给出的以上例证均无法证明佛教或者印度音乐对古琴有直接影响。在《琴道》的附录三《古琴——古董》一文中,高罗佩还以日本正仓院所藏金银平文琴(图 1)上绘有抚琴人物形象的“面板图案”(图 2)为证做过推断。高罗佩指出,尽管这一图案的主题可以断定为“兰亭雅集”,但其图像设计却隐含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非中国的主题”,它包含了受“大乘佛教的庙宇”“大乘佛教的神格”“印度神话”影响的“佛教表现”与“印度元素”。如果我们将高罗佩使用的图像与南京西善桥 1960 年出土的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墓葬砖画(图 3)相比可以发现,二者在细节上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基本上可以判定,金银平文琴上绘制的三人并非高罗佩所言的王羲之及友人,而是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咸和阮籍。
图1 唐代金银平文琴,日本宫内厅正仓院藏,图片来源:日本宫内厅正仓院文物数据库
此外,高罗佩所引图像证据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了印度或者佛教元素而非魏晋玄学元素是需要被讨论的。当然,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存在与影响力的话,那么高罗佩所找到如下的关联来说明佛教和印度影响,似乎就很有说服力。比如,对比“琴坛”(其实往往指的是置琴的琴几)的陈设与《毗卢遮那佛经》中关于择地设坛的说明,二者在偏爱自然隐幽的环境上如出一辙;又如“对在何地以何种方式弹奏古琴的描述”与“大乘佛教的法事仪轨”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
佛教自公元 1 世纪前后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中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然而其影响的性质与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存在较大差异。正如汤用彤所说:
汉代看佛学不过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佛学在当时所以能够流行,正因为它的性质近于道术。到了魏晋,佛学则倚傍着玄学传播流行,虽则它给玄学不少的影响,可是它在当时能够存在是靠着玄学,它只不过是玄学的附庸。汉朝的皇帝因信道术而信佛教,桓帝便是如此。晋及南朝的人则因欣赏玄学才信仰佛教。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继续流行。
总而言之,中国的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毫无疑问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内对琴艺实践和琴学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琴道》作为第一部明确指出并论述古琴文化中佛教影响的现代学术专著,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遗憾的是,前文所检视的高罗佩所使用的论据均不足以采信,要确立他提出的相关学术观点需要另辟蹊径,而这并非本文任务之所在。笔者认为,谈及古琴艺术与佛教关系,高罗佩真正的挑战在于《琴道》似乎有意淡化了宋明古琴艺术史上一度白热化的“排佛运动”及其相关影响。
宋明儒学返本“六经”以“正乐”的努力,促使士人在《乐经》失传的情况下对作为古乐图腾、圣人之器的琴尤为看重。以儒家士人对琴乐艺术空前广泛的参与为契机,宋明时期的琴学探讨也自然而然被纳入理学的概念体系中进行,同时琴乐艺术实践也日趋理学功夫化。这一方面使得琴与士人的文化共生关系在宋明理学规范的生活世界中日益巩固,另一方面也导向了对非儒家的习琴者的排斥和打击,其中最为明显的正是对僧人习琴的抵制,《太古遗音》系统的《琴不妄传》一则即为明证。相较其他琴学材料中普遍的只言片语的短论,逾五百字的《琴不妄传》更像是从儒家立场对释氏发出的檄文。文中先以白鹤子怒斥慕名前来学琴的僧人觉道的故事,申明了“琴乃中国圣人之道”,非“出于西胡夷狄之教”的佛家所宜,“恶而不授”乃“理有所忌”。针对觉道以“当唐之世丧门亦有善琴者”如琴僧怀义等为反驳,白鹤子辩驳说只因释家“不知其所忌而又不识其所耻”,妄学圣人之乐。文中进而援引理学家张载因僧人“以手扪其琴”而勃然弃琴于水的逸闻,再借助程子、朱熹、石守信以儒家立场抨击释氏废三纲五常而为“天地间一大罪人”的言论,巩固了其排佛的观点:
琴者,天地之正音,圣人之灵器,“丧门”乃夷狄之学,悖圣人之道,反天地之常,灭姓毁形之徒,曷足以事之?
其措辞之激烈或令今人错愕。释家不但被排除在琴乐合法的“道统”之外,甚至连参与琴乐实践的合法性都丧失殆尽。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明初如此激烈的拒绝佛家琴乐艺术实践的态度并未被一成不变地继承下来,我们看到晚明时的琴论中对非儒家习琴者的排斥态度已经明显缓和。比如成书于 17 世纪初的《阳春堂琴经》专门对“沙门子不宜鼓琴”作了按语,不仅举出历史上琴僧与文人交好的事实,还称赞释氏“实崇尚乎清高,品流既卓,风韵更饶”,辩护了“淄流衲子”从事琴乐实践的合法性。又如《阳春堂琴经》在梳理儒家琴乐传承的《大雅嗣音》之后有《附方外》一篇:
琴有正派,亦有旁流。明君哲相,骚人逸客,此琴之正派也。至于木容(客)毛女弄丝弦于山谷,衲子羽流杂桐响于钟磬,则又琴之傍(旁)流,亦鼓吹休明之一助也,岂可损为怪诞而不经、沙门而乱雅哉。是为志方外。
这篇短论以区分正派旁流的方式实现了对释道琴乐实践合法性的确立。笔者认为,晚明时期对非儒家文人传统的琴乐实践的缓和态度,其实正是儒家士人阶层全面确立对琴的文化专属的一种体现,是儒家获得主导地位之后的“怀柔”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儒家排斥释道的琴乐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琴乐审美标准就截然对立。恰恰相反,一如宋明新儒家思想不乏以佛老为其自我更新和完善的直接思想资源,在琴乐美学中儒家也以某种“继承—扬弃”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发扬了释道的琴乐审美旨趣。然而,笔者认为,无论是排佛抑老还是正旁分殊,在高罗佩看重的明代琴坛,琴乐艺术实践的主导地位、琴学思想和审美理念最重要的直接来源,只可能是兼容并包的儒学。
(三)再看“文人琴真相”
高罗佩洞见了琴在中国音乐传统中的超越性地位与文人传统有关:“古琴,作为独奏乐器,所演奏出的音乐与中国其他各种音乐有着很大的区别:就它的个性特征和在文人阶层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它完全是独树一帜的。”然而在《琴道》一书中,高罗佩并未成功厘清形成此种超越性地位以及古琴与文人文化共生现象的直接思想资源与历史契机。事实上,钱德明于18 世纪中国观察到的那种文人琴乐实践传统决计不是高罗佩所理解的贯穿整个两千年间的一种主导的、固化的传统。纵观历史,从先秦到唐代,古琴的审美标准千差万别,比如在唐代就还盛行迥异于文人趣味的注重旋律和情感表现性的琴乐传统。
笔者曾在《众乐之统——论古琴的“超越性”进化》一文中尝试论证,文人阶层的出现与理学价值的塑造密不可分,是政教体系逐步强化的结果,这一过程与古琴主流审美标准的转变以及古琴社会地位的提高相辅相成;理学催生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琴乐审美思想,它同时也通过对其他传统(如佛教)和阶层(如职业琴师)的琴学观点进行扬弃,确立起一种独特的权威。理学对传统心性论的进一步开掘,对儒家经典《乐记》中乐的本质和起源的重新诠释,为极具哲学性的文人琴传统之建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文人的日常琴乐实践也内化为理学的修养功夫,可以“藉琴以明心见性,以音应道”。古琴从先秦“八音”之一的乐器转变为“乐之统”,进而成为“道器”,这使古琴在最初作为乐器的价值之上,拥有了一种超越音乐本身的审美与思想价值。忽视理学的修养功夫及其独特概念,就可能导致文人的琴乐实践被误解为一种虚伪、精英的形式主义。而像“静”“声中求静”这类琴乐中的文人旨趣更会被误解为一种悖论,或者被草草标注为佛教或者道家思想。
总而言之,虽然高罗佩对道佛两家在古琴艺术中的影响的论证有不少瑕疵,但他对古琴的文人传统的批评也不乏真知灼见。高罗佩对古琴文人传统的质疑确实触及了古琴研究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揭示出古琴在独特的文人琴学观念与琴乐实践影响下的命运悖论。然而,高罗佩对复杂的琴史加以简单概括或者过度推论,以及他对宋明新儒学发展之于文人琴乐传统形成的影响的忽视,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与厘清留下了很大空间。值得指出的是,《琴道》一书虽然意义重大,却不当被视为高罗佩琴学思想的巅峰与总结,而应被看作一部受限于诸种特定历史的、个人的条件而草成的试啼之作。高罗佩真正集中研究古琴则仅在 1937 至 1941 年,其间便已完成他关于古琴的所有重要著作,如《琴道》和《嵇康及其琴赋》。此后,高罗佩的写作兴趣便转向东方图像艺术研究,再之后则痴迷于侦探小说创作。直到 1942 年从日本调往重庆之后,高罗佩才有机会与中国不同琴派的琴家广泛交游。遗憾的是,1941 年以后他再未特别针对古琴进行撰述,他在古琴的文化与美学方面更为成熟的思考或许永远地湮没在了历史之中。
三、结论:何为文人琴
在本文最后,笔者想就古琴的文人传统或简称“文人琴”进行初步探讨。
高罗佩虽然对文人琴传统有所质疑,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本人都算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琴实践者。在《琴道》文采斐然的后序中,高罗佩阐明了自己的琴乐旨趣:“藏琴非必佳,弹曲非必多,手应乎心,斯为贵矣。”似乎相较于在音乐形式上追求登峰造极(譬如使用极品的琴器、能够演奏丰富的曲目等),他更为看重的是弹琴应心的当下体验。这一观念由来已久,白居易《池上篇序》提及自己的四时琴事:“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被后世奉为文人典范的乐天居士不以琴艺的卓绝或琴曲的丰富为追求,而是将抚琴一事融入日常生活,以琴“自适”。被誉为北宋文坛宗主的欧阳修在《三琴记》中记叙自己晚年的操缦经历时,提到“琴曲不必多学……琴亦不必多藏”,而在感慨自身因年老导致“琴曲率皆废忘”,唯能作《流水》及其他数小调弄时,欧阳修点出弹琴之要义在于“自娱”“自适”。古琴美学重要典籍《溪山琴况》明确指出,“籍琴以明心见性,遇不遇,听之也,而在我足以自况”。上引这些代表性人物或作品传达的思想殊途同归,即文人以琴“自况”“自娱”“自适”,甚至通过琴来成就明心见性的修身功夫。文人的琴乐实践从来不是用以娱人的表演,有无知音见赏,听其自然而已。这样的琴乐旨趣已触及文人艺术的一般特质。
借用成果卓著的文人画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文人艺术的核心价值。陈师曾在他的名文《文人画之价值》中写道:“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朱良志提供了更富哲学性的揭示:“文人画不以美的鉴赏为目点,而以价值意义的追求为根本……文人画在形式之外追求意境的传达……文人画有一种超越形式的思考,变形似的追求为生命呈现的功夫。”二者都指出了文人画对具体绘画表现形式的超越,将其艺术性根植于意义与价值的探究与体悟。二者也以文人画为典范进一步归纳了“艺术”(更准确地讲,文人艺术)的特质。陈师曾认为:“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朱良志写道:“重要的不是艺术家留下的画迹,而是伴着这些曾经出现的画迹所包含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生命省思。艺术最值得人们记取的不是作为艺术品的物,而是它给人的生命启发。”无论是从陶写性灵还是从记录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理解文人艺术的特质,其都与琴乐中推崇“自况”“自适”“应心”的旨趣一脉相通。
事实上,中国文人艺术倾向于超越具体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实践中探索意义与价值的核心诉求并不是文化局限的。这里笔者想借助当代艺术哲学家丹托的理论,来说明文人艺术观念超越时间与文化的可理解性。丹托认为:“某物是艺术作品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种意义,即要是关于什么的;二是意义要被作品体现出来,即一般来讲,是要在物质上构成该作品的事物中体现出来。简言之,艺术品即被体现出来的意义(embodied meanings)。”基于此种理解,丹托尤其强调艺术家的宣言(statement)与对艺术作品的阐释(interpretation)在理解艺术之物与常物的区别时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艺术家富有意图的宣言及其创作的可供阐释性,令其作品的艺术地位得以可能。丹托写道:
从某物被视为艺术品的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阐释的对象。它之所以能够以艺术品的方式存在,正是因为有阐释;而当它不再被认可为艺术时,便丧失了其阐释而沦为一件普通物品……艺术存在于阐释的氛围之中,故而艺术品就是承载阐释的介质。
丹托著名的“艺术终结”命题的预设之一便是当代艺术在他看来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和阐释而得以区分于日常事物并维系其作为艺术品的存在。事实上,丹托认为,在他所观察的一些作品中,对象趋近于零而理论趋近于无限,以至于最后有的几乎只是理论:“艺术最终在一种关于自身的纯粹思想的眩晕中被蒸融了,留下的仅仅是其自身理论意识的对象。”笔者并非主张丹托的艺术理解与文人艺术观念如出一辙,或古琴在文人艺术观念影响下的命运悖论与丹托的“艺术终结”命题可以简单地相提并论,而是想强调,至少二者在对艺术性来源的申索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表现出对狭义的审“美”的超越,将艺术之为艺术的所在系于艺术形式与技法之后的价值与意义。至于中西艺术哲学家共同指向的“意义”,最终以概念化、命题化的理论或阐释呈现,还是转出为浑然饱满的生命省思与启发,可以作为一个开放问题。
作为音乐艺术,文人琴“自适”“自况”的诉求虽然导向对表演心态的拒绝,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贬损音乐的形式特质。换言之,拒绝表演不等同于拒绝实现音乐在审美和交流上的功能,关键在于弹琴作为文人生活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为己”而非“为人”之事。此外,古琴拥有“乐器”和“道器”的双重身份,文人理想的琴乐实践是“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载道而与之俱矣”,“及其妙也,则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几矣”。总之,笔者认为,从自我需要出发,致力于超越具体音乐形式而在音乐实践中涵养性情、探索更为深刻的体验与意义的旨趣,正是文人琴的本质特征。
从以上论述还可以自然地推论出,真正区分文人琴与其他琴乐实践的并非表面的审美标准或音乐风格的差异,而是“艺术意图”(借用丹托的概念)的不同。事实上,在古琴艺术中完全可以构想出一种丹托式的“难以分辨性”,即佛道儒各以不同理念基础支持的琴乐演奏,在特定的音乐风格和审美范畴的呈现上无限趋近,乃至于难以分辨——试想三家能够以不同的哲学阐释支持“简静”的琴风。同样地,以表演心态和娱人目的演奏的琴乐,与文人琴在听觉呈现上亦可“难以分辨”。简言之,文人琴并不是一种从可感知的音响形式特征中得以确立的艺术传统。
笔者在以上提出的文人琴和文人艺术的相关观点,均是从规范性角度出发的一些反思,并非从描述性意义上概括相关术语的使用情况。纵观历史,可以合理认为,许多以“文人”来标榜的琴事,并不一定属于这里所讨论的文人琴。对文人的琴乐实践从描述性意义上研究将是另一个值得展开的课题。最后,让笔者援引汪芝《西麓堂琴统》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琴之为道大矣。所以宣五音之和,养性情之正,而通神明之德也。苟非宅心冲旷,契真削墨,超然自得于林风水月之间者,其孰能与此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风格的哲学美学研究”(项目编号 :19CZX062)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见《中国艺术》2025年第3期,总第146期,注释从略)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