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无常,人生有尽。但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宇看来,要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的与无限的世界进行对话,艺术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艺术能让人保持年轻开放的生命状态,看到儿子开始申请出国交流学习,他也暗暗开始了一次“竞赛”,申请了教育部公派哈佛大学访学。在哈佛访学期间,杨振宇说,其中最快乐的两件事,一是访书淘书,除了哈佛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就是与当地的书店老板交朋友,二是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里看画读画。
无论是与哈佛大学周边的书店老板交朋友,还是看画,都是与外界交流的方式,都是为了拓展视野,提升心智。对于一些艺术实践家来说,学术应该是有专门的理论家来做的,就像一些画画的人认为自己只需要画画就好。但在杨振宇眼中,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不应把理论学术和艺术创作分开。画家不是简单的工匠,画画也不是机械的行为,画家应该像思想家一样,其实绘画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方式,即使以创作为主,也要学习。于实践家而言,要做的恰恰是从创作中找到学术的方向。就像米开朗琪罗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他一再强调,不要认为做雕塑拿锤子凿是一个体力活,他的每一凿都是思想的结果。
前些日子杨振宇在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学院的一次讲座中,结合自己在哈佛大学访学的经历谈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学者的思考
董其昌在《画诀》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揭示了艺术背后的真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彼得拉克曾将旅行的意义和创作的意义,不仅聚焦于古典文化的复兴,还强调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旅行和研究古典文献,强调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歌颂着人性的丰富性。这其实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与价值。艺术史家首先应该是一位旅行者。在讲座中,杨振宇介绍说,自称“哑行者”的美籍华裔作家蒋彝是第一位在波士顿受邀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者。在波士顿访问期间,蒋彝写出了一本《波士顿画记》,以东方文化的视角记录了他在波士顿的生活。
杨振宇对蒋彝的初识源于贡布里希的著作,蒋彝在他创作的画面上将英国的湖山风景注入了中国山水画的意蕴,这正回应了贡布里希在《木马沉思录》等著述里的追问。而贡布里希也因此以蒋彝为案例,做了关于“中国之眼”的分析。杨振宇在去哈佛访学前,就曾购买了一本原版的《波士顿画记》。缘分匪浅,因为这本书的原有主人就生活居住在波士顿。也正是这本原版《波士顿画记》,给了杨振宇启发和深度思考。
杨振宇说,在原版《波士顿画记》一书的封面插图上有一棵松树。这幅画是蒋彝取景于哈佛园的画作。松树之苍劲之生命力,往往存活几十年几百年。但当杨振宇到哈佛大学的那棵松树现场时并没有发现那棵松树。由此,杨振宇的学术思考开始了——对杨振宇来说,蒋彝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贡布里希的书中,贡布里希当时在书中用了蒋彝的一幅画,是蒋彝描绘的英国温德米尔湖,但蒋彝画的温德米尔湖一看却是中国山水画的感觉,也就是说,他把英国的湖画出了西湖的感觉。而贡布里希在《木马沉思录》和《艺术与错觉》中探讨的问题便是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风格。比如作为中国人的蒋彝跑到温德米尔湖后,把英国的湖泊画成了中国的山水画,而英国人在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却画不出中国山水画的味道。贡布里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山水固有的图式,才是蒋彝创作的起点。
基于这样的认知,杨振宇说,波士顿也有很多松树,但他到了哈佛园实地比较蒋彝的画作取景地前,却没有看到这棵松树,这让他不由得产生疑问:蒋彝为什么要在这里画上一棵松树?杨振宇说自己最初给出的自然而然的解释是,虽然在波士顿松树是很常见的树,但显然蒋彝是想把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气节带入到哈佛校园的画作中,可谓有意而为之。而且,蒋彝身上肯定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节,在画面中加入一棵松树,蕴含了他内心的精神取向,同时也反映了他身上刻着的中国文化基因。
但后来,杨振宇发现他的这种联想出现了差错,事实证明他想多了。杨振宇说,他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认识的朋友带给他了一些线索——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校园里的树木曾发生了虫灾,这些害虫杀死了很多树,而那棵被蒋彝描绘过的松树就在这个时候死掉的。虫灾之后,哈佛校园开始重建,这种重建就像我们研究古画和历史一样,有些地方被我们补了上去,有些地方被我们修剪了下来。
所以,在联想背后,广泛与深入的了解也是不可少的。杨振宇的这番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的思考与反省。即在阅读中大胆联想、对比、思考,又要在广泛阅读和交流中,将联想的结果变得更加准确、有效。就像作为艺术实践者的我们,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去进行临摹、读画,让自己在程式化的思考中得到突破——我们在看画、思考的时候不免会带着一些原有的认知去进行,但广泛与深入的认知可以让我们的“固化模式”发生思想的火花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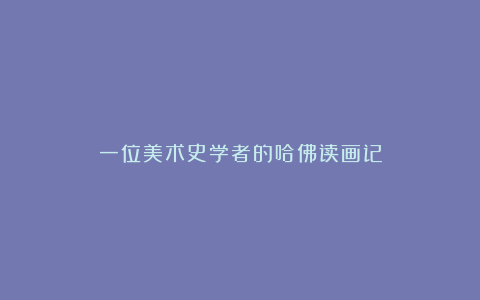
杨振宇说,有些东西,由于了解不够,认知有限,导致误解与一些错误的猜测,人生有时候也是如此。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内心,不要让自己的思想有限制。
在哈佛大学的访学经历让杨振宇从日常的琐碎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一种相对纯粹之中。这种相对的纯粹,呼应着杨振宇曾从范宽《溪山行旅图》中读到的顿悟——人一定要学会安静、学会宁静、学会静坐,你才会慢慢地积蓄能量,所有的流水都源于你的群峰寂静之中。
读画记
如何安静自处,如何面对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终身修行。就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独处,也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去美术馆中静静读画。艺术,如同康定斯基所讲的,源于人内心的召唤。杨振宇在形容他在哈佛艺术博物馆中的读画经历时,他用了“奢侈”一词来形容。他觉得在当时,每天想去读画的时候就可以去静观,看到那些西方美术史中的大师原作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在这一年的读画记忆里,他觉得博物馆里的作品一直在那静静地等候着……而他,想到了,就去看看。
对于一个从事艺术领域的人来说,学画、画画、读画,学术与艺术总是交织相依的。杨振宇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就惊喜地见到了两幅尼古拉斯·普桑的精彩作品:《圣家族》和《小酒神巴克斯托付给宁芙们》。这两幅画,杨振宇觉得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礼遇。
在他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遇到普桑两幅原作之前,他通过对潘诺夫斯基和T.J.克拉克的阅读,对普桑的艺术作品有了长期的研读。如杨振宇所说,“不同的环境下,跟一个人打交道,我们会更丰富的理解这个人。看画也是这样,需要不断的观看。T.J.克拉克和潘诺夫斯基让我对普桑有了一定的研究,到了哈佛艺术博物馆,在它楼上的一个厅,里面有两幅普桑的画,看到画后的那种感觉是难以言表的。仿佛就是因为前面的准备,让我在这里与普桑的两幅画相遇。”
杨振宇说,和普桑的这次哈佛相遇与相聚,让他断断续续地写下了几万字的“读画日记”。有很多“观看”,只有在面对原作的时候,才会偶然生发出来。
生活的流动与无边
博物馆之于美术馆,都承担着社会美育的意义,但博物馆于美术馆而言,它显得更为沉静。因为博物馆中的很多藏品是更为固定的,但美术馆中的作品却更多是“流动的”,艺术品让整个世界都流通了起来,人们因为艺术品的陈列去往各地。杨振宇说:“全世界的时间、空间的间隙和隔离是人为的,其实大家都在流通。”在流通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交往、认识的人乃至整个人生,都会放在一起去促使我们思考。
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人亦拥有不同的经历与命运,就像杨振宇所说,有的人身上天生就有一种命运感,即使命运趴下,有的人承受得了,有的人就崩掉了。世界也是这样。有些人面对灾难的时候,泰然自若,能够面对,也能处理。有的人碰到一点点小事情就手忙脚乱,慌张的不行。
在杨振宇看来,学术不要太狭隘的理解,知道的越多,与创作结合,会有助于思考的深入。不应该直接去问“美术是什么”这样的本质论问题,应该想到的是研究学科、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就在创作中随时都可能遇到,不要忽视。在创作当中,会冒出、面对很多具体的细节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学术,然后去思考它,在自己的角度去把握它,就会有收获。再去看画、再去读书,再慢慢地回到人生。杨振宇说:“无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年纪大的时候,始终保持住这样的状态,我相信这个人生一定会踏踏实实,会非常的美好,”
杨振宇在2023年到哈佛大学时,哈佛大学博物馆出台了访客到访无需证件证明的新规,只需要登记,这个登记也只是为了统计他们的来访人数。这是一个博物馆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让我想到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学院的定位——“无墙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