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南阳府,高家大院。
年仅十岁的云飞跪在冰冷的花厅石板上,小脸红肿,泪痕未干。
“没娘教的小畜生!连个茶都端不稳,想烫死我吗?”继母路燕柳眉倒竖,艳丽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手中的藤条毫不留情地抽在云飞单薄的背上。
云飞咬紧嘴唇,不敢哭出声。自从三年前爹娶了这个女人进门,他的日子就从云端坠入地狱。爹老了,管不动了,何况路燕去年还生了个弟弟,爹的心思更不在他身上了。
病榻上的高员外剧烈地咳嗽着,脸色蜡黄。路燕端着药碗进来,瞬间换上一副温婉面容。
“老爷,该吃药了。”她声音柔得能滴出水,舀起一勺药,轻轻吹凉,送到高员外嘴边。眼角余光却瞥向窗外正在罚跪的云飞,一丝狠毒一闪而过。
这高家万贯家财,岂能分给那前妻留下的野种半分?老爷眼看就不行了,必须尽快动手!她心中冷笑,一条毒计已然成形。
“云飞,”这日,路燕罕见地和颜悦色,“你爹的病越发重了,城里仁济堂的刘大夫医术好,你去给爹抓几副药回来,说不定爹吃了就好了。”她递过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和一张药方,“路途远,辛苦我儿了。”
云飞看着继母“慈爱”的笑容,有些恍惚。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她这样对自己笑了。一股混合着委屈和渴望的情绪涌上心头,他用力点头:“娘放心,我这就去!”
三十里路,云飞天不亮就出发,踩着露水,顶着烈日,心里只盼着爹的药能有效。
第二天傍晚,云飞终于赶回了家。他顾不上喝口水,就按照路燕的吩咐,在小厨房里小心翼翼地煎起药来。
路燕走进厨房,脸上堆满欣慰的笑:“哎呀,我的云飞真是长大了,知道心疼爹了。来,让娘看看药煎得怎么样了。”她接过云飞手中的蒲扇,“你去看看爹醒了没,这里娘来看着。”
云飞不疑有他,乖巧地去了父亲房间。
片刻后,路燕端着那碗漆黑的药汁,坐在高员外床前,一勺一勺,极其耐心地喂他服下。
“老……老爷?”药碗刚空,高员外突然双目圆瞪,身体剧烈抽搐,七窍之中流出黑血!他手指颤抖地指向路燕,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旋即头一歪,再无气息!
“啊——!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路燕手中的药碗“哐当”摔得粉碎,她发出凄厉至极的尖叫,扑到床前,随即猛地回头,指着闻声赶来的云飞,面目狰狞如恶鬼:
“是你!云飞!你这狼心狗肺的小畜生!你竟然在药里下毒!毒死了你亲爹啊!!你连畜生都不如啊!!”她哭天抢地,声音传遍了整个高府。
云飞如遭雷击,呆立当场,看着床上死不瞑目的父亲,又看看状若疯魔的继母,大脑一片空白。
“不……不是我……娘……不是我……”他徒劳地辩解着,声音微弱。
“人赃并获,还敢狡辩!跟我去见官!”路燕力大无穷,一把揪住瘦弱的云飞,连拖带拽,直奔县衙而去。
“青天大老爷!您要为民妇做主啊——!”
公堂之上,路燕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她将早已编排好的故事声情并茂地讲述出来——云飞如何不满父亲管教,如何主动去买药、煎药,高员外服药后如何七窍流血暴毙……
“大人!药是他买的,是他煎的,也是他端来的!不是他还能有谁?求大人将这弑父逆子千刀万剐,以慰我夫君在天之灵啊!”
县令重重一拍惊堂木,目光锐利如刀,射向浑身发抖、脸色惨白的云飞:“高云飞!你还有何话说?”
云飞吓得魂飞魄散,只会磕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大人明鉴!小人冤枉!小人怎会害我爹爹?是娘……是娘让我去买药,药煎好后也是娘端去给爹喝的……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
“哼!巧言令色!”县令冷哼,“药经你手,如今人死了,你一句’不知道’就想推脱干净?天下岂有这等好事!来人,先将这弑父嫌犯高云飞收押入监!待本官细细查证,再行判决!”
“威武——”衙役们水火棍敲击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上前就要拖走云飞。
“大人!证据确凿,为何不立刻判他死罪?!我夫君死得冤啊!”路燕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急切与不甘。
县令目光深邃地看了她一眼,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人命关天,岂能草率?本官自有主张。你先回去,静候传讯。”
路燕无奈,只得叩首,在丫鬟的搀扶下离去。转身的刹那,无人看见她嘴角那抹转瞬即逝的得意。
后堂书房内,烛火摇曳。
县令眉头紧锁,反复推敲着案卷。师爷在一旁低声道:“大人,此案表面看证据链完整,那高云飞确是最大嫌疑人。只是……”
“只是什么?”县令抬眼。
“只是不合常理。”师爷捋着胡须,“那高云飞年仅十岁,与高员外乃是亲生父子,有何深仇大恨要弑父?即便父子不和,高员外死后,家产他也未必能独占,上有强势继母,下有年幼异母弟……此举于他,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错!”县令眼中精光一闪,“反观那路燕,年轻貌美,嫁与垂暮老者,如今夫死,若再除去前妻之子,那万贯家财……而且,她今日在堂上,看似悲痛,眼神却无多少哀戚,反而急于置继子于死地,实在可疑!”
他沉吟片刻,一个大胆的计划浮上心头。
“来人!”
一名心腹衙役应声而入。
“你去查查,高员外死后,那路燕在家中行为可有异常?另外……”县令压低声音,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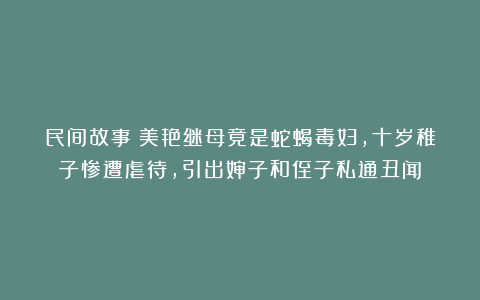
衙役领命而去。
不久,回报来了:“大人,那路燕回家后,并未设置灵堂守丧,反而……反而在房中梳妆打扮,神色间颇有……颇有欢愉之意!”
“果然如此!”县令一拍桌案,“本官心中已有计较!”
是夜,月黑风高。
路燕正对镜贴花黄,欣赏着自己依旧娇艳的容颜,盘算着等高云飞被处斩,家产到手后,就和情夫双宿双飞的美好未来。
忽然,一阵阴风袭来,吹得烛火明灭不定。
“呜……呜……”
似有似无的哭泣声在窗外响起。
“谁?”路燕汗毛倒竖。
下一刻,一个披头散发、面色青白、七窍沾着“血痕”的鬼影,飘飘悠悠地穿窗而入!那容貌,赫然正是死去的高员外!
“啊——鬼啊!”路燕吓得魂飞魄散,瘫软在地,手脚并用地向后爬。
“贱……人…………”鬼影发出幽怨空洞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我……死得……好惨啊……阎君说……我死因不明……无法……上册……只能做……孤魂野鬼……”
“夫……夫君……”路燕牙齿打颤,“是……是云飞……是那小畜生害了你……我已经把他送进大牢了……马上就砍头……给你报仇……”
“放……屁……!”鬼影猛地逼近,阴气扑面,“阎君……明察……说非他所为……快说……我究竟……吃了何物……死的……否则……我夜夜……缠着你……永不超生……”
极致的恐惧摧毁了路燕的心理防线,面对“死而复生”的丈夫鬼魂,她心智崩溃,脱口而出:“是砒霜!是砒霜!夫君饶命啊!”
“砒霜……从何……而来……”
“是……是你侄子高陈给的!是他给我的!是他勾引我,说只要毒死你,嫁祸给云飞,家产就是我们的,我们就能做长久夫妻了!都是我鬼迷心窍!夫君饶了我吧!”路燕涕泪横流,磕头如捣蒜,将她和奸夫高陈的阴谋全盘托出。
鬼影静静地“听”完,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身形渐渐淡化,消失在空气中。
路燕如同烂泥般瘫在地上,浑身被冷汗浸透,久久无法动弹。
日次,县衙再次升堂。
路燕被传唤到来,她强作镇定,一上堂便问:“大人,那弑父逆子何时处斩?”
县令面无表情,目光如冰刀般刮过她的脸:“路氏,你且抬头,看看本官是谁?”
路燕疑惑抬头,对上县令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忽然,她浑身剧震!这双眼睛……这眼神……和昨晚的“鬼魂”何其相似?!
“你……你……”她手指颤抖地指着县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不错!昨夜假扮高员外鬼魂的,正是本官!”县令声如洪钟,惊堂木一拍,“路氏!你与侄子高陈通奸,合谋用砒霜毒杀亲夫,嫁祸继子,还不从实招来!”
“大……大人!民妇冤枉!那……那是鬼话,当不得真啊!”路燕还想狡辩。
“冤枉?”县令冷笑,“你已亲口承认砒霜乃高陈所给,并供出杀人嫁祸、意图霸占家产之全部阴谋!衙役记录在此,容不得你抵赖!来人,传高陈!”
高陈被押上堂,起初还矢口否认,但当县令将路燕的供词摔在他面前,并厉声呵斥其与婶母通奸、谋害亲叔之罪时,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再也无法狡辩,急忙磕头认罪。
铁证如山,两人当堂画押认罪。
公堂内外,一片哗然!旁听的百姓、衙役无不震惊骇然!
“案犯路氏,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又起歹心,谋杀亲夫,嫁祸继子,其行卑劣,其心可诛!依《宋刑统》,判处斩立决!秋后处刑!”
“案犯高陈,罔顾人伦,与婶母通奸,合谋毒杀亲叔,罪大恶极!判处阉刑,刑后充军三千里,永世为奴!”
“高云飞蒙冤受屈,当堂释放!高家产业,暂由族中公正长老代管,待其成年后交还!”
判决一下,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青天大老爷啊!”
“杀得好!这等毒妇,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云飞跪在堂下,泪流满面,朝着县令重重磕了三个响头。他终于洗清了冤屈,可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却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