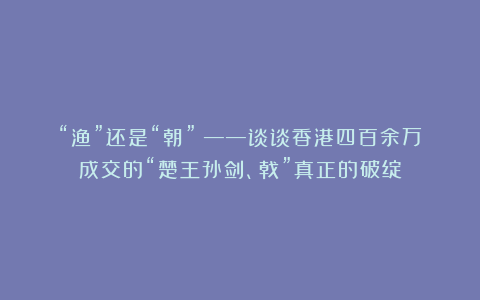|
原创 马鹤逸 信古斋 2025年11月2日 15:30 湖北
上个月月初,香港上拍了一组所谓战国早期的“王孙渔”错金铭文剑、戟,对文物拍卖市场比较关注的读者应该都看到过这套东西的照片。
这组所谓战国早期的错金铭文兵器,两件合在一起成交价刚过四百万,自然远远低于同类器物的市场价格。
两件兵器亮相预展后,很多行内的朋友都对其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点主要在于器物的形制、皮壳,基本都认为不真。
通过形制、皮壳判断真伪,主观性比较强,很难拿出一个行内外公认的标准,所以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但这两件东西的铭文内容里还有一个硬伤,是绝大多数讨论没有涉及到的。
这期文章,就借湖北、河南馆藏的三件所谓“王孙渔”制作的标准器,来聊一聊“王孙渔”到底是楚国的哪位王孙?香港拍卖二器最终判断为伪器的关键证据是什么?
考古发现时间最早的一套“王孙渔”器,出土于1958年湖北江陵县长湖南岸一座楚国墓葬中。墓葬是当地村民疏通河沟时意外发现的,由于时代较早,未经科学考古发掘,仅将墓中的器物取出,共计有铜戈5件、铜剑2件、箭镞22件、铜矛2件与一些车马杂器、玉器。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初步将墓葬的时代定为战国。
1959年,为了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湖北省调拨大批49年以后出土文物前往北京,其中就有此墓出土的一把铜戈。经过国博工作人员的鉴定与清理,在戈的援部与胡部发现六字错金铭文,石志廉先生考订为“楚王孙渔之用”,认为可能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楚国司马子鱼。
实际上,调拨至国博的铜戈只是这套铜戟的主戈,另一把无内的副戈还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目前在“楚国八百年”展馆中进行展出:
由于展厅的打光极暗,戈援上部的“楚王孙”三字可以看见,但戈胡部基本就是黑糊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来看看《铭图》中著录的铭文摹本:
资料来源: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卷31第451、454页。
戈铭这六个字中,“楚王孙”、“之用”这五个字是非常好认、没有疑问的。铭文第四个字,从字形上来看由四个部分组成:左上角为“鱼”,右上角过去一般认为是“舟”,左下角为“水”,右下角为“又”。石志廉认为此字是“渔”字之繁体,象人乘于舟中、以手捕鱼之形。这一解释就当时的认识来说非常合理,过去几十年间,学界对此基本无异议,仅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中将此字释为“鱼舟”,认为“楚王孙’鱼舟’疑即楚公孙朝”,惜只寥寥数语,并无深入论述。
2000年,荆门左冢战国楚墓(编号M3)也出土了一件错金的铭文铜矛,其铭与上引“王孙渔”铜戟基本一致,可以断定是同一人所作器:
白描图资料来源: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著,《荆门左冢楚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此矛铭文与戟铭完全一致,即“楚王孙渔之用”(按石志廉释文)。荆门左冢楚墓的时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按照墓葬规格与人骨检测的结论,左冢的三座墓葬属于一家子,M1的墓主人是楚国的一位大夫,M2葬其子,M3葬其妻。
左冢M3虽然是一位女性墓葬,但这位大夫之妻身佩铜剑下葬,墓中出土有矛、戈、箭镞等兵器,看来也是一位尚武之人。
由于戟与矛都出土于战国时代墓葬,因此左冢楚墓报告的编写者认为“王孙渔”可能是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而非此前研究中所推测的春秋晚期楚国司马子鱼或公孙朝。
2005年5月,河南上蔡郭庄发现两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楚墓。墓葬的形制非常奇特,其中位于南侧的主墓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防盗措施,在墓室上方铺设了近11米厚的纯净流沙层,流沙中又埋放了一千多块大石头,盗墓者一旦挖到流沙层,细沙就会带着石头流进盗洞,将盗墓者淹没。
在流沙层下、主棺的上方,墓主人还布设了两个假棺,并在假棺里放置了少量随葬品,希望给盗墓者一种“已经到达墓底”的假象。
遗憾的是,虽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盗措施,在从古至今历代盗墓者的努力下,此墓还是成功被盗,墓内发现有12个以上的盗洞;幸运的是,流沙层毕竟对盗墓者搬运物品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椁室内还有大约一半的随葬品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那些大型的铜礼器。
由于此墓的发掘报告一直未出(发掘至今已经足有20年,对比上面荆门左冢6年就出大报告,专业程度真可谓是云泥之别),墓葬出土的文物信息散见于各种出版物及研究论文中,只能窥其一角。这些文物中,最早披露资料、目前在博物馆中与观众见面的,要数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件硕大铜鼎。
此鼎从样式上来看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有盖三足附耳鼎,但尺寸特别硕大,通高88cm,口径80cm,耳距103cm,应该是目前考古所见春秋时期第二大的铜鼎(略小于金胜村赵卿大墓所出铜鼎),属于当时礼器中等级最高的“牛镬”,也就是用来煮牛的大鼎。
器盖、器身各铸造有两篇铭文,铭辞基本相同,唯有铸器者的名字不同。器盖铭文公布较早,在2013年出版的《鼎盛中华》一书中附有器盖铭文照片(但书中未标明是器盖铭文);器身铭文则未见于公开出版物,以至于有些学者撰写相关文章时未注意到器身与器盖铭文不同。所幸,河南博物院在介绍此鼎的展牌上附录的拓片恰巧用了器身部分,因此这里才能够为大家展示此鼎铭文的全璧。
此外这里还要批评一句,《鼎盛中华》书中附录了“竞之朝”铭文照片,但释文标注为“竞之宁”;河南博物院展牌上标注此鼎的释文为“竞之朝”,但附录的拓片却是“竞之宁”,非常容易误导认真看书、看展的读者和观众,很有必要予以修改。
资料来源:河南博物院编,《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122页。
两种铭文基本一致,都是三行十九字(含合文二),唯有中间一行的第二个字不同。其铭(宽释)分别为:
唯王八月丁丑,竞之“舟止鱼”自作䵼彝列尝,用共盟祀。
鼎铭的大意很好理解:某位楚王在位的八月丁丑日,两位楚国的“竞氏”贵族作了一套大铜鼎,以供盟会的祭祀仪式使用。
“竞之某”的文例,在此前文章“秦王卑命——楚钟疑云”中已经详细讲过,即战国时楚国王族三大支族之一的景氏,以楚平王的谥号“景平”首字为氏名。“景平”在楚国文字中写为“竞平”,故出土文献中的景氏族人均写为“竞之某”或“竞某”,其全称为“竞平王之某”,已见于上引文章的介绍。
根据武汉大学收藏战国“竞(景)快”祷祝简的信息,景氏家族的族源应出自楚平王的庶子、楚国令尹子西。
我们先来看看器盖铭文自称的器主人,竞之“舟止鱼”的“舟止鱼”字。
很明显,此字与上面戟、矛器主人所谓的“渔”字是同一字,均从鱼、从舟,兵器铭下面所从的“氵”在鼎铭中没有,兵器铭所从之“又”在鼎铭中写作“止”,当是传写之讹。
我们再来看看同墓出土、目前已经披露材料的其他几件有铭铜器:7件鬲、2件方壶、1件簠、1把错金铜戈。其中,方壶铭文是鬲铭的减省版本,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此墓目前披露的铜器铭文还有3种。
资料来源: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10卷河南下》,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406页。
资料来源: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10卷河南下》,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357页。
资料来源: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卷6第489页。
铭文四十一字(含合文一):正月尽期吉辰,不忒竞孙“㫃走舟”也,追孝缵尝,恭持明德,昭事辟王,钦哉不服,永保之用享,子孙是则。
可以看出,以上这三种铭文的作器者自称为“竞孙”、“楚王孙”,显然与上面介绍的鼎盖、戟、矛为同一人所作。作器者之名写法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点:在所有写法中都有“舟”这个组成部分,这说明此字从“舟”字得声,声符表现这个人名的读音,是必须要有的。
当然,这个声符释读为“舟”是不是正确,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李零先生就读此字为“川”,大部分学者都用该字的图像代替释文。文章这里不方便插图,就直接用早期释文“舟”来指代这个字了。
那么,这些所有从“舟”得声的字,究竟应该解释为哪个字呢?上面已经提到,何琳仪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提出,“楚王孙’鱼舟’疑即楚公孙朝,见《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是在后来所有器物都没有出土以前、仅凭铜戟铭文提出的观点,真可谓是远见卓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朝,旦也。从倝,舟声。”在小篆字形里,“朝”字就是从“舟”而得声的。在出土的战国时期铜戈上,也见有从“舟”的“朝”字:
资料来源: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卷32第103页。
此戈是战国早期的魏国兵器,铭文曰:“朝诃右库,工师毁”,“朝诃”即“朝歌”,纣王所都,西周至春秋时为卫国都城,战国时属魏邑。铭文中的“朝”字非常清楚,与上述器组的作器者铭文同从“舟”声。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陈,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君盍舍焉?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
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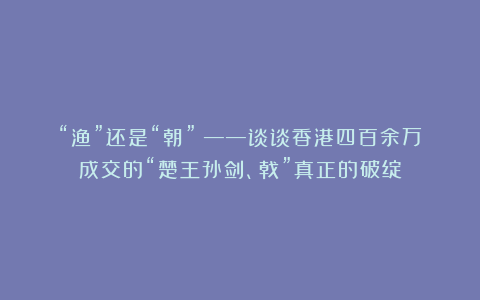
鲁哀公十七年,楚王打算讨伐此前曾经入侵楚国的陈国,向太师子谷与叶公诸梁询问将帅人选。叶公诸梁极力推荐让前令尹子西之子担任统帅,说“令尹子西生前与陈国有矛盾,如果上天要灭亡陈国,必须派子西的儿子前去顺应天命”。经过占卜后,现任武城尹、子西之子公孙朝是吉利的,于是就任命他作为伐陈的统帅,在当年的秋天灭掉了陈国。
前面说到,景氏出自楚景平王之子令尹子西,如果将上述器组的主人对应到子西之子公孙朝,那么“楚王孙”、“竞(景)孙”、“竞之朝”等称呼都完美得到了解释,上蔡郭庄大墓的时代也与公孙朝活动的时代非常契合。
此外,如果将“竞之朝”对应到楚国的公孙朝,那么“竞之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据《左传》可知,令尹子西另有一子名为“宁”,字子国,在白公之乱后继任为楚国的令尹。《左传·哀公十六年》记白公之乱后:
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
杜预注“宁”曰:“子西之子子国也”。
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
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
则子国在担任令尹之前曾经担任楚国的右司马,后来被封为析君。本年《传》文明确称子国为“公孙宁”,可见“宁”确实是子国之名,其人为子西之子、楚景平王之孙,因此在鼎铭中自称为“竞(景)之宁”。
至于为什么一件铜鼎要由公孙朝、公孙宁兄弟两人分铸器、盖?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两天,笔者恰好在网上刷到了严志斌先生的一篇文章:故宫院刊 | 严志斌:商周青铜器同器异铭现象探讨,就提到了商周青铜器盖、器铭文不同的现象。文中虽然没有讲到本文中的“竞之朝、竞之宁铜鼎”,但罗列了不少存在类似现象的器物,认为可能存在“兄弟合伙制器”这种可能。
笔者认为“竞之朝、竞之宁铜鼎”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作之器。在《左传》涉及的年份范围内,公孙宁为楚国令尹,又受封为析君,财力比较雄厚,便铸造了大鼎的器身;公孙朝为武城尹,官职微于公孙宁,就出资铸造了相对便宜的鼎盖。大鼎铸成后,用作景氏与其他族氏进行盟祀的场合。
大概在《左传》涉及的年份范围以后,或许是公孙宁先去世,或者公孙朝的地位最终超过了公孙宁(郭庄大墓距离上蔡故城仅3公里,公孙朝很可能最终受封为楚之蔡公),此鼎最终归公孙朝所有,与朝的其他器物一起下葬于朝之墓。
当然,事实究竟如何,还要等待上蔡郭庄大墓的考古报告面世那一天才能知道了。不过,所谓“王孙渔戈、戟”中的“渔”字属于误读,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香港拍卖的两件所谓“王孙渔剑、戟”,剑的铭文是从“楚王酓璋戈”、“楚王孙朝戟”与“越王州句剑”三件器物的铭文中截取拼凑出来的;尤其是“王、自、作、用、剑”五字,几乎完全与越王州句剑一致。
然而,作伪者没想到的是,虽然吴、越、楚三国都喜欢在兵器上使用鸟虫篆书,但三国文字的“鸟虫化”手法是不一样的。越国的鸟虫篆,偏向于在字的结构以外添加鸟头、鸟爪等与文字无关的形象;而吴、楚两国的鸟虫篆,偏向于把文字本身写得繁复曲折,把文字的笔画化作鸟的形体。笔者在去年的一组文章中,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作伪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把取自两件楚国兵器的“楚、孙、朝”三个字与取自越国兵器的“王、自、作、用、剑”五个字拼在一起,虽然乍一看风格很相似,但前三个出自楚国兵器的文字均无多出来的鸟形装饰,后五个出自越国兵器的文字全部有多出来的鸟形装饰,这是这套所谓“王孙渔剑、戟”露出的第一个马脚。
第二个马脚,就是铜戟铭文的字体与铭文中的称谓问题。首先,铭文的字体取材于楚国简牍文字,这是当时楚国的毛笔墨书书法,与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根本搭不上关系;而作伪者又不明白旧释“渔”的字实际上应该读为“朝”,因此在拼凑文字时从简帛文字编里找出来一个释读为“鱼”的字做了上去,反而把这个文字核心的声符——“舟”给省去了。
其他关于皮壳、形制的质疑,都可以用别的理由来糊混过去;唯有铭文中这个字的写法是硬伤,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理由来解释的。
这也就可以断定,香港拍卖的这两件所谓“王孙渔剑、戟”,必然是不到代的伪作;糊弄一下外行还可以,遇见稍微懂得一点古文字知识的人,马脚很快就露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