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店镇茶马古道的弦歌》
作者:郭闯
这路,瘦了。瘦成一道脊梁,一道疤痕,嶙峋的骨殖从黄土里凸出来,任千百年来的风与脚印磨洗。石阶是凝固的乐谱,深深浅浅的蹄窝,是乐谱上沉默的音符。我蹲下身,将手掌贴在一块被磨出温润光泽的青石上,仿佛触到的不再是冰凉,而是一段被太阳焙干了的、疲惫的喘息。那一定是某个歇脚的午后,一匹老马沉重的吐纳;或是某个星夜兼程的汉子,靴底带来的远方的潮湿。寂静,在此刻是震耳欲聋的。它不再是声音的缺席,而是所有逝去声响的集合。那商旅的驼铃、驮马的响鼻、脚夫的山歌、不同口音的交谈……它们被时间这口巨大的陶瓮密封起来,窖藏在这蜿蜒的山谷里。我站着,便成了一个软木塞,稍一松动,那万斛的喧嚣仿佛就要决堤而出。
风,是唯一的说书人。它掠过崖壁上倔强的酸枣树,穿过荒草丛中半坍的石屋,便带来了故事的碎片。我仿佛看见,一个披着旧棉袄的老人,袖着手,就坐在那块界石旁,他的脸像身旁的山岩一样沟壑纵横。他或许会用浓重的乡音告诉你,哪一块石头是“歇人坎”,哪一道弯曾摔死过最烈的骡子。他的父辈,他父辈的父辈,便是这古道上的藤蔓,生生不息。他们的生命,与这条路的脉搏一同跳动:路荣则家旺,路衰则村寂。如今,他守着这份寂静,像守着祖传的、再无客来的老店。那被风雨剥蚀的窗棂,空空洞地张望着,望成一幅版画,印着流云,也印着无言的时光。
然而,弦歌并未断绝。它只是换了一种声部,在另一种生命里延续。转过一个山坳,一片炫目的红,猛地撞入眼帘。是山楂。路旁坡上,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摊着那饱满的红果,像一串串褪了色的铃铛,却敲击出更浓烈、更扎实的声响。那不再是虚幻的追忆,而是滚烫的、甜酸的生活本身。古道上不再有驮运盐茶的马帮,却有了载着游客与山货的摩托车,“突突”地开过去,留下一缕青烟,和着院子里飘出的炒山楂的焦香。那香气,醇厚而蛮横,一下子就钻进了你的五脏六腑,告诉你:生息,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坚韧的哲学。
同行的当地朋友,一位沉默如山石的汉子,指着远处山腰间一道极细的、几乎被草木吞没的痕迹,说:“瞧,那才是真正的老路,更险,也更直。”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心里蓦地一惊。我们脚下这条被称作“古道”的、已觉坎坷的路,竟也是后世拓宽修缮的了。那真正的、最初的足迹,早已归还给荒草与峭壁,像一位真正的隐士,将自己藏得更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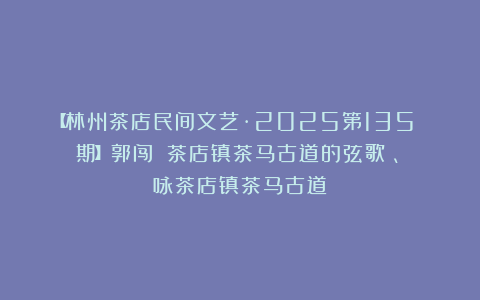
原来,我们所凭吊的,不过是历史的影子;我们所感怀的艰辛,也不过是后人眼中的一层滤镜。那最初的开拓者,他们所经历的,是比这影子更浓重千百倍的黑暗,是比这滤镜更尖锐千百倍的锋刃。
暮色,说来就来,像一滴巨大的、温润的墨汁,滴在宣纸似的群山上,迅速晕染开来。我们该离开了。回望茶店镇,灯火已次第亮起,暖融融的,缀在大山的黑袍上。那光,不再诉说远行的凄苦,而是安于当下的温暖。古道的故事,终究被这万家灯火收纳、消化,成了梦的养分。
下山的路,很轻。那万斛的喧嚣,不知何时已沉淀下去,化作心底一片澄明的静寂。我仿佛听见,那弦歌仍在,只是不再由风与驼铃演奏,而是由这沉默的山、这不息的生活、这灯火的温度,共同吟唱的一首更恢弘、也更安详的长诗。
《咏茶店镇茶马古道》
作者:郭闯
太行深处古道长,曾伴驼铃送晓光。
马踏青石留旧迹,茶飘远域韵悠长。
今朝焕彩新街市,昔日遗风古栈房。
最是铃声传雅韵,生机勃发续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