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智中,佤族,1967年生,沧源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临沧市作协副主席,云南省“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委联系专家。文学作品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新人新作奖、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边疆文学奖”“滇西文学奖”;教育成果获云南省高等教育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完成云南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一项。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佤族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口述史《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口述实录》(合著),参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佤族卷》《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佤族卷》等。
嘎多村落记忆
一
这是一个叫作嘎多的佤族村落故事。我将它称之为远古部落,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离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太远,而与那些早已随风而逝的历史传说却是如此之近。
嘎多是沧源佤族自治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所有的历史事件均与它无缘,加之地处中缅边境最为偏远的单甲乡,这似乎注定了无论是在佤族文化旅游的热潮中还是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它都只能以一种沉默的姿势远离人们的视野,成为视野边缘中被遗忘的村落。
图片来源:今日临沧
2005年的冬季,当我背着相机、拿着笔开始居无定所的佤山部落探秘之旅时,嘎多进入了我的视野。尽管当时的佤族文化旅游热潮已经奔涌而至,单甲乡却因为地处沧源县经济、文化的死角而远离了这种喧嚣,加之嘎多又是离乡政府驻地最偏远的村,更是与这种喧嚣无缘。
其实,只要车方便,到嘎多并不是一件难事。从沧源县城到嘎多总里程只不过80多公里路,但每日一班的客车只到达单甲乡政府所在地,这让到嘎多村余下的近20公里显得特别遥远。在我们乘坐的吉普车从乡政府前往嘎多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没有遇到包括拖拉机在内的任何机动车。乡政府的领导告诉我们,这条公路是去年才开通的,雨季车辆行走还不是太方便。一路上,我们果然看到很多劈山造路的痕迹,公路像是原始森林中一条撕裂的伤口,嘎多就处于这个伤口的尽头。
从村的外观和族人的眼光中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少有外人涉足的村落。大山以北与本乡的单甲、安也两个清一色的行政村相邻,大山以南则与缅甸北部的阿佤山中心地带佤邦勐冒县昆马区司岗惹乡、公古乡和绍帕区永丁乡等相邻。嘎多村落又有上寨、下寨之分,总共只有100多户人家。尽管山外的村寨在现代文明的感召下,已纷纷将草房改为了石棉瓦顶房甚至是汉式砖混平顶房,但这里大多数人家仍然延续着佤族千百年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加栅栏的居住方式,整个村落呈现出远离现实的古朴和神秘。
图片来源:今日临沧
就是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古朴和充斥着神奇的静谧中,我们与村里80余岁高龄的老人肖安姆块相遇。肖安姆块老人向我们讲述了我们到达嘎多后听到的第一个关于猎人头祭谷的故事。
二
肖安姆块老人讲,丈夫被猎人头的前几天,她梦见天上飘着雨,落在她家竹楼上的时候变成了血,像冰雹一样一颗一颗地结在一起。她看见,丈夫和三个被猎人头的同寨人站在一座独木桥上对着她笑,洪水突然倒流把丈夫和木桥给卷走了。接连两天,她一直做着同样的梦。寨子的魔巴告诉她,她的丈夫不会死在家里,会死在野外,就是杀再多的鸡、杀再多的猪、看再多的卦都改变不了,这是他的命。
过了几天,丈夫去卖篾笆回家的路上,在途中的一座独木桥边被猎去了人头。流淌一地的血就像梦中她家竹楼上的血一样凝结成块。面对一地的血,肖安姆块老人没有哭出声来,只是木然地坐在河边望着河里滚滚东去的水,想着魔巴跟她讲过的话。尽管她不知道,没有男人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但她仍不能哭泣,她不能让自身的晦气随着哭声传递给整个部落。她只能看着,她和丈夫住过的草房在寨主和魔巴的带领下被一把大火给烧了,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一栋全新的草房又在原地竖了起来。村里人说,这样可以远离死去的恶鬼,但肖安姆块老人还是常常看见丈夫的魂在房里四处走动。
肖安姆块老人年过八旬。黑暗矮小的草房、火塘中奄奄一息的火光和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让我们所有人对她故事的真实性坚信不疑。我们推算,肖安姆块老人的故事应该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距离今天50年。
肖安姆块老人说丈夫死的时候,她30多岁,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在她出嫁的前几天,她的梦说,不是她要葬丈夫就是丈夫要葬她。当时的她疯狂地爱着她的男人,她的男人也疯狂地爱着她。她不想让她爱的男人死在自己前头,如果可以选择,她说就让她死在自己男人前面。她家请来部落里最大的魔巴,杀了一头牛、两头猪、三只鸡,结论都是一样的:她的命硬,留不住身边的男人,她的一生注定要亲手埋葬她所爱的男人。后来,在她儿子25岁的那年,在离丈夫被猎人头不远的地方,她唯一的儿子被来路不明的手榴弹炸死。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老人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眼圈仍禁不住红了起来,干涩的眼睛渐渐充满着泪水。她说,这是在丈夫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她第一次向外人讲起自己的丈夫和所经历的不幸。在她的意念中,这种讲述会将过去的不幸再次转嫁成当下的生活现实。把不幸沉默在心底让它慢慢地烂掉,这是村落族人面对不幸常用的方法。坚守在丈夫和儿子住过的草房里,是老人对丈夫和儿子最有效的怀念方式。尽管现在老人年纪已大行动不大方便,但仍然不愿搬到姑娘家去住。她说,她要为丈夫和儿子守着家魂,在她死后,让家魂带着她去与丈夫和儿子的魂灵相聚。
如果没有眼前昏暗狭小得像坟墓一样的草房、没有这些奄奄一息的火苗,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是出自一个世纪老人的讲述,我无法相信曾经停留在一些简单文字概述中的佤族猎头祭祀习俗会突然间以这种方式再现。
《沧源佤族自治县志》对于佤族猎人头祭祀的描述是这样的:“按照惯例,砍了木鼓后就要猎人头来祭,社神才使地方平安,保佑粮食丰收。猎人头是全寨性的活动,老人、寨主杀鸡占卜后选择吉日,派几十个壮汉去猎取人头。猎获人头后要尽快返回寨子,走到离寨子不远处就鸣枪高呼,寨子里的寨主得知获得人头后就敲锣击鼓,敬告村民不要上山下河。然后由寨主、老人带着红包头、一碗米、一个鸡蛋到指定地点迎接人头,将红包头戴在人头上,把米粒、鸡蛋喂给人头,然后祈祷,给人头敬酒,几个妇女一边哭一边给人头梳洗。接着要举行祭人头活动。主祭人家是经过寨主选定的、能承担祭祀期间村民吃饭的富有人家。祭祀活动结束后,由主祭人家的壮年男子,在众人的吼叫声、铓锣声、木鼓声中把人头装进竹笼里,拾到放置人头的神林里。”
一些史书的记述更为简略:“猎人头祭谷是佤族古代社会沿袭下来的比较原始落后的重大宗教祭祀习俗。主要是为了祭祀谷物神,祈求农业丰收,衣食丰足。往往把氏族之间的血族复仇、部落械斗同猎人头祭祀联系在一起,形成原始落后的猎头陋习。”
在这样抽象的文字概述中,我始终以为,佤族猎人头祭谷习俗就像佤族众多的神话故事一样,仅仅停留在一种口耳相传的记忆中,是一种离现实很远的传说和故事。却不想,在嘎多村落,这段惨烈的历史却是上一辈人共同经历的故事。
三
肖安姆块老人对自己的不幸十分坦然,她说,被猎人头是上一辈嘎多部落人共同的命。
肖安姆块老人讲,在她十二三岁的一个晚上,全寨一夜被猎走了12个人头。猎头手们潜伏在一些人家的竹楼外面,第一个被猎头的人家叫喊起来,其他人家跑出竹楼看的时候,潜伏着的猎头手一跃而起把更多的人头猎走。当时她正在睡觉,听见全寨人的吼叫声跑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些被猎去人头的尸体有的站着、有的朝前倒着,血从他们的脖子流出来然后顺着竹笆滴在地上再往寨子矮的地方流去。这些猎头手来自缅甸一个叫永定的佤族部落,猎头事件的起因是嘎多一个卖篾笆人和永定一个卖刀人的一次口角。
尽管如此,部落中大多数老人都始终坚持,嘎多曾经是一个极为强盛的部落,现在单甲乡的永武、安也、护娥、刀埂和糯良乡的帕秋、南撒等佤族村落都是从嘎多村落分裂出去的,均归属于嘎多的管辖范围。每年举行镖牛祭祀的时候,这些村落寨主都按佤族风俗给嘎多寨主送牛腿子肉,要向嘎多交粮纳税。在嘎多最为强盛的时代,部落的粮仓占满了半个山坡,仅寨主一家就有12个粮仓。
嘎多的另一个佤语名字是“莱格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嘎多曾经拥有过的繁荣。“莱格龙”佤语的意思是“河边的街子(集市)”:“嘎多”则是傣语的译音,意为“黄蜂街”。老人们讲,包括缅甸在内的整个阿佤山区,最早开街赶集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是缅甸的勐冒,另一处是沧源的岩帅,再一处就是单甲的嘎多。每逢街子天,嘎多长长的河岸边便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赶街的人,因为赶街的人多得像黄蜂一样的“嗡嗡”作响,被当时到嘎多赶集做生意的傣族叫作“嘎多”,并作为地名存流至今。据说,正是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嘎多人能言善辩、善于经营的特性。时至今日,在阿佤山区一带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能够说服一锅煮着的猪食,也说服不了一个善辩的嘎多人。”
一生致力于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王敬骝教授从史学角度也证实了嘎多曾经拥有过的繁荣,明末清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起义军将领李定国的护卫下进入阿佤山区。出于持久抗清考虑,起义军在阿佤山区开办银厂,其中的一个王家银厂就在现缅甸境内、离嘎多不远的地方。
人与物的聚集,促使嘎多集市的出现,造就了嘎多昔日的繁荣。随着桂王银厂的倒闭,嘎多逐渐冷落,不断被猎人头的命运加快了这个曾经强盛、繁荣部落的衰落。
老人们说,20世纪30年代,嘎多一夜被猎走了数十个人头,人们四处逃散。这时的嘎多已经无力与那些猎人头部落进行面对面交锋,他们只能把防御寨沟挖得尽可能地深,寨门尽可能设置更多防范的机关。为了自保,大多数人家甚至放弃田地的耕种,以出卖编织竹篾制品来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就是这样,许多嘎多人仍然像肖安姆块老人的丈夫一样,不断重复着被猎人头的命运。
现已年近七旬的老人陈岩倒虽然在一次猎人头中保住了性命,但他的人生也从被猎头的那一刻起彻底改变。他说,他被猎头的时候单甲已经解放,解放军已经进驻嘎多。当时的他正走在回寨子的路上,突然一声枪响,他的脚被密林中飞出的子弹打中,紧接着冲出几个壮汉挥刀就往他的身上砍。他知道,他遇到猎人头部落的猎头队了。为了保命,他一边使劲呼救,一边顺势向一个很深的山谷滚去。最后,是解放军救了他的命。
尽管过去了40年,但被猎人头的记忆仍然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陈岩倒老人说,几十年来,他一直一个人生活。由于他是被猎过人头的人,全身充满着晦气,寨子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来往相处,更没有姑娘愿意嫁到他家里来。在他看来,他真正的人生从被猎人头的那一刻起就结束了,他活着就是为了等死。
老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坐在自己矮小的草房前。夕阳的余晖穿过草房顶上“丫”字形木桩,落满他的一侧身子和半个脸,让我们无从窥见他任何的悲伤。由于他的草房不仅小得无法同时容纳我们四个人,也无凳子可坐,我们只好用一根柴火当凳子,在他的房门口进行我们的采访。
老人说,如果不是解放军的到来,嘎多被猎人头的历史还将持续好多年,缅甸阿佤山区也不会这么早就结束砍头的历史。说到这里,老人脱下上衣指着身上长长的伤疤告诉我们,这些伤疤便是当年被猎头时留下的。
图片来源:今日临沧
四
从史料的记载和我们对其他佤族村落的走访,猎头祭谷习俗曾经普遍存在于阿佤山区的中心地带,其中以缅甸北部佤族聚居的阿佤山中心地带最盛。
在沧源县岩帅镇建设村,陈尼嘎老人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共亲历过四次猎头祭祀活动。第一次是在他十二三岁的那年,最后一次是在1950年。连年粮食歉收和天灾人祸,让潜伏于族人们平静生活之下的拉木鼓渴望再度复燃。他们坚信,所有的灾难都会随着一只新木鼓的诞生而消失,而新木鼓通神的灵性则必须是在隆重的镖牛血祭和神圣的人头祭祀过程中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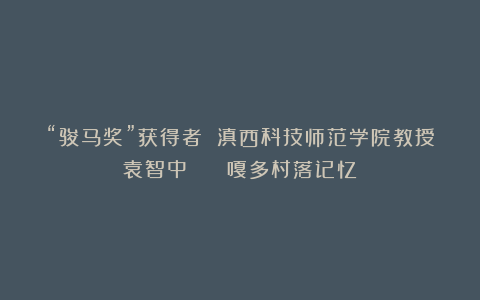
那一年秋收刚结束,村落寨主和魔巴就把全寨的老人召集起来,决定冒着被批斗的风险进行一次盛大的拉木鼓活动,而有没有人头祭祀木鼓则是新木鼓能否获得神性的关键所在。
在一个属虎的日子里,十名肩负着猎头重任的壮汉背着长刀走出山寨。按照传统猎头习俗,所猎人头最好是长有长胡子的外族人或是与本寨有仇部落的人头,但随着各部落械备的加强,猎头变得越来越难,为了在规定的时辰里猎到所需的人头,所有与猎头队相遇的人都会成为被猎头的对象。新时代的到来,要猎取一个活的人头更是变得难上加难。猎头队听说十多公里外的单甲永武有一个亡人刚刚下葬,便在深夜潜入墓地将死人的头猎回寨中。
当猎头手向寨子发出猎到人头信号的那一刻起,全寨猎人的火药枪声便在山间此起彼伏地响起,男人和女人的歌声、舞声便在山间回荡,部落寨主就会为那些脸上和臂膀抹着黑锅灰的猎头手们藏上漂亮的红包头,魔巴的《祭头歌》就会在寨子上空响起:
好人头啊,
你是最良善的人,
你是最尊贵的魂:
你是男人中最强悍的人,
你是女人中最温柔的人,
我们请你来当家,
请你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请你来守护我们的田地。
不要让洪水淹没我们的庄稼,
不要让岩鼠偷吃我们的谷穗;
让庄稼裸裸长得好,
让谷穗粒粒饱得倒地。
一颗谷子结三枝穗,
每枝穗像苞谷一样大
让我们的粮仓个个满,
让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
对于往事的讲述让陈尼嘎老人回到了过去,激起了他年轻时代英雄梦想的激情。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对父辈猎获人头的壮举充满着向往。但现在的他已经老去,只能在唱起《祭头歌》的时候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嗓音如当时的祭司那样真实。老人的双眼望着远处的山,声音不大,但十分苍凉,它以超越世俗的神秘力量直抵我的心底,让全身的血液停止了流动,手脚也变得有些冰凉。
尽管相隔遥远的时空和性别,在老人粗粝的苍凉歌声中,那个壮烈的年代与那些雄壮的身影、夯实的舞蹈、狂欢的喜悦,仍旧踏着魔巴的歌声奔涌而来,像老人们向我描述的那个神灵世界那样真实、那样令人战栗。
一起从“司岗里”出来,都是木依吉神的族人,都有着黑黑的皮肤,为什么还要用自己同胞的头去祭祀谷魂?老人回答:这是神的安排,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习俗,只有这样才能让部落族人远离灾难、稻谷丰产。所幸的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猎头祭谷也成为一段尘封的记忆。
五
作为一个在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佤族后裔,我曾经试图在阿佤人神性世界之外去寻找佤族猎人头祭祀的合理解释,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民族都有过猎人头祭祀习俗。比如说,古代西南夷一些部族中就流行猎人头习俗,考古学家从一件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人头祭场面中发现用于祭祀的人物达127人之多。古代这些部落里的武士们像陈尼嘎老人向我所传达的信息那样,均以猎取敌对部落、族人的头来标榜勇武,形成了猎取人头是部落对外战争的组成部分。我无法理解的是,佤族猎人头祭祀仅仅是对一种习俗的传承,还是佤族人希望通过猎头祭谷这一最高的血祭形式帮他们找回昔日的辉煌,让自己回到传说中丰衣足食的坝区生活年代?
对于我的提问,老人们的回答却是惊人的一致:这是神的安排,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习俗,只有这样才能让部落族人远离灾难、稻谷丰产。所不同的是,嘎多这个被猎人头部落所包围的部落,早在上几辈就舍弃了猎人头祭木鼓的习俗。在嘎多下寨,人们用镖牛的方式替代了猎人头习俗,在大多数部落还没有舍弃拉木鼓活动之前,便以拉木桥活动替代了拉木鼓活动,血腥的祭祀早已远离他们的生活:而在嘎多上寨,人们甚至将行酒礼改为了行茶礼,不仅让茶主宰了祭坛,让酒也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亲历那些讲述,我无法相信在这些平静得有些淡漠的眼睛深处会隐藏着如此深刻的痛。
我进行以上联想时,太阳正从山的那边落下,雾正从我的脚下升起。站在嘎多如同壕沟般的村落道路上,仰望着一道道如同迷宫般的栅栏和一栋栋具有数百年历史沉淀的干栏式草房,这些故事在我眼前幻化成一幕幕现实的真实,让我的行走陷入了一种神秘文化的迷雾中。
现在的嘎多早已经没有了防范森严的寨门,深至齐肩的寨沟已经演变成了人和牛马牲畜行走的村落道路,整个村落与这里的山完全融为了一体,和这里的村民一样变得安静、从容。时间这只无形的手,把这里曾经拥有过的强盛、繁荣,以及所有遭遇的不幸都一点一点地抹去,让这里的人们超越于所有的幸福与不幸,与他们所祭拜的众神一起,安静从容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但是,从嘎多村落的格局和建筑中,我仍能够感受到被村落族人刻意隐藏的关于灾难的强烈记忆,所谓的遗忘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按照建筑学的理论,所谓的建筑风格就是一个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在嘎多,大多数村民的房子仍然保持着佤族传统干栏式建筑,只是这里的干栏式房屋与我所走过的大多数佤族村寨相比,显得更加矮小。像肖安姆块老人和陈岩倒老人这样的贫困户,住的是直接落地的鸡笼式草房,就是像我这样只有1.55米高的小个子出入时都得猫着身子,家里挤得除了火塘的位置就只剩下一个人的空间。但是,无论房子是大是小、是矮是高,全寨一百多户人家每家每户的院子和菜地都用一人多高的石心竹或细树枝密密匝匝地围起来。层层叠叠的栅栏在一条条壕沟似的村落道路的映衬下,形成一道奇特的、别有韵味的景观。
当我们这些身着奇装异服的外村人从他们房前走过时,他们便会停下手中编着的篾箩或是正在劈着竹篾的长刀,透过栅栏久久地窥视着我们。我相信,这样层层叠叠保护式的建筑和挤挤密密的村落布局,曾经让很多族人幸免于被猎头的命运,让族人们在猎头祭祀盛行的年代产生更多的安全感。但这种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阻塞了族人与族人之间的沟通,更阻断了与外面世界的心灵通道,让他们在这种自闭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拱手交给了神灵。
图片来源:今日临沧
六
走访中我们发现,尽管已经进入21世纪,村落的族人们仍然跟神灵世界建立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今天的嘎多,仍然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村落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草房、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个有形的存在都有灵魂栖息,在日积月累中,都附着自己部落族人的气息。如果不是天灾人祸,如果不是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村落的族人从不愿意随意改变村落的模样,哪怕是一条道路的走向,甚至是一个石头的位置。他们认为,打破了神灵世界的平静,就会打破人与神灵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默契,轻则会生病,重则会引发各种的灾难。
我们的到来似乎打破了村落的宁静,我们的生魂让这里的魂灵世界嗅到了来自远方的气息。我们到寨主家拜访的时候,寨主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举行滴茶礼、念经叫魂。村支书解释道,不行滴茶礼、念经叫魂,我们携带的生魂就会惊吓着他家的家魂,他家的人畜就会生病:如果遇上那种命相很硬的人,还得举行叫寨魂仪式。从寨老们的神态中,我们也看出他们把这次行滴茶礼看得很重。
寨主面对我们的到来一言不发,而是从火坑头上抓了一把茶叶放在土茶罐中,放到火塘边慢慢烘烤。待茶叶发出一股茶的清香时,再把火塘上铁壶里的水倒进茶罐,放在火塘边煮沸后倒在一个小碗里。寨主才摘下帽子,将头垂下,用双手将茶碗举过头顶。魔巴从竹篾桌上抓了一把米花向空中抛洒的同时,诵经声便在房子里响起。寨老们则垂下双眼、双手合在一起放在头顶,和魔巴一起沉浸在神灵的世界中。
我的呼吸也变得缓慢起来,心也渐渐迷乱起来,我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呼吸都会惊动或是惹怒了四周的神灵。直到魔巴的诵经声落地、寨主把茶滴在地上,然后把茶碗双手递给支书,开始用正眼看我们的时候,我的心才落了下来。
老人讲,嘎多的祖先是从缅甸绍帕迁来的,但他们已经说不清在这里居住了多少代,只是说在一次狩猎活动中他们的祖先发现这里有河、有水、有茂密的森林,可以开田种地,便带着部分家族成员到这里劈山开地建寨。勐买绕(肖姓)家族祖先建了上寨,然后格沙(陈姓)家族祖先建了下寨。直到今天,嘎多上寨仍然是以肖姓为主,嘎多下寨仍然是以陈姓为主。尽管历经了数十年被猎人头的命运,但整个嘎多早在上几代就摒弃猎头祭祀习俗,上寨改信骞玛教,行滴茶礼,不猎头、不镖牛、不拉木鼓,而是以歌舞的方式取悦神灵;下寨仍然拉木鼓,行的是滴酒礼,拉木鼓活动中以镖牛祭代替了人头祭,或是猎虎头来祭木鼓,最后又以拉木桥替代了拉木鼓活动。
图片来源:云南网
我们走访的是上寨,行的自然是滴茶礼。老人们边讲,边双手把茶碗传递到我们面前。茶很少,只盖住碗底,却是浓浓的、黄黄的,却又晶莹透明。小心喝下一口,一阵浓浓的苦涩之后,透彻的甘甜便从舌面向着整个口腔弥漫开来,接连数小时访问所产生的疲惫也在体内慢慢散去。喝完之后,我们学着支书的样子,揩了揩碗口再双手把茶碗递还给老人,并让与我们同来的翻译把我们的一个个问题传送给老人。与我同来的采访者把录音的话筒放到了老人们中间,我紧握着笔,眼睛直直盯着讲述者,生怕遗漏了哪怕一个音节或是一声叹息。但是,茶一直让老人们对我们的到来保持着一种警惕和戒备。村落的封闭,让他们在与陌生人的接触中充满着不安。当我们要求老人们为我们唱一些类似于拉木鼓、猎虎、贺新房、结婚的调子时,老人们更是变得沉默起来。支书告诉我们,老人们的吟诵和经文必须依据现实祭祀场景而起,在不合时宜的场景唱不合时宜的调子会惹怒神灵,神灵会降罪于他们。虽然我们看不见神灵,但神灵看得见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灵的眼中。
七
从寨主家出来的时候下起了雨,前面的山和房屋沉浸在雨雾中。雨点滴在竹篷上、草片房上、树叶上的声音、远方河水的“哗哗”声,伴随着泥土的清香从不同方向汇聚到耳边,有一种身居世外的奇妙感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大地的声音,看到大地的存在。
支书开玩笑说,这几天总讲一些与鬼神相关的故事,神灵生气了,下起了雨。在支书的提示下,我果然听到了来自神灵世界的声音:有的奔腾如河水,有的沙沙如细雨,有的如轻落在头上的雨滴,有的如流过脚面的积水,有的如浓雾般萦绕,有的如雨水般欢腾,带着泥土和丛林的清香,从发尖和洞开的毛孔向着心灵进发。我看见带给我嘎多的第一个传奇故事的老人——肖安姆块背着一个背箩站在雨中看着我们。透过密密的栅栏,老人正安详地笑着,似乎天上飘落的不是雨而是一缕缕温暖的阳光。她的身后有云雾在缭绕,透出的村落和房屋、树木和道路,都变得遥远而模糊。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有着一种想哭的冲动,我知道我的心与这个村落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血浓于水的深情。
在我们即将告别嘎多的时候,村支书告诉我们,寨老们突然同意为我们诵经和唱调,但诵经和唱调的地点不能在他们当中的任何一家,只能在村委会。理由是:村委会一个强大的组织,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不用说是现实中的人,就是村落的鬼神都会服从于它们,不会因他们不合时宜的吟唱而怪罪他们。在几天的访问中,我们都是在不同人家的火塘边度过。这些衍生于火塘边的村落故事,因为火塘的体温、摇曳的火光、昏暗迷离的脸谱,让所有的讲述充满着一种奇妙的现场感。我们决定,把唱调的地点选在村委会的火塘边。
老人们在寨主带领下,来到了村委会。他们重复了一回上次的茶礼,魔巴念着向鬼神请罪的经:
不是我们要在不合时宜的时间,
唱不合时宜的调子,
是远方的客人想要听见你们远古的声音。
要睡你们就好好地睡,
要吃你们就好好地吃。
让我们的声音像风一样从你的耳边飞过,
让我们的声音像尘土一样不被你记起,
魔巴把碗里的茶滴在地上,再将余下的一口喝了进去,用手掌擦了
擦碗边双手递给寨主便唱了起来:
管理世间的神,
管理山水的鬼,
如果不小心触犯了你,
你不要伤害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沿着祖先足迹走的阿佤,
我们是传颂父兄礼节的后人;
我们不会失落祖先传下的种子,
我们不会丢掉祖先传下的礼。
我们会顺着你们的心意行,
我们会踩着你们的足迹走;
我们会用最高的茶礼敬你,
我们会用最好的鸡献你。
让我们的谷秆粗又壮,
让我们的旱谷背不完;
让我们的粮仓排成行,
让我们的猪牛个个壮;
让我们像麻雀一样快乐,
让我们的人站满山岗。
……
魔巴的声音很轻,担心惊扰了沉睡的神。我知道,他正在神灵与我们之间做着艰难的平衡。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知道我们总是会走,也在心里暗暗祈祷,我们的要求不要破坏了他们与神灵之间建立起来的默契,让这里的村民安静、从容、幸福地走过每一天。
那一天,老人们的调子一直唱到很晚,他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出一种眷恋。
图片来源:云南网
八
离开嘎多后,我们来向乡里的领导告别。乡里的领导自豪地告诉我们,也许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嘎多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村落。当我们询问原因的时候,乡领导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茅草房改造,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嘎多村也要像现在许多佤族村落一样全部改造成石棉瓦顶建筑,这里的阿佤同胞将永远告别茅草房。我的心突然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不是我要在不合时宜的时间,
表达我不合时宜的悲伤,
是我无法改变的悲伤让我如此悲伤。
要睡你就好好地睡,
要吃你就好好地吃。
让我的悲伤像风一样从你的耳边飞过,
让我的悲伤像尘土一样不被你记起。
当我在电脑上写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距离嘎多的这次访问已经过去了近一年,但在嘎多的每一次走访仍然如此清晰。在远离嘎多的日子里,每一次想起嘎多,每一次讲述她的故事,我的心仍然被她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我相信,随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嘎多人向神灵祈祷的那些美好生活向往,都会逐一实现。
2007年3月完稿
2016年5月定稿
节选自袁智中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书籍介绍】《我的母语部落》一书是学者袁智中为深入研究佤族历史变革的专著,该书获得“201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立项,2017年获得批准为社科立项项目云南“民族直过区”佤族村落社会变迁研究,该作品由此前两项研究成果整理而成,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准的关于佤族的历史散文作品。作者通过一个个带着生命体温的文字、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群群鲜活的小人物的故事,向读者呈现其亲历见证的村落变革,以及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的变迁交集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改变。作者试图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佤族村落的变化应该是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语境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村落深刻变迁的样本,是作者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书写的一部村落志,是人类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心灵史。书中所描绘的应该是作者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当下的生存现实、生态、独特审美的真实画卷,著作的讲述应该是从容的、客观的、理的,同时又充满着生命的质感、情感的温度和人的温暖,而不应该承载过多个人主义的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作者试图通过云淡风轻的文字,带有母语韵律的叙事,真实客观立体的记录,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拓宽自己文学叙事的边界,为传统村落志的书写提供更多的可能。
木色年华
▼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