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8 13:33
新世纪乡村建设20年,我们鼓励了数以万计的青年人下乡,在这个过程中有了对青年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当然外界对我们的做法也有一些批评,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我们耽误了很多年轻人,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出路;甚至有人认为我们是在诱骗青年人下乡。
如果说诱骗,我们是先把自己“诱骗”下乡了。说到耽误,我这一代人当年就是所谓被“耽误”的一代。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遭遇“文革”,全校停课,大家都上山下乡了,从事着简单的体力劳动,被认为是耽误的一代。
后来我们这些人在知青返城之后确实也经历了一段相对而言比较卷的时期,但很快大家又都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我就是当年下乡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也是被“耽误”的一代中的一个。从我自己早期的经历以及后来我们从事的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来看,这个恐怕也谈不上是耽误不耽误。
当年我们回城以后,我们中学的班主任老师请大家聚了聚,他很看好我们班的学生,花了很多心血,老师为我们感到很惋惜。但在场的同学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老师,我们没什么可遗憾,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生难得的经历,经过这种锻炼,我们都成长了,至少在精神上,我们是强大的。
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的老主任杜润生,曾对我们说,你们这批人,如果能够动员起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下乡支农,你们的事业就成功了。这段铿锵有力的话,我记忆犹新,至今仍然把杜老先生当年对我们的要求,当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所以无论有多少批评,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如果我们动员起来的这些下乡青年,都认为自己被耽误掉了,那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确实应该算是教训大于经验。但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反映,我想外界各种各样的说法恐怕也不必计较。
世纪之交,我们发起了大学生支农活动,在演讲中我引用了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这四个字,当时主要针对的是90年代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
90年代,中国遭遇美国带领西方的全面制裁,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期,突然遭遇到外资归零,工业化进程遭到极大的打击。再加上我们当年走了一个宏观紧缩的调控之路,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失业,导致各种社会不安定事件频发。
面对经济的长期衰退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找不到根源,传统理论给出的那些结论,无法有效解释当时面临的复杂局面,于是当时就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照搬思潮。
从90年代开始,高校首当其冲,照搬了西方教科书。比如现在一般所说的经济学,其实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称其为“庸俗经济学”,全称“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专注于分析表面现象(如需求和供给),而忽视结构上的价值关系,不愿意以公正的科学方法探究经济关系,忽略对潜藏在商品交换行为下的阶级关系进行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庸俗经济学有所描述和批判。
但随着西方的学科体系进入中国,庸俗经济学没了,西方经济学前边的“西方”俩字也没了,它就被当成普通经济学,成为一个似乎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一个学科体系。
从历史角度来看,对于包括我们在内的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只要把西方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全套照搬过来,没有谁能逃脱得了走向反面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下,从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高校教育以及基础教育产业化的现象。产业化就意味着创造了外部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的空间,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导向对原有的教育体制形成了根本性的破坏。各种各样的学校一时风起,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收费一路攀升,教育逐渐变成了一个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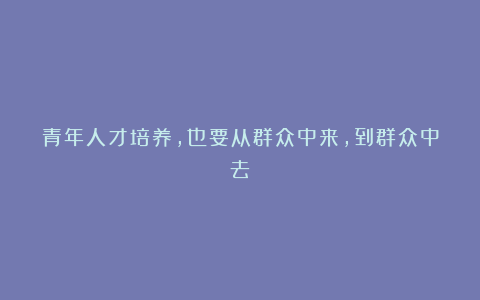
教育是一个可以凭借对知识信息体系的单方面垄断来获得收益的领域。只要信息具有垄断性,它一定是高收费的。同时,教育质量不断下降也导致了很多后果。
当然,大量照搬的西方理论,跟中国具体国情是不相符合的,那些从实践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他们很难完全心服口服地接受这套教育体系所传授的这些所谓的知识。
在这个阶段上,很多青年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更有甚者,跳楼、自杀等现象都在发生着。所以我说“救救孩子”,教育已经这样了,我们如果能够带动这些青年人下乡,相对来讲,对他们思想精神的正面作用可能会更大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帮助大学生下乡,是针对当时主流的教育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思想。
更具体地说,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来自于工农群众的生源越来越少,教育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入场券的发放机构;另一方面,这些青年人进入到高校,不可避免地面临城乡差距、阶层分化带来的冲击,其中一些人就从原来小镇精英变成了失落者,这种失落感也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组织他们回乡,他们多多少少能做一点回报家乡的事情,就会使家乡的父母、家族能有一种光荣感,他们仍然是家乡父老乡亲心中的那个精英。那种荣耀很大程度上会形成他们回到高校这个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中维持自信的基础。这个想法在当时比较有现实意义。
我当时在国务院体改办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工作,担任社长兼总编,我们就给这些下乡青年的调研报告评奖,帮他们去做发表,这样使他们可以在上学期间获得一些资历。
如果回到当下,我们的领导人强调要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研究和脚下的热土结合,应该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与此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年关于青年人培养的思考和实践,在今天其实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农民负担问题都非常突出。而在当年,高校学生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开始流行,有车有房、中产阶级等成为所谓的成功的标准。
很多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年轻人进入高校,他们既看到了城市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也看到家乡的亲人朋友仍然面对着种种艰辛,在这种强烈对比之下不免生发出朴素的不忍之心。而这种不忍之心,其实是百年乡建非常重要的动力,也是让百年乡建内在血脉相通的情感内核。
当年我们把这批大学生支农社团中的骨干,安排到村里做一年的志愿者,他们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们只给点零花钱,维持他们在当地的基本生存。在这个过程中就看他们能不能跟农民结合,能不能生存在农民群体之中,能不能多多少少对农民有所帮助。用这种方式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本质上,应该至少有了那种不忍之心,他们就是我所说的“白豆腐”了,哪怕掉到灰堆里边,沾了点灰,拿回来用水冲冲,它还是白的。
这种不忍之心其实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它是历史传承延续下来的,不忍觳觫嘛。尽管被批判者们嘲笑,但它实际上就是“人称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精神状态。用这种方式,我们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今天在各个岗位上都算是有一定能力、发挥了一定作用的骨干。
应该说,我们参与推动新乡村建设运动二十多年来,是先把自己“诱骗”成了下乡青年,在推动大学生下乡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实践出真知的青年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个过程是不是诱骗,他们可能比外界更清楚。而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经验过程。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