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城
/ BOOK TOWN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强调“自动者”才是历史,“他动者”不是历史。而英国史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主张,凡有思想的行动是历史的,没有思想的便是非历史的,他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然而,历史学的发展已经出现无数的新课题。王汎森的《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秉持陈寅恪“从史中求史识”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各种形态的历史都可能提供今人意想不到的资粮。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启示,而王汎森更强调的是读史如何提升人们整体的心智能力(“心量”)。
在《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中,作者手挥五弦,通过许多史学名著的智慧,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理念,使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一些重要的史学观。这些观念并不是定论,更非“定于一尊”,而是尽可能地开阔读者的视野。
《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
王汎森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4年版
王汎森检视三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第一,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认为只有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文明的包袱越少越好,他抗议:学习太多的历史只是加重人身上的负担。第二,许多史家刻意迎合当代的需求或当代的渴望,写出来的历史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翻版。就像在一个情报局中,情报员所收集的材料太想迎合局长的偏好,以致收集的情报变得毫无用处,历史成了“活人在死人身上玩弄的诡计”。第三,人类始终有一种古老的期望:能够借由阅读历史获得像占星家般预测未来的能力。事实上,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最不同,及其同样精彩之处,即在于其无限可能性及不可定律性。为了应对关于历史的悲观论调,王汎森提出“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把人的内在世界想象成一个空间,平日就不断地开拓它,充实它,使它日渐广大,不至于心量浅陋,甚至收缩成一道扁平的细缝。一个心量广阔的人,立身、应事,志量视野都比较宽大,而且因为资源丰富,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用处。如果心量过狭或心中没有积贮,即使是天资非常高的人,其深度、广度都很有限,只能靠着一些天生的小聪明来应事。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 尼采 著
周思成 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
在日常生活的“历史思考”中,王汎森认为,“未来”是没有地图的旅程。一九五一年,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有一段名言:“当人在从事政治行为时,就仿佛在一个无垠无界、深邃无底的海洋上航行。在此海上既无港湾以资屏蔽,亦无浅滩可供下锚;航行既无起点更无目的。一切所努力者仅求平稳地漂浮着。这海不但是朋友,亦是敌人;而此际航行的要领乃在于利用我们所享有的传统中所蕴含的资源与启示,来克服每一个惊惧危疑的时刻。”以此观疫情之后的景象,颇有启示意义。
古希腊悲剧有净化人心的作用,读史亦然。戏剧家翁托南·阿铎(Antonin Artaud,1896—1948)说:“它逼使人正视真实的自我,撕下面具;揭发谎言、怯懦、卑鄙、虚伪。它撼动物质令人窒息的惰性,这惰性已渗入感官最清明的层次。它让群众知道它黑暗的、隐伏的力量,促使他们以高超的、英雄式的姿态面对命运。”王汎森有感而发: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共鸣箱,历史撩拨琴弦,人们想看电影,想看故事,即如想看史书。人常在读史中生起庄严、悲凉的感觉,一如听古典音乐,一方面激发情感,一方面净化内心世界。对一般人而言,历史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充实、享受快乐、知识、美感、教养、认同、情感等。
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历史研究》中提出许多律则性、“挑战与回应”等,当时便有人嘲讽他在提倡一种“历史占星术”。而通俗史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写了十几册《世界文明史》,后来他还写了《历史的教训》,试着找出历史的某些定律,如“历史教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所有民族都有贡献”,“抗拒改变的保守者和提倡改变的激进者一样重要”,“战争是历史常态,和平不是”,等等。但“历史考证学派”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历史规律”。傅斯年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宣称,历史是一种人学,但历史是没有规律的。
《历史的教训》
[美]威尔·杜兰特、
[美]阿里尔·杜兰特 著
倪玉平 张闶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
王汎森将“律则”做了若干区分:“强律则”“弱律则”“大律则”“小律则”等的分别。而历史的确有一些“软性的律则”,如,但凡暴虐之政最后终归灭亡。清代读书人赵钧在日记中写下:“余观史册,见有一人坏国,而天下均被其患,至有耳不堪闻者。譬如不戒于火,其初仅一星耳,不力加扑灭,延烧莫制。”历史上横暴、荒淫之君臣,最后下场大多是相似的。虽然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可循,不过,有经验的读者即使不一定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也应该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类型或演变趋势。历史思考能培养人们对“长时段”的判断,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了解任何事件都得了解它的历史。刘易斯·加迪斯(Lewis Gaddis)说,读历史如看后照镜,可以帮助驾驶前检视后方、左右的车况,然后决定如何开车。
现世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世界。理想可以是永恒的,但这世界不应被亘古不变的原理或范畴来解释。王汎森认为统治者不可能永远压抑得住历史真相,各地皆然:“压抑历史,使得社会错失了和解的机会,即你充分了解我的历史、我也充分了解你的历史,并寻求互相谅解、寻求和谐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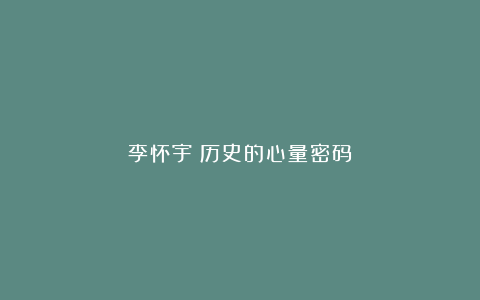
龚自珍在《释风》中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风之本义也有然。”人类历史并不总是井然有序、因果相续地进行着,因此,“察势观风”也是“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历史如果只是为了把过去的历史打扮成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样子,那还研究它做什么呢?王汎森认为“历史思考”的一部分是发掘历史中的各种音调(不只是低音),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层次,免得读者误以为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单音。
“以史为鉴”“历史的道德教训”等传统史学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宋代的叶适便主张恢复古代的史法,不要像司马迁《史记》那样把项羽写得那么正面,可见把历史与“道德”紧紧绑住是一个非常强的历史书写传统。王汎森认为人们是可以从各种历史著作中看到是非善恶、理乱兴衰,以及一些带有长远性的价值的,自古以来所谓“以史为鉴”就是历史与现实、人生之间的一道桥梁。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完成之后的《进通鉴表》中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读史所获得的“知”本身与智性的满足、充实感是人类天性里最重要的需求之一。王汎森说,他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最重要的便是“知”的乐趣,而不是有任何立即得到的现实益处。读许多的史书,最重要的也是一种“知”的乐趣与满足感。更何况读古往今来许多史书,本身便是极大的美感与享受。
历史虽然不一定重演,但并不表示没有相似的情境。当人们感觉古今情境相仿佛时,会从历史的前例中找寻。《马歇尔回忆录》中讲到当二战开始,他决定在美国进行“动员”时,发现战况与他早年读过的战史何其近似。基辛格在梅特涅的生平中看到核子时代平衡外交的精神。拿破仑深受普鲁塔克《英雄传》的影响,精研意大利各地的历史,当他进军意大利时,简直像来到一个熟悉的环境,无往不利。腓特烈大帝曾说“没有欧洲国家可能征服俄国”,在相仿佛的境况下,拿破仑、希特勒两度重蹈历史的覆辙。
读历史可以让我们“重访”过去。王汎森深入地探讨“重访”的必要性。历史在舞台上时刻上演,如果历史没有“重访”,古往今来发生过的许多事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罗马史大师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完成《罗马行省史》研究后,有人说:“一个消逝了的世界,由于一个人的天才而得重现。”
王汎森提到“使历史上的成为我的同时代”的意识,与艾略特说的文学创作中的“历史意识”相近。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他又说:“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具备历史意识时,在他的意识中,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跟他之间有处于同一个时代的感受。”所以必须衡量它、审度它,从中吸取教训。
在论证如何化“在心上”的为“在手上”的时,王汎森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将战史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之中。克劳塞维茨强调“科学”与“艺术”的不同,也就是说战争的历史、战争的知识是科学的,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是“艺术”。克劳塞维茨说:“科学必须成为艺术。”“亦即这知识必须彻底融入头脑,几乎完全不再是某种客观的东西。”“通过与他本人的心灵和生命的这一完全同化,知识转变成真正的能力”。而《资治通鉴》在讲一件历史中大事的发展时,常常将臣下的各种不同意见一一胪列之后,再从事情最后的发展回头去看,究竟哪一家的建议比较对,然后司马光再做一个评析。这也是磨炼读者从“在心上”转到“在手上”的一种办法。读史要充分熟悉史事,并时时磨炼自己,使得自己像是在历史上的那位人物,可以几乎脱口而出历史人物想说的“下一句话”。历史知识化为实践性知识,由“科学的”成为“艺术的”,由“知”的变成“行”的,由说得一口好菜到做得一手好菜,从说得一口好经济到真能振兴经济,殊非易事。王阳明强调,熟读两京十三省地图与实际走一次两京十三省的路程是不同的,前者即“在心上”,后者即“在手上”,但是不熟悉两京十三省地图,也到不了京师。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性格即是命运”。王汎森对此言并不完全反对,但也不完全同意,人的性格跟其命运是互相决定的,后天要依靠先天,先天也要靠后天。通过历史中的各种事例,说明人可以因“量才适性”,超越自己性格的限制,而得到成就、事业与人生的智慧和勇气。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说过:“一个故事先于一个人生。”这句话看来很玄妙,大意是说人生本来是茫茫无定的,而历史的范例可以赋予生命轨迹。许多人的人生,是从历史上某一个人物的轨迹中获得现实人生的暗示、指引,并赋予生命的结构。譬如苏东坡学白居易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而清初的宋荦则自认为是苏东坡的后身,此后一生的生命轨迹、成就,也多与苏东坡相似。史书对一个时代的人物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了不起的原因之一是把人物的性格都写活了。史家章学诚就抱怨中国历史上的正史写人时,太为“格套”所拘束,所以他只写一般传记不写进去的东西,如此才可以把那个人的性格凸显出来。而西方经典《摹仿论》说,西方人的性格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影响。中国思想史里,对人的性格与自我是非常关注的。《人物志》里认为,能担大任的性格是“既在乎又不在乎,不在乎中又时常在乎”。人的性格要像白开水一样,因为像白开水一样的人才能调和各种不同的味道,才能调和各种不同才能的人。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里提到“转”,他认为人的性格中有部分极难变但是可以“转”。“转”就是“量才适性”“尽其在我”,只要用对地方、用对时机,人人都能有所成。清代阮元是了不得的经学家,同时也兼做大官,他编了几部大书,譬如《皇清经解》《经籍纂诂》等。他让聪明的学生去写考证文章,资质平庸的学生则集合起来编一部工具书《经籍纂诂》。如今《皇清经解》里那些聪明人写的文章都已经不大有人理会,而资质普通的人编的《经籍纂诂》则还有用。傅斯年有句名言:“进我史语所的人即使是天资普通的人,将来也可以青史留名。”因为史语所中天资不高的人编材料书,天资高像陈寅恪去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两者都有各自的贡献。
《天风阁学词日记》
夏承焘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歌德有句名言,能有大成就的人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好的头脑,一个是好的时势。朱熹说,他发现某一个禅宗寺院墙上挂的历代大师都像土匪(渠魁)。这其实可以理解,禅宗要人斩断一切。明代名僧紫柏尊者(1543—1603)出家前饮酒恃气,自称“吾本杀猪屠狗之夫”,邂逅某一僧人,在虎丘寺听闻八十八佛名,隔天便剃度出家。据《天风阁学词日记》所载,宋元人笔记说文天祥的头顶上有“凶发数茎”,看相的人就说头顶上有凶发的人不得好死,可是文天祥的“死”选对了时机和情况,便成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又如“司马光砸缸”,好像他很急智,但是同时代的前辈邵雍,认为司马光只不过是一个天分不高的老实人,只是他充分发挥老实的性格,耐着性子慢慢地去编《资治通鉴》。善用其短也可以成为人才。章学诚次子章华绂在道光大梁本《文史通义》序里写道,其父是天资普通的人,记忆力很差,所以没办法成为一个考据学家。可是章学诚擅于思考,他就用自己的特质成就了一个史家,与当时天资极高的考据学者戴震成了清代中期学术中并峙的双峰。
小提琴家穆特(Anne Sophie Mutter,1963— )说,要一个人成为航海家,先要给他看航海的美妙,他自己就有办法逐步摸索达到。王汎森借此以论如何成一个领袖:历史教导我们许多领袖人物的特质,譬如宏阔的心量,请比自己聪明的人来帮助自己做事,集天下人之智为自己办事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三人主导了晚清思想的走向。康有为说我们要在大自然里面“观”,看大自然来扩大我的心量。康有为在《南海先生口说》跟他弟子的谈话中强调,“观”要在高远的地方看,“我大则事小”:心量如果够大,事情就小。王汎森认为才能、性格、心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代施肩吾说:“大其心,容天下之物”,“大其心”便有“扩充心量”之意。想象自己的心是一个浩大无比的空间,可以容纳天下万物,并想象用历史或一切用得上的知识与道理去充实它。
王汎森举了几个例子,说明许多古今中外知名的领袖人物以历史名人为模范。拿破仑的人物典范是恺撒,他连头发的分法都跟恺撒一样。华盛顿的学习典范是古罗马大将军辛辛那提,古罗马那些有名的将军最理想的人格表现就是胜利之后回到家乡营造一个庄园,不要去干涉政府,在那边度其一生。哈佛大学普特南(H. Putnam,1926—2016)悼念政治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文章说:罗尔斯亦步亦趋地学林肯,读了几乎所有有关林肯的东西。罗尔斯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可能是从林肯那儿转手而来的。
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察势观风,从中观察出大趋势。王汎森认为事件、中时段、长时段三者互相交织式的读法,并且详究史事发展的“症结”,才是较佳的读史方式。朱熹说,读春秋史要能瞻观两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中看出历史的变化及治乱得失的“机括”。读书要熟到好像永远再也见不到这本书,所以朱熹形容是如“作焚舟计”,“如相别计”。而吕祖谦认为“历史”是一座“药山”,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各种药,而且“随取随得”。他反对人们只看或记诵历史事实,而是要人们“观史如身在其中”,这样才能得“药”。吕祖谦认为历史是优先的,必须在水库中蓄积足够的水(历史),才可以打开水闸,与“义理”互相印证。曾国藩教其子弟读史时则说:“莫妙于设身处地,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
前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王汎森认为,每一次“用史”都是一次全新的经验。所以从来没有人宣称饱读管理学即可成为大企业家,饱读战史就可以称霸沙场,饱读政治史就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外来的知识只是条件,要化成自己的智慧才能受用。《石涛画语录》中贯穿全书的“一画之法”,石涛怕把画法本质化或格式化,所以绝不明白说死,只从“一画”说起。他又强调“受”在“识”前,也就是说要尊重感受的独特性,不要被“识”把它从外而来加以了解,加以框限化、平板化了。画家吴冠中用了一个传神的例子做说明:西方有一位名画家有一回见到一片黄泥泞路,他宣称要用这一片黄色画一个女孩的金发。即使是一块脏兮兮的黄色,只要运用得当,正是描绘金发最合适的颜色。读史之受用或历史知识之发挥作用,正像那一片路上的黄泥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即可画成一头最好的金发。
历史是超越人类生命限制的,人的生涯有限,但通过历史知识可以扩充心量,超越现在,从生活环境及条件的限制中解放。“心量”的观念是从佛家来的,如《六祖坛经·般若品》中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在佛家的观念中,“心”是一个空间,佛经中经常有“心量广大”之类的话,其中有大小之别,而得道者心量大。宋明理学承袭“心量”的概念,每每用来诠释先秦思想。朱熹说:“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理学家设想内心的世界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要用格物穷理的工夫把它填满、扩充开来。“扩充心量”可以理解为心中天生便有众理,应如大厅中由千灯组成的吊灯,每穷一理,便开启其中一盏小灯,读书穷理,基本上是使得人心原有的各盏灯(众理)获得开启。王汎森认为读史一方面是可以“穷理”,但同时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潜在的无限大的空间,里面有许多小空间,要用知识、经验去充填,它才会撑开,否则它会皱缩在一起,而这两者都是扩充心量的工作。
《东林书院志》中说:“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王汎森用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这个表述,是为了强调“心量”中积贮的历史知识并不必然是以“律则”“定律”或“重演”的方式使我们从中获益。现实的情境有无限复杂的变化,即使古今有相似的情境,也不一定能把古代的历史照着搬到现世来用。故“心量”中的积贮是要经过大脑的吸收转化之后,再成为生命中有用的一部分。用陈寅恪的话说,是“在史中求识”。
教养、见识是一种资产,是一种本领。王汎森认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抉择往往都是由教养或心量决定的,而在关键时刻,凭借“教养”“心量”所形成的一个小小抉择决定了后来重大的结局。美国名将李奇微曾说,伟人自传与战史是一宗最大的资粮:“人们靠自己拥有的个人经验十分有限,所以你必须依靠外人的经验。”而章太炎观察民初许多乍起乍落的政治人物,认为他们就像是只凭天生聪明在下围棋的人,“心量”不足、纵深不够,没有古今成败在胸中,也没有古今许多史事来到心上,所以心量太浅,志量亦不深。加上革命太快成功,没有机会磨炼其心志,他说如果清末革命能晚两三年成功,则革命人物心量更深,对国家发展更好。清初学者方中履(1634—1698)说:“坐集千古之学,折中其间。”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说,所谓“深度”是“一把能抓住多少的东西”。没有“深度”的生活,不免陷入“贫穷文化”,王汎森的理解是:因其内心中没有生命的深度,心量不足,只能从“某刻”到“某刻”,在那一刻之外没有任何时空之关联与想象。
王汎森经常被问到,在搜索引擎这么发达的时代,许多史事都可以在网络上一查而得,为什么还要读史?王汎森认为用关键词查询是片段的,而读史是较成系统、有机的,两者都不可或缺,但也要靠人们由平常阅读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阅读者,人们应秉持一些信念,即期待从历史中重新获得意义、智慧与勇气。读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视野,一些向往,一些模糊的典型或场景,以及人生的、精神的、气氛的、态度的、品格的莫大资粮。所谓“从史中求史识”,包括人类用自己的努力,在历史的变化中找出人类发挥智慧与勇气而改变历史格局的部分。吕思勉说:“读了历史,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希望,知道有道德的人经常能够克服困难或障碍,知道腐败政治终究要垮台。当事情可以有许多选择时,应该选择符合人道及普遍价值的方向。
“历史”与“义理”像两个上方有着通孔的贮水槽,两者都要足够丰盈才可能互相灌注、互相滋养。王汎森倾向于认为在“历史”旁边的这个“义理”的贮水槽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良善、包容等道理的深刻体认。历史是一种扩大人生视野之学。人的生活有限,史书中的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个人生命与经验的局限,扩大我们的视野。历史是一种培养“长程视野”之学,而“长程视野”每每能帮助人们发现许多问题的根本症结。历史是一种乐趣之学,“乐趣”使我们不只有“生存”,还有“生活”。读史本身即是人生充实感、满足感、欢乐感的来源。
人生是一场宴席,王汎森更想这样问:“当人生的宴席结束时,我们吃了多少而去?”在历史的不同时空里,过客上下求索,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END」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