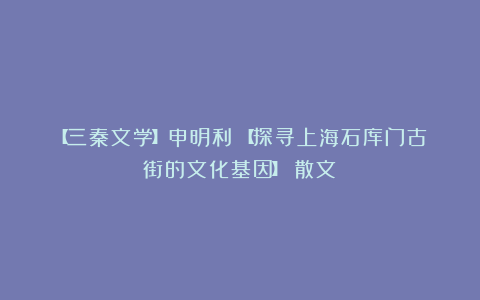|
文/申明利
序:在时光褶皱里漫步石库门,触摸石库门古朴又时尚的文化肌理,探寻石库门久远又稳定的文化基因。
晨光初醒时,我站在泰康路的弄堂口,看第一缕阳光如何被雕花的山墙裁剪成碎片。田子坊的石板路还浸着昨夜的雨润与爱意,青灰色的纹路里沉淀着上海开埠以来的几万个晨昏。
那些被脚步磨光滑的铺路石子,曾听过黄包车夫的吆喝,见过旗袍女子的纤足,如今又承托着穿帆布鞋运动鞋的旅人们匆忙的走动。
老街区的建筑外观仍保留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成为都市里的静谧存在。
入口门楼上挂着“安且吉兮”的古色古香的牌匾,底层的商铺继续赓续着石库门的繁华,唯有门牌号默默诉说着还未远去的过往。
石库门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也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符号。它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承载着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记忆与市井风情,其名称、形制与文化内涵都深深烙印着中西合璧的时代特征。
琳琅满目的时尚元素与历史建筑的融合,让一座座老宅成为“活着的文化地标”。
张爱玲在《私语》中“老洋房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的描述,正是对这一座座老建筑的鲜活注解。
老街区的呼吸带着独特匀称的韵律,是煤炉生火时的“噼啪”声,是隔壁阿婆用上海话呼唤孙儿的尾音,是咖啡馆研磨机转动时溢出的焦香,三种时态在此刻的空气里绞成细绳,牵引着我走进这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推开某扇黑漆斑驳的木门,门楣上的三角形山花突然让我想起圣三一教堂的尖顶。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语汇,正是石库门最精妙的文化隐喻。
19世纪中期,当第一批石库门在老城厢与租界的缝隙间生长时,英国建筑师将联排别墅的形制与江南民居的天井嫁接,用中国传统的青砖清水墙包裹西洋建筑的拱券结构,老虎窗的斜顶既借鉴了上海本地民居的“观音兜”,又藏着伦敦阁楼的影子。就连早期石库门的门楣,都常常融合了西式山花装饰与中式吉祥的图案。
张爱玲在上海的居所犹如她笔下交织的时空褶皱,既深植于历史肌理,又裹挟着都市摩登的气息。这些散落在城市脉络中的建筑,不仅承载着她的创作灵感,更成为解码海派文化基因的重要坐标。
它们印证了上海“在冲突中融合”的城市精神,就像常德公寓的老虎窗同时映出摩天大楼与过街楼,这些建筑在历史与现代的张力中,成为理解海派文化的密钥。
这些散落在上海街巷中的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如同张爱玲笔下的文字,在时光中沉淀出独特的韵味。当我站在常德公寓的雕花拱门前,或是坐在康定东路的老洋房里,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的生命轨迹,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在岁月长河中的悄然流淌。
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写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这些石库门建筑又何尝不是传统基因与现代文明相交融之后的文化新物种。
我的眼前,是张爱玲慵懒的站在宽阔的意大利式阳台上,沉思着不同阶层人的生活,写下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名篇。唯妙唯俏的述说着“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来去”的经典场景。
征得主人允许,我轻缓的走进还留有张爱玲影子,以肉粉色外墙与咖啡色线条勾勒出Art Deco的优雅轮廓,沿街高大的法国梧桐与古建筑历史感交织成独特的视觉诗篇的公寓。
公寓底层“千彩书坊”咖啡馆复刻了张爱玲笔下的充满哀怨与不甘韵味的文艺氛围,老钢窗、壁炉与张爱玲的作品构成时空对话。仿佛置身于张爱玲写作时,细腻、愤懑又不甘心的思绪里。
弄堂深处,一位修鞋匠正在竹椅上敲着鞋钉,他面前的木箱上放着半块“蜂花”檀香皂。这种1928年诞生于上海的国货,如今成了老物件收藏者的宠儿。
隔壁裁缝铺的缝纫机“嗒嗒”作响,老式蝴蝶牌机器上还留着1953年的出厂编号,而玻璃窗上贴着的二维码,又让这台“古董”完美融入了现代时尚的潮流。
这种时空的折叠感,在石库门的每一寸肌理中都能触摸到。雕花的门簪旁边可能嵌着智能门锁,“上海制造”标语与网红打卡的荧光贴纸共享墙面。就像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描述的:“老日子和新日子在上海的弄堂里相遇,像水和酒一样慢慢交融。”
在一家旧物商店里,我被一叠1930年代的月份牌吸引。画中穿着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倚着石库门的门框,身后是挂着竹篮的晒台,美国柯达胶卷的广告与传统的“嫦娥奔月”图案并排而立。
店主是位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他指着画中女郎的旗袍开衩处说:“看到伐?这里用的是盘扣,但裁剪是巴黎的省道工艺。那时候的上海人,最会’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的沪语谐音,意为第一)地把洋派和本土捏合到一起。”
说着,他小心翼翼从抽屉里拿出一本1947年的《良友》画报,熟练的翻开其中一页,指着宋美龄在石库门里主持慈善活动的照片,满脸傲娇,语气里全是浓烈的怀旧之情,是兴奋中的炫耀。
宋美龄身上的蕾丝旗袍领口,正绣着石库门特有的“马头墙”纹样。仔细观摩之下,我却发现,精致的旗袍,却无法掩饰宋美龄内心的绝望和愈加渺茫的希望。
这本画报,严肃里藏着俏皮,厚重里氤氲着时尚,已经是非常宝贵的文化瑰宝了。
午后的阳光斜穿过“慎余里”的过街楼,在青石板上投下密密麻麻的菱形光斑。
我跟着一群穿校服的中学生走进一座石库门民居,他们正热烈又投入的用3D扫描仪记录堂屋里的每一处细节。
屋主赵阿婆端出刚蒸好的“条头糕”,雪白的糯米团子上撒着桂花,甜香里混着她讲述的往事。
“阿拉屋里厢从前是开’老虎灶’的,就靠着门口头那口铜锅子,养活了三代人。”
她指着客堂间墙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1950年代的上海青年们在八仙桌上排练沪剧《罗汉钱》,桌上的“三五牌”台钟与墙上的“人民公社好”标语形成奇妙的呼应。
这种石库门独有的鲜活状态的文化传承,在老街区的每个角落,时刻都在发生着。
转角处的“上海剪纸”作坊里,传承人李守白正在用刻刀在红宣纸上复刻石库门的砖雕纹样,他的作品里既有传统的“梅兰竹菊”,也有戴着耳机的时尚的弄堂少女。
而隔壁的黑胶唱片店,老板正用1970年代的“上海牌”电唱机,循环播放着周璇的《夜上海》,老旧的喇叭里流淌出的歌声,与店外年轻人用手机拍摄vlog的议论声,在午后的弄堂里织成优美的合奏曲。就像历史学家熊月之所说:“上海文化的本质,是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
在一座改造为艺术空间的石库门里,我撞见一场名为“弄堂实验室”的展览。年轻艺术家将老式“万国旗”(弄堂里晾晒的衣物)转化为光影装置,用传感器让晾衣竹竿在观众靠近时发出不同年代的上海童谣。
最动人的是一组名为《七十二家房客》的互动影像,屏幕上的石库门里弄随着观众的手势变换着不同的场景。
1948年的“亭子间”里,作家巴金正在煤油灯下修改《寒夜》;1980年代的“前楼”中,一对年轻人正用“三五牌”台钟、“蝴蝶牌”缝纫机和“红灯牌”收音机组成新婚“三大件”;而2025年的“阳光房”里,一位设计师正在平板电脑上重构石库门的数字模型。
这种时空的跳跃,让我突然理解了石库门为何能成为上海的文化基因——它从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死标本,而是始终在生长的鲜活生命体。
石库门不仅是民居,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石库门那一抹最鲜艳的红色记忆,令人动容。中共一大和二大,均在石库门建筑内庄严召开。革命先驱曾在客堂间频繁的秘密集会,使石库门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最具历史魅力的鲜明地标。
今天的石库门,还是近现代文化的地标。鲁迅、巴金等文人曾居住于石库门,茅盾小说《子夜》中描绘的“弄堂生活”即以此为背景;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曾藏身石库门,推动近代思想和近代文明的传播。
黄昏时分,我在“田子坊”的弄堂里迷路了。红砖墙上的“上海手表厂”老招牌下,一位穿汉服的姑娘正在喝着“网红”咖啡,她袖口的云纹、咖啡杯上的拉花与“外滩三件套”相映成趣。
转过弯,一家老面店的玻璃柜里,本帮“辣酱面”旁边陈列着分子料理版的“阳春面”,厨师用低温慢煮的方式处理传统浇头,却依然能够保留着虾子酱油的灵魂。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和弦,正是上海老街区最迷人的变奏。
在一家名为“石库门声音博物馆”的小店,我戴上耳机,听见1920年代的留声机杂音、1950年代的公共食堂广播、1980年代的弄堂叫卖声,最后汇入2025年代的电子音乐。
店主是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设计师,他指着墙上的装置说:“你看,这是用老弄堂的’水斗’(公共水池)改造的音响,拧开水龙头,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放出不同年代的上海声音。”
这种创意不是对传统的消解,而是让老物件在新语境中焕发新生,就像新天地的石库门被改造成时尚餐厅后,那些被保留下来的砖雕依然在讲述着一百多年间发生的每一个故事。
最让我驻足的是一家“旗袍定制”工作室,老裁缝周师傅正在用传统的“滚边”工艺缝制香云纱旗袍,他的徒弟则在电脑上用3D软件模拟旗袍的立体剪裁。
工作室的展示架上,既有绣着龙凤呈祥的传统款式,也有拼接牛仔布的改良版旗袍。门口塑料模特身上的那件,领口是石库门特有的“石库门”造型,裙摆却采用了西式的鱼尾设计。
周师傅放下手中的绷架,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些骑共享单车的年轻人,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个’老上海’的情结,就像我这件时尚的唐装,里面却会穿上涤纶内衣。”
暮色渐浓时,我登上石库门褐黄色石头垒砌的晒台。远处摩天大楼正在依次点亮灯光,上海地标“三件套”的五彩轮廓,与近处弄堂里晾晒的被褥、被磨平了棱角的石晒台,形成魔幻般的对比,格外和谐的同处一框。
风从老虎窗吹进来,带着一股旧木头和樟脑丸的味道。晒台角落堆着几个旧藤箱,上面印着“上海制造”的字样,箱盖上的划痕像极了老人脸上的皱纹,让我想起了祖母那件很有年代感的老木箱。
在这里,时间不是线性的流逝,而是层层叠叠的堆积,是五彩斑斓的交织。就像石库门的砖墙,外层是新刷的涂料,内里却藏着一百多年前的砖纹。
坐在晒台边缘,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老街区里寻找“乡愁”。这种乡愁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而是对一种文化根脉的追寻。
当我在一家老相机店看到1980年代的“海鸥”相机,与最新的数码相机并排陈列时;当我在“明星咖啡馆”(1930年代上海俄侨聚集的场所)喝着拿铁,听店主讲述傅雷在此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往事时;我意识到老街区的魅力正在于这种“时空的复调”。
它让我们在岔路口多如迷宫的现代大道上狂奔中,能回头看见自己的来路,而不至于迷失了追寻的方向。就像本雅明笔下的“拱廊街”,是城市记忆的毛细血管。
离开时,我在弄堂口的“烟杂店”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店主是位会说英语的大爷,他指着烟盒上的英文“CHIENMEN”说:
“这个拼法还是1916年的老写法,就像阿拉上海,变来变去,骨子里还是有股’老克拉’(沪语,指讲究的老派上海人)的味道。”
夜色中的石库门灯笼亮了,五彩光芒映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斑斓而时尚。
恍惚间,我看见一位穿西装的先生与一位穿旗袍的女士擦肩而过,他们的对话在弄堂里回荡。一半是吴侬软语,一半是夹杂着洋泾浜英语的上海话。就像这条老街区,在历史与当下的褶皱里,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呼吸节奏。
回到家里,我立马打开笔记本,激动的敲下一句话:“上海的老街区不是历史的遗骸,而是文化的活火山。”这是我漫步石库门时,脑海里反复冒出来的最深的感悟。
当石库门的砖墙吸收了咖啡的香气,当弄堂的石板路记住了高跟鞋与运动鞋的交替节奏,当老虎窗的玻璃同时映出摩天大楼与过街楼的影子,我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巨大的韧性,和独有的同样巨大的包容性。
它懂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传承中变异,在借鉴中生存,在坚守中创新。就像那些在石库门里出生的孩子,他们既记得阿婆讲的“弄堂经”,也熟练地在手机上分享老街区的新发现,这种代际的接力,让文化的火种在时光的褶皱里代代相传。
如今的石库门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上海独特的文化图腾:从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到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石库门的青砖黛瓦、斑驳门环常被用作海派风情的视觉符号;上海方言中“弄堂”、“石库门房子”等词汇,也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石库门的本质,是近代上海“中西杂糅、新旧并存”的城市基因的物质呈现。它用江南民居的骨架,穿上了西方建筑的外衣,又在里弄生活中孕育出独特的市民文化。
从建筑形制到生活方式,从革命遗址到商业地标,“石库门”三个字承载的,不仅是一栋房子的名字,更是一部浓缩的上海史,一个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共生的东方城市寓言。
石库门门楼上的文字是一部活的历史书,传统题字承载着里弄文化、吉祥寓意与中西合璧的美学;现代招牌则记录着城市更新中的商业转型与文化创新。无论是“步高里”的中法双语门楣,还是新天地的国际化品牌标识,都共同勾勒出上海从传统到现代的多元文化元素,以及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文化面貌。
江南梅雨季节里,一个难得的雨霁天晴的清晨,我又去了一次田子坊。阳光穿过某家店铺的彩色玻璃,在地面投下细碎斑驳的光影,像极了石库门里那些新旧交织的日子。
一位老人正用毛笔在黑板上写着当日的菜单,粉笔字旁边贴着二维码,而他身上的蓝布衫,袖口已磨出了温柔的毛边。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老街区的魅力从来不在复古的滤镜里,而在它始终与生活同步呼吸的潜能里。
就像石库门砖缝里长出的野草,既扎根于历史肥沃的土壤,又向着未来的阳光生长。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成就了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申明利:陕西蒲城洛河川人,自由职业者。骨子里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浸淫着古典文学和诗词博大精深的魅力,度过了60多年的人生。平日里喜欢随心写写古体诗词、现代诗、散文、随笔、小说等。已在《中国诗刊》《当代诗刊》《三秦文学》《华山文学》《三贤文苑》《乾陵文苑》《北方文学艺术》等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诗作、散文、小说数百首(篇)。
三秦宗旨:营造一片文学爱好者的乐土,共创文学梦想的家园!
文学总顾问:鹏 鸣
平台总顾问:边士刚
法律顾问:李木子
顾问:白忠德、邓汉章、罗旭初、束宝荣、史 波、孙德科
策划:李书忠
宣传推广:鼎 文、王宝群、孙传志、袁胜民
平台主播:梦锁清秋、英子、王迎旭、慧 质、晓 锋
总编:鱼儿姐姐、徐萱波
主编:谢亚红、初阳、谭文群
编委:刘旭平、唐桂英、吴远红、张晓强、刘马陵、梦而诗、喝 茶、南友锋、马永清、张兴军、吴风平、张巧莉 、秦岭人家、秋日私语、徵 蔚、党月琴、刘军英、米兰花、陈祖金、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