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蒙克|艺术家和他的模型 1919-1921
我的色彩:血与火的挣扎
我,爱德华·蒙克,在此刻的静寂里,感知着生命的潮汐正缓缓退却。然而,意识深处那长久灼烧的火焰,从未熄灭过。我眼前浮现起童年那间被死亡气息弥漫的房间——母亲离去时,她苍白面容上最后一丝气息飘散,如同最微弱却最深刻的一缕刻痕,永远烙在了我灵魂的底板上;而姐姐索菲亚,像一朵初绽即被寒霜扼杀的花,她的枯萎是缓慢而清晰的酷刑,在病榻之上,她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像针扎入我幼小的身体。
父亲在角落里近乎狂热的祈祷,他的无助与绝望如浓雾般弥漫,那声音渗进墙壁,渗入我的骨血,成了我生命中永不消散的蓝色阴影。死亡,竟如此早地成了我生命里最熟稔的邻居。
后来,我拿起画笔。那并非为了描摹窗外的阳光或欢颜,而是为了将心中日夜燃烧的痛楚倾泄出来。我涂抹着颜料,在画布上反复刮擦、覆盖,如同在反复撕开难以愈合的伤口。当《病孩》诞生时,我仿佛看见索菲亚在画布上重新微弱地呼吸,她苍白的面容在病榻上挣扎着,又渐渐沉寂。颜料层层叠叠的堆积,恰如那一次次希望与绝望的反复煎熬,那模糊的轮廓与病态的色调,正是我心中无法愈合的创口在向外流淌。有人斥责我的笔触粗砺、色彩刺目,可他们怎会懂得?我画布上流淌的并非油彩,分明是我心中难以抑制涌出的血啊!
我独行于峡湾边的小路,那是1892年一个黄昏。暮色四合,天空仿佛被无形之手撕裂,骤然燃起一片令人窒息的猩红,云霞如鲜血般翻涌,又似地狱之火在燃烧、在蔓延,似乎要将整个世界吞噬殆尽。脚下的路蜿蜒扭曲,桥栏仿佛也在熔岩般的天空下挣扎变形。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对虚无深渊的惊骇,令我浑身颤抖。我紧紧按住头颅,仿佛只有如此才能阻止颅内的尖叫炸裂开来。
于是,《呐喊》诞生了——那个立于扭曲世界中心、惊骇到溶解了面目的灵魂,正是我自己在宇宙深渊前战栗的永恒倒影。我画出了那种绝望的声波,那无声的尖啸,足以撕裂每一个面对它的人的神经。这幅画,是我从灵魂最黑暗的深渊里掏出来的、仍在悸动的恐惧之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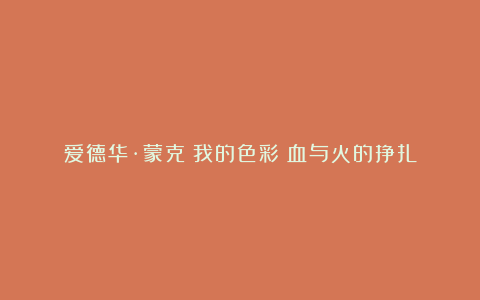
我穿梭于柏林、巴黎、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旧称)的街道,如同一具承载着家族诅咒的容器。酒馆的喧嚣、烟雾缭绕中模糊的面孔、情爱纠缠后更深的空洞……这一切不过是徒劳的麻醉剂。我最终被投入疗养院,那里刺眼的白色墙壁,映照着《病房中的死亡》中那冰凉的床榻、沉默的亲人、凝固的悲伤——那是童年鬼影的又一次回归。
我惊觉,这缠绕我一生、几乎将我碾碎的痛苦与恐惧,竟是我唯一真正拥有的真实。我的画布,正是我与这宿命般苦痛搏斗的战场,每一笔扭曲的线条,每一抹刺目的色彩,都是灵魂深处无声的嘶吼,是生命在重压下爆裂开来的印记。
此刻,生命渐渐流逝,像水从指缝间无可挽回地消逝。我的目光再次投向那角落——画架安静地伫立着,仿佛已等待了千年。空白的画布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一种邀请般的微光。那纯净的空白,竟如同深渊,又似救赎的入口。我心中残存的火焰,微弱却固执地跳跃了一下:倘若还有一丝力气,我定要再次拿起画笔!即使那画布上最终只留下一道痉挛的笔触,一抹绝望的色彩,那也是我——爱德华·蒙克,存在过、挣扎过、燃烧过最确凿的证据。
颜料与血,都是生命。我用伤痕蘸着颜料涂抹,灵魂里的烈火与鲜血,终究凝成了画布上那永不褪色的、痛楚的蓝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