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第三极牧民》海报
《第三极牧民》中的冈仁波齐
剧照
在阿里拍摄的花絮
十一岁之前,我生活在大渡河上游源头的一个小小牧村,那里封存着我整个童年的世界。在记忆深处,人与牛马羊、人与自然之间,始终牵系着一种无形的信号。这信号藏在长短错落的口哨里,躲在舌腭相击的声响中,融在悠扬绵长的牧歌内,也飘在鹰笛、竖笛与六弦琴的旋律间。
剧照
正是凭借这些独特的信号,人与自然、与牲畜之间得以顺畅传递万千讯息。这份记忆在我二十岁后依旧清晰,驱使着我迫切想要探寻信号背后藏着的生命真谛——它与牧羊人历经的狩猎时代、野生动物驯养阶段、游牧阶段紧密相连,可古籍中对此的记载却寥寥无几。我想,这大抵与’牧野之能,纵精不过末节;圣贤之道,虽拙方是根本’的传统价值观密不可分。
剧照
为了这份探寻,我花了六年时间,往返于亚洲八大河流之源头——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亦作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冈底斯山,以及黄河、长江、扎曲河与澜沧江的源头。更重要的是,每次我都会用一个月时间,深度融入这些河流源头的牧人生活,悉心研究、记录并拍摄那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牲畜的无形信号。这段历程中,我写下两本书,2025年6月底至8月间,便以这两本书为基础,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拍摄牧民中
说实话,我虽热爱摄影摄像,却毫无相机操作的专业基础。2021年,我从色达离家,开启了五个月的旅程,除了那曲南北部,我走遍了藏地几乎所有村落。当时买的一部索尼相机,今年四月因筹措摄像设备资金,不得不折价卖回给原店。看着相机的光圈、快门等设置悉数恢复出厂状态,唯有库存里那上万张照片还留存着我的足迹,心中百感交集。这些照片曾收获不少赞誉,网上常有相识或陌生的人问我是不是专业摄影师,尤其有人说许多女孩喜欢我的作品时,我虽会暗自得意’拍得确实不错’,却也始终坚信:摄影师若没有敏锐的审美眼光,单靠技术绝拍不出好作品。
门驶拍摄中
今年耗时五十七天拍摄完成的,是这部纪录片的上部。按地域划分亦属’上部’——聚焦于冈底斯山四方四大河流源头牧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狩猎、中期驯养野生动物、晚期游牧。影片以岩画、壁画为历史佐证,结合当下牧人的真实生活展开叙事,完整记录了当地牧人一天的生活轨迹。
在桑耶寺拍摄壁画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以为我是开着车、带着设备齐全的摄制组上路的——但事实远超出你的想象。过去六年,我的旅行方式从未改变:徒步行走为主,偶尔招手搭车,累计搭车行过三千多公里。我并非要向你诉说旅途的艰辛,只是这段经历本就这般模样。我一人身兼数职:摄影师、导演、录音师、设备搬运工,所有工作全由自己承担。六年下来,早已习以为常,并未觉得格外艰难。
搭车过程中的悠闲
以冈底斯山为中心,可分为南北两麓。南麓多为农区,山谷纵横,古迹古寺密布,因此游客与历史研究者大多云集于此,北麓却鲜有人至——这里是纯粹的牧区。六年间,我往返北麓的牧村六次,心中早已积攒了无数镜头下的故事。在我看来,人与牲畜、与蚂蚁、与岩羊等野生动物,乃至与整个自然界之间的信号,既关乎语言学的符号传递,又牵涉音乐学的韵律表达。可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相关论文,即便向语言学、音乐学的专家请教,他们也多是含糊其辞地说’大概就是这样’。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也正因如此,我觉得所有艰辛都值得——我得以记录下许多老者口中世代相传的传说与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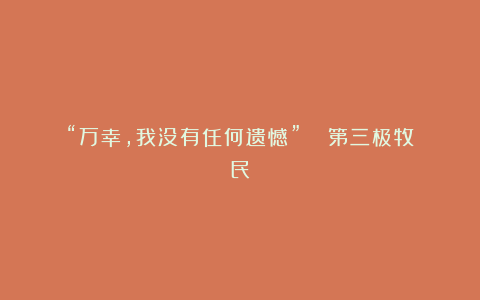
门驶在阿里牧区
许多官方记者和私人采访者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这样行走,路上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吧?’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一个人反复经历的事,久而久之便会归于平常;而平生从未遭遇的事,一旦突然降临,往往会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一天只吃一顿饭、半天搭不到车只能步行、夜晚睡在牧人的牛圈里——这些在六年中反复发生的事,如今对我而言已稀松平常。但确实有一件事刻入骨髓,那是一场险些让我丧命的车祸。
在阿里
那天,我在狮泉河与象泉河上游拍完素材,搭车前往孔雀河源头。路边有几辆车停靠休息,一位汉族大哥同意让我搭车。谁知车辆因严重超速失控,翻滚着坠入路边深沟。那一刻我完全懵了,毫无反应。片刻后,耳边只剩嗡嗡轰鸣,检查全身竟无大碍。我下车坐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回望半生:这些年始终专心做着自己热爱的事,即便未有像样的成果,万幸,也毫无遗憾。唯一的牵挂,是书尚未正式出版,纪录片也只完成了上部。至于精心赡养的父母兄弟,明知终将因时光流逝而分离,那一刻竟未涌上心头。过了许久,母亲的身影才悄然浮现,耳边依旧嗡嗡作响。万幸的是,司机大哥也安然无恙。那天下午,阳光依旧洒满雪宝顶前的村庄与牧场,许多车辆陆续停下,人们探出头询问伤情、提供帮助。
门驶在冈仁波齐前
五十七天的拍摄结束后,我直奔拉萨寻找剪辑师。联系了多人后,最终与岗坚央措老师一见如故——这是他第一次剪辑纪录片,而我也是生平第一次手持摄像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与岗坚央措老师约定的剪辑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半就完成了进度。我提出请他吃饭,他欣然应允。席间我们谈及,要是万玛才旦老师还在,一定要请他第一个看这部片子。
与岗坚央措老师编辑中
我给岗坚央措老师的两万元剪辑费,是成都’阿热藏餐’的阿热姐借给我的。起初我想向她借一万,再向他人借一万,她却直接说:‘要是一万不够,这两万你都拿去。我知道你孤身一人做音乐研究不容易。’这番话让我热泪盈眶,即便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未曾如此体谅我的内心。这让我想起了成都的几位老师。
初到成都时,以古嘉·慈诚老师为首的一群前辈给予了我诸多关照。他们中有收藏家、文物研究者,也有商人,我一到成都就爱往他们那里跑,总能收获满满。拜访仓旺老师、成林老师、喇嘛扎西时,我学会了文物鉴定、典籍研读的方法,甚至从他们店内的物品陈列中都能汲取知识;在耷·琼培师傅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文物造型、图案象征意义的新奇见解,他画的’山川源流归大海’,在我登上阿里南麓的山峰时,屡屡清晰浮现在脑海;宗智老师则教会了不善言辞的我如何与各界人士沟通交流。我虽因性格使然,与他们相处时话不多,心中却始终充满敬意与感激。去索南老师家做客时,我们常聊古代译师、各国风情、文物分类鉴别,常常一聊就到深夜十二点。
门驶和古嘉·慈诚老师
如今,每当我扪心自问,都深知这部片子远算不上我六年研究的所谓’成果’,但它却无疑是这段旅程最真切的记录。至于何为’成果’,我至今未能找到确切答案,未来能否寻得也未可知。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不断地寻找、寻找、再寻找!这份追寻本身,不正是这个问题赠予我的、比答案更珍贵的诱惑吗?循着这份诱惑,在纪录片开拍后的第一百四十余日,也就是2025年10月26日,我于拉萨,仅凭朦胧记忆草草记下这些流转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