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双壁岩下的时光
——湘西古道上的山水清音
文/杨志军
“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
——唐·王维《青溪》
晨雾,似一匹被母亲河平溪江的溪水浸软的素帛,懒洋洋铺在江面上。江风一吹,帛衣便微微漾动,把对岸那两座石壁罩得愈发朦胧——打小就在这江边摸爬滚打,老双壁岩的影子,是刻在我童年窗棂上的画。它们就那样静立着,像从鸿蒙之初就守着洞口塘的老人,岩脊上流淌的薄雾,是还没拭去的睡意,又像外婆画鞋样时没干的墨,浓淡相宜,晕染出几分我们洞口人都懂的亲切禅意。这便是方以智笔下“石壁未经人一语”的双壁岩,但我们不叫它“双壁岩”,更爱喊“双岩”,像喊邻家大伯似的。它们面对面站着,中间只留一道窄窄的缝,漏下一线天光。
我的脚步声落在青石板路上,“咚、咚”的响,在岩壁间撞出空空的回响,又被雾霭温柔接住。这是湘黔古道的起点。每一级石磴都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像爷爷盘了一辈子的旱烟杆,带着沉淀下来的暖意。凹陷处积着昨夜的雨水,浅浅一汪,倒映着天上碎裂的云影。我俯身,指尖轻轻抚过石面,那石面光滑如镜,竟没有一丝石头的冷硬。指尖传来的,是熟悉的温热——那是马帮汉子的汗,顺着黝黑脊梁滑下,滴在石板上,蒸发出盐粒的结晶;是挑盐客的喘息,混着山间雾气,凝在石缝里,成了岁月的露珠。
一
转过一道山弯,景致陡然精致起来,像外婆绣的手帕,每一针都透着灵秀。岩钵井就藏在这山弯里,我们洞口人都说,这井的水是“仙水”。井水澄澈得让人心尖发颤,井底卵石上的纹路弯弯曲曲,是水流千万年的抚摸,是时光刻下的指纹。小时候跟着外婆来挑水,外婆总说“慢着点,别惊了井里的仙”。我伸出手,掬一捧井水,凉意顺着掌纹丝丝渗入肌肤,带着一股山涧特有的清冽,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那是山里楠竹的气息,是我们洞口山水最本真的味道。
井边立着一棵老杨梅树,枝头结着青涩的果子,小小的,藏在嫩绿的叶子间。细碎的阳光透过枝叶,投下斑驳的影子,落在井面上,随水波轻轻晃动,像古人在绢帛上点染的苔痕,淡而有味。
再往前,实心桥便静卧在水面上。我们洞口人都叫它“老石桥”。小时候最爱在桥上捉鱼,盯着水里的小鱼发呆。那些寸许长的小鱼,脊背半透明,静立时,便与身下的卵石融为一体;可一旦动起来,尾鳍轻轻一摆,便划出一道转瞬即逝的银亮弧线,像爷爷写毛笔字时笔尖留下的一抹飞白。
最堪玩味的,莫过于“一线天”了。两堵百尺来高的石壁紧紧偎在一起,中间只留尺余宽的间隙。正午时分,天光从岩顶的缝隙里漏下来,被过滤成温润的翡翠色,斜斜铺在岩壁上,照出岩纹的万千走向。爷爷说,那些酷似文字的裂纹,是仓颉造字时不小心散落的笔划。它们与岩壁上古人题咏的残痕相映成趣。每当此时,我便仿佛能听见千百年前,笔墨落在石上的轻响,那声音清越而悠远,穿过时光的隧道,至今仍在这缝隙间回荡。
二
行至水穷,坐看云起。立于四清坝上远眺,景致陡然大变,刚才的精致灵秀被一片苍茫取代。坝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用青石垒成的,石缝里钻出几丛倔强的灌木,枝桠虬曲,就像我们洞口人的性子,坚韧又乐观。湖水在这里揽成一汪深潭,颜色比下游沉郁了许多。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箔,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对岸的晒霜石泛着淡淡的银白,石上的纹路纵横交错,如焦墨干擦而成,遒劲苍老,像爷爷脸上的皱纹。更远处,“四十八弯”山路像一条失却了色彩的丝带,在黛青色的山间时隐时现。
正看得出神,一阵清越的声响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是同村的王大爷赶着黄牛从坝上走过。牛蹄叩击着青石板路面,发出“笃、笃、笃”的清响,与坝底传来的低沉水声交织在一起,谱成一曲原始而古朴的韵律。他不吆喝,只用手中的竹枝轻轻一点牛的脊背,牛群便温顺地沿着山路蜿蜒而去。最后一头老牛走过时,还回头望了望这坝,望了望这潭水,仿佛也在留恋这山水间的宁静。
坝下的水边,棣谷坪上生着一大片芦苇,青郁郁地立着。风一吹,芦苇便轻轻摇曳,俯仰之间,发出“沙沙沙”的絮语,那声音比松涛更柔软,更细腻,也更贴近土地的呼吸。偶有几只白鹭从芦苇丛中惊起,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短暂地划破了山谷的静谧。可没过多久,山谷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那种宁静比之前更甚,更温柔。
三
循着水声与记忆的指引,仙人洞便藏在一片苍翠之中。洞口的石壁上,兰陵碑志静默地立着,我们洞口人都叫它“老碑”。碑文早已被风雨蚀刻得斑驳不清,只有“光绪七年”四个大字还顽强地透着时间的印记。
我伸出手,指腹轻轻抚过碑上模糊的刻痕。就在指尖触到石碑的那一刻,方以智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夜窥翡翠屏前镜,诗写桃源洞里天”。遥想这位明末学者当年立于此处,眼前该也是这般“鸡犬无声炉尽灭”的幽邃吧?那时的他,心中该有怎样的感慨?或许,只有这沉默的石壁,这流淌的平溪江水,才能读懂他心中的万千思绪。
这山谷,俨然是时光的叠影。税门前的石阶上,散落着几块货栈的柱础,上面还留着当年雕刻的花纹。一块青石板上,一个深深的蹄印里生着一丛嫩绿的苔藓,柔软与坚硬、新生与古老在此达成了最完美的和解。衙门口的断墙边,几株野菊花开得正热烈,黄色的花瓣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在秋风中摇曳。
激战坡的空地上,我拾起一块沉黑的石头,指尖摩挲着上面深凹的斫痕。爷爷说,当年太平军曾在此与清军鏖战。而今,所有的嘶喊都已沉入潭底,所有的热血都已凝固成岩。站在这里,仿佛还能触到金戈铁马的余温,可转眼望去,只有青山依旧,绿水长流。
黄昏的山谷最易令人恍惚。夕阳慢慢西沉,把双壁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坐在古桥亭里,闭上眼睛,能听见万物的细微声响:岩缝里,蟋蟀在吟哦;树枝上,落叶在旋舞轻叹;远方的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带着柴火的噼啪声和米饭的温香。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四
当地人说,洞口塘的月夜极美。这次回来,特意留到农历十五。夜幕降临,山谷渐渐安静下来。月亮慢慢从双壁岩的顶端攀升而出,悬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洒下清辉。
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整个山谷都变了模样。青黑的岩壁泛着清冷的辉光,真如方以智笔下的“翡翠屏前镜”。潭中的月影被水波轻轻揉碎,化作万千片银箔,在水面上跳跃、闪烁。那些沉睡的古老传说,似乎都在此刻苏醒了。
“猴牯石”的投影最是称奇。月光下,它把影子投映到对岸的石壁上,那影子竟比本体更灵动,更有魂。月移影动,影子的表情也在不断流转:一开始,是沉郁的冥思;过了一会儿,是无言的悲戚;又过了片刻,是片刻的欢愉;最后,它又恢复了平静,眼神澄澈而安宁。那影子,仿佛在用光与影上演着一部被遗忘的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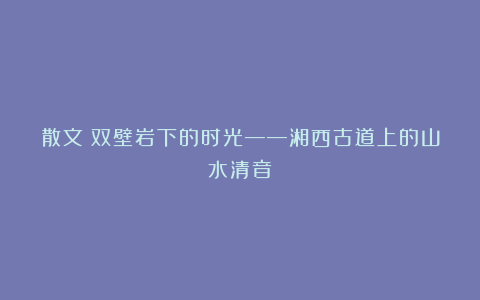
此情此景,方以智“丹青难与世人传”的叹息,化作满谷的月光与水声,悄然渗入肺腑。 再高明的画笔,也留不住这水月交辉的刹那;再灵秀的诗句,也载不动这岩壁与光影的缄默对话。或许,唯有像我们洞口人这样,生于斯长于斯,把根扎在这山水间,才能窃听到时间那深不可测的密语。
启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潭边已有了少年的身影。他们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脊背在晨光下闪烁着健康的生命光泽。他们笑着,闹着,纵身跃入水中,“扑通、扑通”的声音打破了山谷的宁静。少年们在水中嬉戏、追逐,笑声清脆而响亮,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唤醒了沉睡的山谷,也唤醒了新的一天。
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的身影,心中满是眷恋。平溪江的水依旧潺潺流淌着,奔赴它的远方。双壁岩依旧默然地站着,将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记忆,都压进岩层的深深皱褶里。
我轻轻挥了挥手,不是告别,是与家乡的山水打个招呼。转身踏上青石板路,脚步声再次在岩壁间回响。我知道,我带走的,不仅是山水的记忆,更是时光的馈赠——那些藏在岩纹褶皱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我心里的外婆、爷爷的模样,都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皱褶,成为我作为洞口人,永远的根。
双壁岩记
时光在此对折,
岩壁是厚重的封面。
平溪江的水流,
将千年故事,订成绵长的册页。
青石板上,马蹄声碎,
是祖父的旱烟杆,磕出的星火明灭。
井中云影,桥下飞白,
是外婆的绣花针,穿起的童谣清澈。
月光如水,淘洗着古老的碑文,
将金戈铁马,浸透成温柔的霜雪。
那猴牯石的影子,是徘徊的诗人,
用光与影,写一首无法寄出的诀别。
而少年纵身一跃,
跃入的,是另一道时光的皱褶。
他们用身体,砸开宁静的镜面,
让新的故事,在古老的岩层里,
生根,蔓延。
当我转身,脚步声在岩壁间回响——
我不是过客,我是一粒被故乡
深深按进,它指纹里的,
温热的石屑。
【作者简介】杨志军,湖南邵阳人,1996年参加工作,现供职于广东一上市大型公司,机械制造工艺与设计方向高级工程师职称,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曾代表公司参编过高职院校《机械制造工艺基础》教材。文学书法热爱者,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邵阳日报、湖南文学、武冈作家、武冈文艺、乡土文学、麦溪文艺、雪峰文艺等媒体,作品多次被中国作家网重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