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若传》:最惹人心疼的女人
文/鼎客thinker
《范若若传·卷一·儋州春》
一
儋州的春日总是来得早。当京都的贵人们还在议论倒春寒时,南海之滨的药圃已然铺开一望无际的新绿。晨雾未散,七岁的范闲便牵着五岁的若若穿过回廊。青石板沁着露水,若若的小绣鞋踏上去,发出’嗒嗒’的轻响,像一串散落的玉珠。她总要走两步跑三步才能跟上兄长的步伐,发髻上系着的银铃随着动作摇晃,在寂静的晨光里荡出细碎的音符。
‘慢些,哥哥慢些。’若若喘着气,小手攥紧了范闲的衣角。那布料是老夫人用澹州特产的青麻所制,经年累月洗得发白,此刻沾了晨露,摸起来像一片湿润的树叶。范闲闻言驻足,转身时带起一阵微风,将药圃里初醒的草木气息拂到若若脸上。她仰起头,看见阳光正穿过哥哥肩头那株老梨树的枝桠,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药圃的木栅门’吱呀’一声推开,惊起几只彩蝶。范闲熟门熟路地拨开那些疯长的忍冬藤,露出藏在深处的苗床。若若蹲在他身旁,看阳光透过哥哥的指缝,在泥土上画出跳动的光斑。他采药的动作很特别,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捻,茎秆便齐根断开,断口处渗出清亮的汁液,沾在他指尖,像凝固的琥珀。
‘这是黄柏。’范闲将一截树皮放在若若掌心,’味苦性寒,能泻火解毒。’若若好奇地舔了舔,立即皱起整张小脸。范闲轻笑出声,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展开是几颗蜜渍梅子。酸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时,若若忽然发现哥哥的手腕内侧有道浅浅的疤痕,像月牙的阴影。
‘去年试药时留的。’范闲漫不经心地拉下袖子,’所以若若要记住,苦的药未必不好,甜的东西……也未必都无害。’他说这话时眼神飘向远方,越过药圃的篱笆,落在更远处的海平面上。若若不懂其中深意,却把这句话连同他腕上的疤痕,都刻进了记忆里。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日头渐高,药圃里的蒸汽氤氲上升,将两人的身影晕染得模糊。范闲教她辨认夏枯草与益母草的分别,教她用手指丈量黄芩该留几寸根须。他的声音低而稳,混着海浪的节拍,像一首永不完结的催眠曲。若若抱着膝盖坐在田垄上,看蚂蚁列队爬过自己的绣鞋,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某个晌午,她在书房外听见老夫人与管家的对话。
‘……京都来信催了三次,总不能让若若小姐一直养在乡下。’
‘那孩子身子弱,经不起舟车劳顿。’
‘可老爷说……’
若若贴着雕花门扇,漆木的凉意渗入脸颊。她看见自己的影子斜斜投在青砖地上,那么小,那么薄,仿佛一缕随时会散的烟。当晚她发起了高热,梦里全是破碎的画面:海浪变成巨兽,药圃燃起大火,而范闲的背影始终在前方,任她怎么追赶都不回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病愈后的第三个清晨,若若被奶娘早早唤醒。妆台上摆着新裁的衣裳,海棠红的料子刺得眼睛发疼。她赤脚跑到范闲的院子,看见他正在石臼里捣着什么,晨露打湿了他的鬓发。
‘要走了?’范闲头也不抬地问。石杵与臼底摩擦的声音又沉又闷,像远处酝酿的雷声。若若盯着他泛白的指节,突然发现哥哥的睫毛在阳光下是浅褐色的,像蝉翼般透明。
一只青瓷小瓶被推到面前。瓶身还带着体温,釉面下藏着细密的冰裂纹,对着光看时,仿佛有星河在瓶内流动。’装了醒神的药丸。’范闲终于抬头,嘴角挂着惯常的笑,眼底却像结冰的湖面,’路上若头晕,含一粒。’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离别那日的雾气浓得化不开。码头的木板在脚下’咯吱’作响,咸腥的海风裹着渔歌飘来。若若攥紧瓷瓶,感觉到瓶底刻着细小的纹路——后来她在摇晃的马车里就着月光细看,才发现是朵五瓣梅花,与范闲书房窗纸上常剪的窗花一模一样。
马车启动的瞬间,若若突然挣脱奶娘的手。她跑得那么急,海棠红的裙裾扫过潮湿的礁石,银铃的声响惊起一群海鸟。雾中的范闲似乎叹了口气,伸手按在她发顶,力道比平日重三分。
‘京都的蜜饯铺子在朱雀大街转角,别贪嘴。’他弯腰替她系紧披风带子,呼吸间的白雾拂过她冻红的耳尖,’每月初七,等着收信。’
车帘落下时,一滴泪砸在瓷瓶上。若若用袖子拼命擦拭,却怎么也擦不净那些突然决堤的泪水。她不知道,此刻码头边的范闲正望着马车消失的方向,手里捏着片刚摘的忍冬叶,叶缘已被掐出深绿的汁液。
马车驶上官道,沿途的野蔷薇开得正好。若若把瓷瓶贴在胸口,数着车轮碾过青石的声响。瓶中药丸随车身摇晃,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像儋州雨季时,雨滴落在药圃瓦盆里的动静。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范若若传·卷二·京都秋》
一
京都的秋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那日若若正在西厢房整理这些年与范闲往来的书信,忽闻庭院里传来一阵异样的喧哗。她手中狼毫一顿,墨汁在宣纸上洇开一朵乌云。十年了,每月初七收信的日子雷打不动,可这个秋天连着三封信都迟了。窗外的银杏叶扑簌簌落着,像无数封未能寄达的信笺。
‘小姐!大少爷回来了!’丫鬟的声音带着颤,像是怕惊醒了什么。
若若的绣鞋踩过满地黄叶,鞋尖沾着两片金箔似的叶子。穿过三道月洞门时,她下意识摸了摸藏在袖中的青瓷小瓶——瓶中药丸早已用完,如今装着南海商人带来的龙脑香,是她照着范闲信中所教配的。朱漆大门前,管家仆役跪了一地,她却在台阶下生生刹住脚步。
那个披着墨狐大氅的背影转过身来,十七岁的范闲眉骨上多了道浅疤,笑起来时眼角堆起的细纹里藏着若若读不懂的风霜。他身后跟着个抱剑的冷面侍卫,剑鞘上还沾着未化的雪粒。
‘小若若。’他这样唤她,声音比信纸上工整的字迹要沙哑得多。
若若屈膝行礼,发间玉簪的流苏晃出细碎的光影。起身时她奉上那个摩挲得发亮的瓷瓶,釉面映着秋阳,像捧着一汪凝固的泉水。范闲接过时,她闻到他指尖的铁锈味——不是血,是北地风雪淬炼过的寒意。
‘长大了。’他手掌落在她发顶的力道,与十年前码头分别时一模一样。但若若藏在袖中的手指突然蜷缩起来,她惊觉自己竟要微微仰头才能看清哥哥的眼睛了。那双眼不再像儋州的海,倒像京都深夜的护城河,表面平静,深处却沉着太多东西。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范府的秋天突然热闹起来。每天寅时,若若就能听见东厢房传来规律的叩击声——那是范闲在案前批阅文书的声响。她悄悄数过,每次都是轻叩三下,像是某种暗号。某夜她提着羊角灯去送安神汤,透过雕花窗棂,看见烛火将他的侧影投在宣纸屏风上,像皮影戏里孤独的剪影。
‘进来吧。’他没抬头,笔锋在奏折上划出凌厉的弧度。
若若发现案头镇纸下压着张药方,字迹狂放不羁,与每月家信中工整的楷书判若两人。她目光扫过’朱砂”雄黄’的字样,心头突地一跳。范闲突然用笔杆轻敲她手腕:’太医署的考题?’
‘我……我照着哥哥信里教的,认全了《本草经》里的三百味药。’若若将食盒里的青瓷盏取出,汤药表面浮着几粒枸杞,像雪地里散落的红宝石。
范闲笑了。这个笑容终于让若若找到几分儋州那个少年的影子。他端起药盏时,袖口滑落,露出手腕上缠着的绷带。若若瞳孔微缩,那绷带边缘隐约渗着淡青色——是中了’碧蚕毒’才会有的症状。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重阳节那日,范府设宴。若若穿着新裁的藕荷色襦裙,发间只簪了支素银步摇。她在回廊拐角处撞见范闲与二皇子密谈,两人站在一株将谢的木樨树下,细碎的花瓣落满肩头。
‘……北齐使团三日后抵京。’二皇子的玉扳指在掌心转得飞快,’那个司理理……’
范闲突然抬眼,目光越过皇子肩头直刺若若藏身的廊柱。她慌忙后退,绣鞋踩断一根枯枝。清脆的’咔嚓’声里,她看见哥哥眼底闪过刀锋般的冷光,又在认出她的瞬间化作春水。
‘若若来。’他招手时袖中落出个油纸包,’儋州带来的龙眼干。’
纸包还带着体温,若若捧着它,听见自己心跳声大得吓人。范闲的指尖在她掌心短暂停留,有薄茧,粗糙得不像读书人的手。二皇子意味深长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忽然笑道:’范小姐可知,你兄长在边关有个绰号叫……’
‘殿下。’范闲截断话头的声音很轻,却让满树残花都颤了颤。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宫变来得比预报初雪的云层还快。那夜若若正在誊抄《千金方》,忽闻皇城方向传来沉闷的钟声——不是报时的清越,而是丧钟般的长鸣。她推开窗,看见东南角腾起的火光将乌云染成血色。
范闲闯进闺房时带着浓重的硝烟味。他往若若怀里塞了把轻鸿剑,剑柄上缠着的青丝绳还是她去年端午编的。’呆在地窖里。’他语速极快,手指在她腕间一触即离,’除非听见三长两短的竹哨声。’
若若却抓住了他的袖角。布料上沾着种特殊的腥气,不是血,是御书房特有的金墨混着硝石的味道。’哥哥要去勤政殿。’这不是疑问句。她看着范闲骤然紧缩的瞳孔,突然明白了那些药方、绷带和深夜密谈的意义。
当范闲的身影消失在火光中,若若摸了摸发间的银簪——空心簪身里藏着按他信中方法提炼的’回魂散’。她提起裙摆奔向马厩的动作,比任何闺秀都要敏捷。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
皇城的混乱像幅被泼墨的工笔画。若若躲在运水车的暗格里,听见叛军的铁靴踏过青石板的声响。她数着心跳摸到偏殿时,正看见一道寒光袭向范闲后背!
轻鸿剑出鞘的龙吟惊飞了檐下栖鸟。若若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的血肉被刺穿时,会发出类似熟透西瓜破裂的闷响。箭头没入她左肩的瞬间并不疼,只觉一阵刺骨的凉,接着才有温热的液体浸透衣衫。
‘胡闹!’范闲接住她踉跄的身子,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山谷传来。若若看见他眼底炸开的血丝,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她在信里问边关的月亮是否和儋州一样圆。范闲回信说,朔月时分的戈壁滩上,狼的眼睛就是月亮。
此刻他眼中的血丝,比戈壁的狼瞳还要骇人。
‘《黄帝内经》有云……’若若疼得吸气,却固执地拽住范闲的衣领,’怒伤肝,哥哥……别生气……’有温热的液体滴在她脸上,不知是范闲的汗还是泪。视线模糊前,她看见那个总跟在哥哥身后的冷面侍卫终于赶到,剑锋上淋漓的血迹在火光中泛着诡异的蓝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
若若在满室药香中醒来时,窗外正在下那年第一场雪。肩头的伤被处理得极好,用的正是范闲信中提过的’金疮药方’。枕边放着她的青瓷小瓶,瓶中新装了药丸,闻着有雪山灵芝的苦香。
‘小姐昏睡时,大少爷天天来扎针。’丫鬟捧着药碗轻声道,’有次奴婢看见,他握着您的手在哭……’
若若望向窗外。雪地里新鲜的脚印延伸向东厢房,每个脚印间隔都分毫不差——那是范闲独有的步调。她突然笑起来,笑着笑着便有泪珠滚落,砸在瓷瓶上发出轻响。瓶底那朵梅花沾了血,反倒愈发鲜艳,像雪地里绽放的红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范若若传·卷三·烛泪笺》
一
腊月二十三,祭灶的糖瓜香气飘满范府。若若在书房整理医案,窗纸上映着斑驳的竹影。她手中狼毫突然一顿——案头那本《伤寒杂病论》里夹着张陌生药方,字迹潦草如狂风过境,却在’雪上一枝蒿’这味药旁画了朵精巧的梅花。这是范闲独有的标记,意味着’剧毒慎用’。
‘小姐,大少爷进宫面圣去了。’丫鬟捧着新剪的窗花进来,’说是北齐使团递了国书。’
若若指尖抚过那朵墨梅。自从宫变那夜替范闲挡箭后,她发现府里突然多了许多生面孔的侍卫,他们走路时像猫儿般无声,腰间却都别着太医署特制的银针囊。最奇怪的是范闲的书信又开始准时了,每月初七,总能在晨露未干时收到盖着北境火漆的信笺。
‘备笔墨。’若若突然说。她展开一张洒金薛涛笺,墨锭在砚台里磨了整整三圈半——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十年间积攒的情愫在笔尖凝成墨滴,最终落在纸上的却是工整如药方般的字句:’见字如晤。闻兄近日……’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信送出七日后,范闲踏雪而归。若若在暖阁里煮茶,看他在廊下抖落大氅上的雪粒,动作间露出腰间新佩的羊脂玉牌——北齐皇室才用的形制。茶釜中的泉水第二次泛起蟹眼泡时,他终于推门而入,带进一缕松针味的寒气。
‘若若的字愈发好了。’他从袖中取出那封信,纸页平整如新,唯有边角处细微的褶皱透露曾被反复展阅的痕迹,’只是……’
铜壶里的水突然剧烈沸腾,白雾模糊了若若的视线。她看见范闲的手指在信笺某处摩挲,正是写着’夜读《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的那一行。水雾散去时,案上多了支白玉簪,簪头雕着并蒂莲,花心嵌着粒罕见的血珀。
‘本打算送人的。’范闲声音很轻,像在说给窗外的雪听,’如今……’
若若注视着簪尖折射的光斑在宣纸上游移。她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范闲信中描述北境有种冰蝴蝶,翅膀薄如蝉翼,遇暖即化。此刻她胸腔里扑腾的东西,大抵就是那只永远飞不进春天的蝴蝶。
‘哥哥是要娶嫂嫂了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出奇平静,像在讨论明日天气。
烛花’啪’地爆响。范闲的影子在墙上剧烈摇晃了一下。他嘴唇开合几次,最终只吐出个’嗯’字,尾音沉得坠地。屋外风雪渐急,有枝丫折断的脆响。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信笺焚毁的过程比若若想象的缓慢。火苗最先吞噬’心悦君兮’四字,墨迹在高温中卷曲变形,像她此刻揪紧的衣摆。范闲突然伸手想抢救什么,却只抓住一把浮灰。他掌心被烫红的痕迹,日后成了若若记忆中最鲜艳的伤口。
‘我去看看药圃。’她起身时带翻了茶盏,褐色的液体在宣纸上漫延,像幅写意的山水。范闲欲言又止的表情倒映在釉色温润的瓷片上,随着茶水渐渐晕开。
药圃里的积雪足有半尺深。若若跪在雪地里扒开冻土,指尖碰到个硬物——是当年范闲教她认药用的青瓷钵。钵底还沾着干枯的黄连,苦香被岁月酿得愈发醇厚。她突然明白,有些感情就像这味药,明知极苦,却总有人甘之如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上元节那夜,范府挂满琉璃灯。若若在回廊遇见醉醺醺的范闲,他衣襟上沾着酒渍,眼神却清明得可怕。他们隔着盏走马灯对视,灯影里流转的山水花鸟在彼此脸上投下变幻的光斑。
‘鸡腿姑娘……’范闲突然开口,又猛地住嘴。这个称呼像把钝刀,在若若心上来回拉扯。她看见他腰间多了个绣着梨花的香囊,针脚细密得不像出自武将之手。
更鼓响过三声时,前院突然骚动起来。若若赶到时,只见范闲单膝跪地,胸口插着把泛蓝光的短匕。影子——那个永远如影随形的侍卫——正用布条死死勒住他上臂,可黑血还是不断从指缝渗出。
‘碧蚕蛊!’影子声音嘶哑,’见血封喉……’
若若的银针比思绪更快。三根长针已刺入范闲颈侧要穴,针尾颤动如蜂鸟振翅。她撕开他前襟的动作堪称粗暴,露出匕首周围蛛网般扩散的青紫色血管。
‘备热水、白布、烈酒。’她的声音陌生得不像自己,’再取我妆匣底层的青瓷瓶。’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
手术持续到东方既白。若若的襦裙下摆全被血水浸透,凝结成冰冷的铁锈色。当最后一丝毒血被金针引出,她才发现自己咬破了嘴唇,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
范闲昏迷中攥着那个梨花香囊,指节发白。若若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发现香囊夹层里藏着张字条:’庆庙初见,至今思君’。字迹秀逸,与那幅藏在暗格里的画像题款如出一辙。
‘小姐……’老管家捧着参汤欲言又止。
若若将染血的帕子浸入铜盆,清水顿时绽开朵朵红梅。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范闲教她认的第一味毒药就叫’一点红’,说是见血化碧,中者无救。如今她才懂,世间最毒的从来不是草木金石。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
三日后范闲苏醒时,若若正在廊下煎药。药吊子里的液体咕嘟作响,蒸汽模糊了她的面容。她听见屋内传来瓷器碰撞的轻响,接着是范闲沙哑的呼唤:’若若……’
阳光穿过药雾,在她睫毛上挂满细碎的光珠。这一刻她忽然释然——有些缘分就像药方里的君臣佐使,她注定是那味不起眼的甘草,不能治本,却能解百毒。
‘哥哥该喝药了。’她端碗的手稳如磐石,碗底沉着朵干枯的忍冬花。十年前那个追着马车奔跑的小女孩,终于学会了把眼泪熬成苦口的良药。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范若若传·卷四·辞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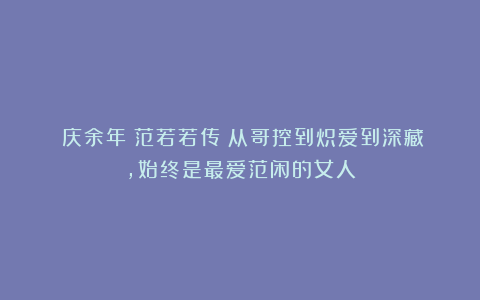
一
五更三点,喜鹊开始在范府最高的那株梧桐上啼叫。若若坐在妆台前,看着铜镜里自己眼下淡淡的青影。昨夜她亲手将七十二味药材装进锦囊——白芷安神、丹参活血、冰片醒脑——系在了范闲新房的门楣上。此刻指尖还残留着药材的苦香,与窗外飘来的喜乐声格格不入。
‘小姐,该更衣了。’丫鬟捧着叠得整齐的衣裙站在身后,欲言又止。若若摇摇头,自己拉开樟木箱,取出一件雨过天青色的素罗襦裙。这是用儋州特产的’海天霞’染的,阳光下会泛出极淡的绯色,像黎明前最后一抹将褪的月色。
梳妆时,她发现妆匣底层多了一卷《金匮要略》。羊皮封面下压着片薄如蝉翼的玉简,上面刻着北齐三皇子特有的飞白体:’医道无涯’。玉简边缘还沾着些许塞外的黄沙,摩挲时会簌簌落下,在掌心堆成小小的沙丘。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吉时将至,范府中门大开。若若站在回廊转角,看满院红绸在春风中翻飞如浪。那株百年海棠开得正好,花瓣被风卷着掠过她发间,有几片沾在鬓角,像是不忍离去的挽留。
新人踏着红毡走来时,若若下意识摸了摸袖中的青瓷瓶。瓶身早已被摩挲得泛起柔润的包浆,在阳光下流转着琥珀色的光晕。范闲一身大红喜服,金线绣的麒麟在袖口腾跃。他侧头与新娘低语时,眼角笑纹里盛着的温柔,比若若在任何一个梦境中想象的都要明亮。
新娘盖头下的金步摇随着步伐轻响,声音清脆如儋州海边的小铃铛。若若突然想起十二岁那年,范闲信中描述北齐新娘的嫁衣要缀满九百九十九颗珍珠,’走起路来像把星河穿在身上’。此刻长安城的阳光穿过海棠枝桠,在新娘霞帔上洒下跳动的光斑,确实比星河还要璀璨。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交拜天地的唱礼声中,若若悄然退出人群。她沿着抄手游廊慢慢走着,指尖抚过每一根廊柱——七岁那年她曾用炭笔在这些柱子上悄悄标记身高,最高的一道刻痕旁还画着歪歪扭扭的小花。如今那些痕迹早已被新漆覆盖,就像她藏在瓷瓶里的心事,终将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如初。
厨房飘来合卺酒的甜香。若若驻足片刻,想起自己昨夜在酒坛中投下的那枚解毒丹。丹药是用雪山灵芝混着南海明珠粉制成,入水即化,无色无味。就像她这些年的情愫,终究要无声无息地消融在别人的合欢酒里。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暮色四合时,若若独自在药圃里采撷最后一批春菊。这些金黄的小花晒干后能制安神的药枕,她要留给范闲——自从宫变那夜,他总在睡梦中惊悸。竹篮将满时,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踩在泥土上的节奏她闭着眼都能辨认。
‘明日就走?’范闲的声音比平日低沉,衣襟上还沾着喜宴的酒气。他手里拿着个紫檀木匣,匣盖上的缠枝莲纹在暮光中泛着幽暗的光泽。
若若将一朵菊花别在篮绳上,点了点头:’想去岭南看看,《本草拾遗》上说那里有能解蛊毒的凤凰草。’
范闲突然抓住她的手腕。他掌心有一道新愈的伤痕,粗糙的触感让若若想起儋州海边粗粝的礁石。木匣被塞进她手中,沉甸甸的,里面装着太医院全套的金针,每根针尾都刻着细小的梅花。
‘带着防身。’他松开手时,指尖在她腕间停留了一瞬,温度比暮春的晚风还要暖些,’每月初七……’
‘我会写信。’若若接过话头,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明日天气。她没告诉范闲,自己已经请求三皇子打通了北齐的驿路,往后那些信会走最快捷的官道,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延误数月。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
次日拂晓,若若的马车悄悄驶出范府角门。车厢里除了一箱医书,就只有那个装着青梅的陶罐——是去年和范闲一起腌的,原本说要等他大婚时开封。车帘放下前,她最后望了眼生活了十年的宅院。东厢房的窗纸上映着微弱的烛光,范闲大概又在批阅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公文。
马车碾过朱雀大街的青石板,远处传来净街鼓的声响。若若打开范闲给的木匣,发现金针下面还压着张地契——是儋州港附近的一座小院,临海靠山,院里种着成片的药草。地契背面用朱笔画了简略的布局图,药圃位置标着株小小的忍冬,笔触稚嫩得像孩童的手笔。
车过灞桥时,天已大亮。若若取出青瓷瓶,轻轻拔开木塞。瓶中飘出儋州海风特有的咸涩,混着药圃泥土的芬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墨香——那是十年书信积攒的气息。她将瓷瓶倾侧,一缕细沙般的灰烬随风飘散,落在桥下的春水里,转瞬不见。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
三个月后,北齐边境的官道上多了个背药箱的女郎中。有牧民看见她在暴风雪中独自攀爬悬崖,只为采一株传说中的雪莲;也有商人传言,说她用金针救活了被狼群围攻的小王子。偶尔夜深人静时,她会就着篝火翻阅随身携带的医书,书页间夹着的信笺上,字迹工整如列队的士兵:
‘见字如晤。岭南湿热,凤凰草确有其物,花如金铃……’
信纸的右下角,永远画着朵小小的梅花,在火光映照下,仿佛刚从枝头摘下般鲜活。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范若若传·终卷·忍冬香》
一
北齐的初雪来得比往年更早。若若在医馆檐下挂了串风铃,是用南海贝壳与雪山冰晶串成的,风过时叮咚作响,像极了儋州港的潮声。这日她正在誊抄《黄帝内经》的残卷,忽闻门帘响动,带进一阵裹着雪粒的风。
三皇子依旧穿着那件半旧的玄色貂裘,肩头落雪未化,在炭火旁蒸腾起细小的白雾。他默不作声地蹲在药碾前,将晒干的忍冬花倒入石臼,研磨的动作熟练得像个老药童。若若瞥见他冻得发红的手指关节——那是去年冬夜为救坠冰孩童留下的冻疮。
‘殿下不必日日来此。’若若递过一杯热茶,茶汤里浮着几粒枸杞。
青年皇子接过茶盏,指尖在杯沿轻轻一叩,算是应答。他从不称她’范小姐’,也不唤’若若’,总是用这种轻微的响动代替言语。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将医馆包裹成与世隔绝的茧。石臼与碾轮摩擦的声响规律而安宁,若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无言的陪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腊月最冷的那夜,若若冒雪去山坳里为牧民接生。归来时已是三更,棉靴浸透了血水与雪水,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医馆门缝里透出的灯光让她怔了怔——本该熄灭的油灯此刻亮如豆星。
推门看见的景象永远烙在了记忆里:三皇子跪坐在火塘边,正用雪搓她昨夜未及清洗的染血布巾。铜盆里的水已结了层薄冰,他修长的手指冻得发紫,却仍固执地揉搓着那些顽固的血渍。听见门响,他抬头望来,眼底映着跳动的火光,像雪原上突然亮起的星辰。
若若的银针在掌心攥得生疼。她想说些什么,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击中。朦胧中感觉有人用貂裘裹住她,那衣裳带着松木与薄荷的气息——是北齐贵族熏衣用的香,却混进了药草的苦涩。
高烧持续了三日。每当她挣扎着醒来,总能看见床畔小几上换着新冰的帕子,和一碗始终温热的药汤。第四日清晨,她发现窗前多了个粗糙的木架,上面晾着所有染血的衣衫,洗得发白,在朝阳下像一片片飘荡的云。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开春时,若若决定南下。收拾行囊那日,三皇子突然出现在医馆门口,身后跟着两匹矮脚马,马背上驮着轻便的行李。
‘江南湿热,多瘴气。’他递来一个锦囊,里面装着犀角与雄黄,’我认得路。’
若若望着他晒黑的面庞,忽然想起范闲信中提过,这位皇子曾为绘制边关舆图,独自穿越过死亡沼泽。她接过锦囊,闻到一丝熟悉的忍冬香——正是她平日用来熏衣的配方。
他们沿着黄河古道缓缓而行。三皇子总在日落前找到最安全的宿处,若若则用银针为沿途村民治病。某个雨夜借宿破庙时,她发现他腰间佩剑的剑穗竟是儋州特有的双股编法,与自己当年送给范闲的一模一样。
‘十年前北齐使团路过儋州。’他罕见地主动开口,’有个小姑娘送了我这个。’
雨声渐急,篝火噼啪作响。若若望着跳动的火焰,忽然明白为何总觉得他捣药的动作似曾相识——那节奏与范闲分毫不差。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江南的梅雨季来得猝不及防。若若在苏州城东租了间临水的小院,檐下挂满驱湿的艾草。三皇子每日黎明即出,总在暮色四合时带回新鲜的草药,有时是带着泥的茯苓,有时是沾露的薄荷。
这日若若在溪边清洗新采的鱼腥草,抬头看见他蹲在上游石阶上,正仔细漂洗一捧忍冬花。朝阳穿过柳枝,在他玄色衣袍上洒下流动的光斑。他洗花的动作很轻,仿佛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连花蕊里的露珠都不忍碰碎。
‘给你。’他忽然转身,将一朵半开的忍冬别在她鬓边。花茎上的细刺已被小心剔除,断面还带着新鲜的汁液。若若闻见熟悉的清苦气息,恍惚间回到儋州的药圃,七岁的范闲正指着藤架说:’此花冬日不凋,故名忍冬。’
水珠顺着她的额发滴落,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小的水花。三皇子忽然伸手,用袖口拭去她颊边的水渍。这个动作太过自然,就像山溪终要汇入江河,就像他们早已这样相处了千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
立秋那日,苏州城举办药王祭。若若在集市上为孩童施防疫的香囊,抬头看见三皇子站在糖画摊前,正认真看匠人浇铸一朵梅花。金黄的糖浆在石板上流淌,渐渐凝固成透明的花瓣。他接过糖画时,指尖被烫得微红,却仍小心护着那易碎的甜蜜。
返程时路过一座石桥,桥下船娘正在唱《子夜四时歌》。三皇子突然驻足,从怀中取出个布包:’给你的。’
包里是套崭新的金针,针尾刻着细小的忍冬花纹。若若认出这是北齐皇室工匠的手艺——当年范闲大婚时,她收到的礼物也是这般制式。
‘我查过典籍。’他声音很轻,’范闲那套针,原是准备送给……’
‘我知道。’若若打断他,指尖抚过金针冰冷的光泽。这些年来,她早已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拼凑出真相:鸡腿姑娘就是三皇子的胞姐,当年化名游历庆国时与范闲相识。命运像个圆,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晚风拂过,桥下流水载着落花远去。若若将糖画举到唇边,甜味在舌尖化开的瞬间,她忽然释然地笑了。原来最苦的药草也能酿出蜜糖,最深的伤痕终会开出花朵。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
多年后,当范闲的商船停靠北齐港口时,总要去城西的医馆坐坐。馆前那株移植的忍冬长得极好,冬日里也挂着金黄银白的花。若若发间永远簪着朵新鲜的小白花,三皇子则在一旁安静地捣药,仿佛他们从天地初开时就该是这样。
有次范闲带来儋州特产的青梅酒,酒过三巡,忽然指着墙上那幅《黄帝内经》的挂图笑道:’这字迹倒像我年轻时的笔法。’
若若笑而不答,转身去添茶水。窗外夕阳正好,将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最终在青砖地上融为一处。案几上的瓷瓶里,新采的忍冬花静静绽放,清香弥漫一室,盖过了经年的药苦。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范若若传·外篇·星河渡》
一
漠北的夜风像一把钝刀,剐蹭着帐篷的毛毡。若若的银针在灯下泛着冷光,针尾系着的红丝线随着产妇的喘息轻轻颤动。汗水顺着她的眉骨滑落,在颧骨上结成细小的盐粒。帐外传来马蹄声,接着是三皇子压低嗓音的询问:’还需要热水吗?’
‘再烧一锅。’若若头也不抬地回答。她正用左手按住产妇高高隆起的腹部,右手三根银针刺入合谷、三阴交等穴位。产妇的指甲深深掐进她手腕,留下月牙形的血痕,她却浑然不觉。
帐帘突然被掀开,带进一阵刺骨的风雪。商旅打扮的老者搓着手哈气:’范大夫在吗?老朽从京都来,带了些南边的药材…’
若若的针尖微不可察地颤了颤。她认得这个声音——是范府的老管家,当年她离开时,老人曾偷偷往她行囊里塞了一包金叶子。此刻他刻意改换的称呼,是不愿惊扰这场接生。
‘放在药箱旁吧。’她声音平静,手上银针又深入半分。产妇突然一声痛呼,帐内顿时乱作一团。等婴儿终于发出第一声啼哭,东方已现出鱼肚白。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二
老管家带来的樟木箱里,整整齐齐码着岭南的肉桂、川蜀的黄连。最上面是个锦囊,倒出来是几颗蜜渍梅子——正是当年范闲常给她解药苦的那种。若若拈起一颗含在口中,酸甜滋味在舌尖化开的瞬间,恍惚又看见儋州药圃里,那个总把最甜的梅子留给她的少年。
‘范大人添了位千金。’老管家递上一封火漆封口的信,’小郡主满月时抓周,一把就攥住了您当年留下的金针。’
信纸上是范闲特有的瘦金体,笔锋却比往日柔和许多。若若读着那些关于女儿如何咿呀学语的琐事,忽然发现信笺角落画着个小像——圆脸女婴抓着金针傻笑,眉眼活脱脱是范闲的翻版。她指尖抚过墨迹,想起许多年前自己也是这样,在儋州的书房里,踮脚去够范闲案头的医书。
帐外传来三皇子与牧民交谈的声音,他正在学用胡语说’当归’。若若将信仔细折好,忽然注意到信封内层有极淡的胭脂香——想必是那位’鸡腿姑娘’亲手封缄。这个认知让她心头泛起奇异的平静,就像看见故人坟前开了朵野花。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三
夜幕再次降临时,若若独自走出帐篷。漠北的星空低垂得惊人,银河像一条缀满碎钻的缎带,随时会垂落到人间。她解下披风铺在沙丘上,仰头望着那些闪烁的光点——小时候范闲告诉她,人死后会变成星星,如今她忽然明白,活着的思念同样会升上苍穹。
寒风卷着细沙掠过耳际,恍惚间化作无数声音:五岁时范闲教她认药草的温言,十五岁在范府书房誊抄医案的纸响,宫变那夜金针破空的轻吟……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最终凝成星河流动的声响。
‘要起风了。’
三皇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手里拿着件新絮的羊裘,领口镶着银狐毛,在星光下泛着柔和的蓝光。若若任由他将大氅披在自己肩头,忽然发现他左手上缠着绷带——想必是劈柴时伤的,这人永远学不会量力而行。
‘你看那颗星。’她指向天鹰座最亮的一等星,’在南齐传说里,那是位不肯嫁人的医女变的。’
三皇子在她身旁坐下,沙粒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从不接这些关于星辰的故事,只是安静地陪她仰望。但若若知道,下次路过集市时,他一定会买下所有关于星象的残卷。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四
回到帐篷,若若取出妆匣底层的青瓷瓶。这是她离开范府时唯一带走的物件,如今瓶里装着漠北特产的沙棘油,治疗冻疮有奇效。她将油膏轻轻涂在三皇子手上的伤口处,感觉到他掌心粗粝的茧子——这是常年握剑的手,却为她学会了捣药、劈柴、煮粥。
‘京都来信了?’他突然问。
若若点点头,拧紧瓶盖。瓷瓶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已看不出原本的釉色。这些年它装过南海的珍珠粉、西域的龙血竭,就是再没装过儋州的青梅。
‘范闲有了女儿。’她将药瓶放回匣中,’眼睛像他,性子倒像她母亲。’
三皇子正在拨弄炭火,闻言火星四溅。他向来寡言,此刻却说了句奇怪的话:’孩子该叫你姑姑。’
若若正在整理银针的手突然顿住。针囊上绣着的忍冬花纹已经褪色,就像那些曾经灼烧肺腑的情感,终究会随着呼吸化为温热的雾气。帐外风声呜咽,像某种远古的回应。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五
次日清晨,牧民们送来新挤的马奶。若若正在清点药材,听见帐篷外孩子们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谣:’……星河渡口有个姑娘,她的药囊能装下整个月亮……’
她掀帘望去,看见三皇子蹲在孩子们中间,正用草茎编着什么。阳光下,他冷峻的侧脸难得柔和,手指灵活地翻飞着,不一会儿就编出个精巧的药囊形状。最小的女孩欢呼着抢过去,戴在脖子上当宝贝。
若若忽然想起昨夜那个未竟的星空故事。在天鹰座的传说里,那位医女最终化作星辰,不是为了纪念未得的爱情,而是为了永远照亮人间疾苦。她摸了摸袖中的银针,针尖在晨光中微微发烫,像一颗坠入掌心的星辰。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六
当商队再次启程时,若若的行囊里多了包京都的蜜饯。三皇子照例检查马鞍的系带,突然从褡裢里取出个木雕的小像——圆脸女婴笑得见牙不见眼,活脱脱是信中所绘的模样。
‘路上雕的。’他将小像递给若若,木头还带着体温,’可以挂在药箱上。’
若若接过木雕,发现底部刻着两个极小的字:’安康’。这不是范闲的笔迹,也不是她的,倒像是某种无声的承诺。她将小像系在药箱铜环上,随着马背的颠簸,木雕轻轻叩击箱体,发出笃笃的轻响,像远方故人的问候。
驼铃声中,商队逐渐变成地平线上的黑点。若若转身回到帐篷,取出昨夜未写完的信。墨迹在沙地特有的宣纸上洇开,她写下:’见字如晤。漠北苦寒,然沙棘果实可制良药……’写到这里,她顿了顿,又添上一句:’随信附小儿惊风药方一帖,可缝入香囊佩之。’
帐外传来孩童的笑闹声,混合着三皇子教授汉语的只言片语。若若将信纸折成方胜状,忽然发现自己的掌心纹路里,不知何时渗进了些许药草的青绿。这颜色再不会褪去,就像那些融入骨血的记忆,最终都成了生命本身的底色。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