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煊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出土了上千件陶质兵俑,按照身份级别不同可大致分为高、中、低级军吏俑和普通武士俑。高级军吏俑发现数量少,等级最高,其中重装铠甲高级军吏俑身着甲衣上均饰有一种浅浮雕彩绘V形纹,与甲衣类型和秦俑身份构成固定搭配,并与其它彩绘纹样共同构成甲衣的图案纹样体系。V形纹原本是模拟甲衣实物上用甲带制作的独立编饰,具有表征功能,本文试从秦文化背景对V形纹的内涵进行阐释,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V形纹的服饰文化属性
(一)高级军吏俑甲衣的纹样元素
高级军吏俑的甲衣通体彩绘,色彩绚丽,甲衣纹样种类丰富,有较明确的形制结构分区,除披搏外,大致可分为上旅前身胸部、后背上段(包括肩),上旅腹部、后背下段,下旅,边饰几大区域。V形纹见于上旅腹部、后背下段暴露的甲片上(图1),通过对高级军吏俑札甲的实验考古学复原可知,V形纹应是对甲衣实物上此型甲片中部独立甲带编饰的模拟(图2)。
图1 甲衣后身V形纹及其它纹样分布位置示意
图2 复原甲片及V形编饰正面示意
甲衣上的纹样图案主辅搭配,一般先构成纹样单元,然后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循环的方式展开,呈现出对称性图案效果,除甲带编饰外,还表现出织绣纺织物或髹漆皮革彩绘的特征。上旅胸部与后背上段主体纹样是交错分布的鸟纹、磬纹、八角形纹、对己纹(黻纹)等,其间以菱形、六边形纹等作为装点。边饰主体纹样为填充各种适合纹样的菱格纹。下摆甲带“似编贝般的整齐”“分外鲜明”。V形纹则顺应甲片排列以四方连续方式展开,构成了波折状图案。
色彩的运用也使甲衣纹样图案看起来格局分明,每个区域都包含多种色彩,其中边饰最为复杂;然后是甲衣上旅胸部与后背上段;甲带编列最为简洁,赭黑色甲片上的V形纹,多敷以五正色之一的朱红色,格外引人注目。
高级军吏俑甲衣主体纹样显然都蕴含着相应的主题,V形纹仅具简单的几何形态,从其纹样图案的体量、形式、色彩,以及作为甲衣实物上的独立编饰来看,与其它主体纹样的地位别无二致,只是如今并不似头顶小冠的鸟纹般是明确的显性元素,而是和其它几何类主体纹样一般都成为甲衣上主题模糊的隐性元素。
(二)中级军吏俑甲衣的纹样元素
秦俑甲衣上的纹样图案主要发现于高、中级军吏俑甲衣上。兵马俑坑曾出土车兵中级军吏俑,身着二类一型铠甲,仅在前身有护甲,两肩设有背带在背后交叉,与护甲腰部的系带相连,在身后打结系牢。护甲的四周都留着较宽的边沿,居中有甲片连缀,甲片较大,在护甲的领缘、左右两侧及下边环绕的边缘、双肩背带都能隐约地看到用白色、朱红、粉紫、粉绿、紫色、浅蓝色、黑色等绘制的图案花纹,据此可大致勾勒出此类甲衣彩绘图案的基本样貌(图3),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V形纹的内涵。
图3 中级军吏俑二类一型甲衣彩绘图案复原
原图来源:王亮
从中级军吏俑甲衣复原效果和整体风格看,彩绘图案刚劲有力,对比强烈,但体量、色彩、纹样的种类和构图的规矩性,都较高级军吏俑甲衣有所不及。
甲衣背带分为内、外两幅,外侧与前身甲周缘相连为一幅,内侧与领缘相连为一幅,每幅皆为带状,单位纹样按照二方连续方式展开构成折线式图案,彩绘应是对服饰实物色彩、纹样的再现。背带内幅的主体纹样特征鲜明,报告认为主要为几何纹样,经过仔细辨识,笔者认为应是身体饰点状纹的顾首状豹纹(图4-1),姿态与陕西凤翔长青乡南头村采集的顾首豹兽纹瓦当(图4-2)、秦都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丝织物上的顾首动物纹(图4-3)相类;身体的点状装饰则与湖北马山楚墓出土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衣领外侧车马田猎纹绦图案中的豹纹相似(图4-4)。
1.豹纹(中级军吏俑)
2.顾首豹兽纹瓦当(凤翔)
3.顾首动物纹(咸阳)
4.豹纹(马山)
图4 中级军吏俑甲衣背带上的豹纹及对比图案
(三)V形纹的服饰纹章属性
服饰纹章是国家政治军事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先秦时期军服有严格规定,无论普通士卒还是最高指挥者皆需在军服上佩戴便于识别的标志物,是为军服徽、章。章服制度更是为了满足“明尊卑”“别上下”的统治需求,用不同的纹样图案装饰帝王和百官公卿服饰,从国家政治层面区别和彰显地位身份。《后汉书·舆服下》追溯服章之制“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礼记·明堂位》记载“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司马法·天子之义》云“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尉缭子·经卒令》亦云“卒有五章”。由此可知服饰纹章滥觞于先秦时期,多取自然物象,具有鲜明的政治、军事意象,且随着政权的更迭不断被强化和调整。《诗·小雅·六月》言“织文鸟章”,郑笺云:“鸟章,鸟隼之文章,将帅以下,衣皆着焉。”《诗经·郑风·羔裘》载:“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可见鸟纹、豹纹等动物纹饰在服饰上的应用由来已久。
战国已将,各国“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鞌,以相夸上。争锥刀之利,杀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灭。荣利在己,虽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显然,伴随秦国的统一进程,服饰纹章也经历着新的建构。
高、中级军吏俑甲衣上的纹样类型丰富,内涵复杂,其纹样体系的多元素组合特征和主体纹样的物象属性,反映出这一时期秦国服饰纹章发展的特色。鸟纹是高级军吏俑甲衣上部显性的动物纹饰,极有可能是其鸟章标识;豹纹则可能是中级军吏俑特有的服章之一。豹纹和鸟纹的发现,明晰了甲衣主体纹样的范畴,反映出动物题材在秦俑服饰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在不同等级秦俑甲衣上的应用和差异,也体现了秦俑造型艺术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V形纹应属其列。
二 V形纹的艺术主题
春秋战国时期,秦瓦当虎纹的虎身上出现了一种典型的V形和锯齿形装饰,如陕西凤翔出土的秦雍城时期猎人斗虎瓦当(图5-1)和奔虎逐燕瓦当(图5-2),陕西咸阳秦栎阳城出土的战国晚期虎燕纹瓦当(图5-3)等。这种几何单独纹样成组排列,具有条纹波折特征,与传统云雷纹等存在较显著区别,有人称其为虎身“V形纹”,有人则将其归纳为波折形虎毛纹。
1.猎人斗虎瓦当(雍城)
2.奔虎逐燕瓦当(雍城)
3.虎燕纹瓦当(栎阳)
图5 秦瓦当所见V形和锯齿形虎身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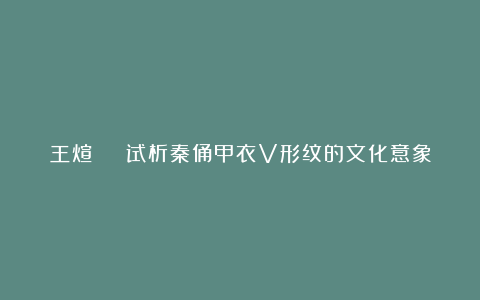
从考古学角度观察,相关研究中所涉波折形纹样在先秦时期不同地域、文化和动物主题都有所流布,其概念范围广,文化面貌复杂,说明秦文化波折形虎身纹极具包容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秦文化波折形虎身纹可大致分为“弧曲”和“折曲”两大类型,秦瓦当所见虎身V形纹、锯齿纹应属“折曲型”,且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
秦文化“弧曲型”虎身纹主要包括重环纹、连弧纹等,皆为单独纹样,可一种或多种组合排列作为主体或局部装饰,春秋早中期即有所见,早期装饰手法多满饰。重环纹浅凹弧端和两角向虎首,两端连贯排列呈重环纹带。连弧纹型式多样,且多有对称或变化形式,单独纹样两端具有显著的多段弧曲相连接特征,整体呈条纹状,依据弧曲和廓形的变化,大致可分为无廓的“”形、“”形;有廓的 “”形、“S”形。如日本miho博物馆藏金虎饰“”形、“”形纹(图6-1);甘肃礼县大堡子山K5:7铜虎颈部饰重环纹(图6-2),K5:2铜虎腿部饰“”形纹(图6-3);礼县圆顶山青铜器虎形支足虎躯饰“”形纹(图6-4);比利时所见大堡子山被盗鎏金虎饰“”形、“”形纹(图6-5);美国私人藏秦式铜虎饰“”形、“”形纹(图6-6);陕西宝鸡千河魏家崖村出土金卧虎尾部和躯侧分饰“”形、“”形纹(图6-7);陕西凤翔虢镇出土金虎躯侧和背部分饰“”形、“”形纹(图6-8);陕西秦都咸阳采集陶具上所见的虎身“S”形纹(图6-9)时代较晚,已处于战国晚期或秦代。
1.金虎(日本miho博物馆藏)
2. 铜虎(大堡子山K5:7)
3. 铜虎(大堡子山K5:2)
4. 虎形支足(圆顶山)
5. 金虎(比利时收藏)
6. 铜虎(美国收藏)
7.金虎(魏家崖)
8.金虎(虢镇)
9.陶具虎纹(咸阳)
图6 秦文化“弧曲型”虎身纹
秦文化所见“弧曲型”虎身纹的艺术形式多样,主要承商周传统,又融入多元因素,反映出兼容并蓄,继承发展的特点。如重环纹是由鳞纹抽象而成。 “”形、“”形纹广泛分布于中原和周边各区域文化,用于不同材质不同种类器物上的动物纹装饰,“”形纹似介于“”形纹和传统鳞纹之间,而两者同时具有鳞纹、“S”状纹,立刀状纹、云纹的某些特征,却更趋简洁、独立。“S”形纹形象更为直观,则是约从春秋晚期开始,先在北方地区流行的动物装饰尤其是虎身上出现的。
秦文化“折曲型”虎身纹出现于秦迁都雍城至栎阳时期,为虎身主体装饰,相较“弧曲形”纹样而言,其艺术面貌焕然一新,更为符号化,并且较为固定地用于瓦当等建筑构件上的动物主题装饰(图5-1至5-3)。作为大型动物躯干主体纹样的“折曲型”几何纹在北方地区出现较早,也较为常见,如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巴日沟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岩画群虎(图7-1),宁城县南山根、汐子北山嘴出土铜剑剑柄虎形装饰(图7-2、7-3),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罐上的虎纹(图7-4),陕北地区出土的动物形带钩(图7-5)等。有人认为秦瓦当“折曲型”虎身纹是源于秦人自身传统,但从商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已出现文化趋同现象,商周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互动从未中断,若追根溯源,这种秦虎身纹装饰及其器物组合,则更有可能是秦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面貌和审美观念。其深层意义在于对中原传统的突破,体现了秦文化发展求变,从向商周文化靠拢,再到“去商化”“去周化”,进而塑造秦式风格的强烈意图。
1.岩画群虎(乌盖苏木巴日沟)
2.剑柄虎饰(南山根)
3.剑柄虎饰(汐子北山嘴)
4.铜罐(北白鹅)
5.带钩(陕北)
图7 先秦时期动物躯干 “折曲型”几何纹装饰
高级军吏俑甲衣V形纹具有鲜明的秦文化政治军事属性,抽象的符号特征使其艺术主题和象征意义不易被理解,通过反观秦文化“折曲型”虎身纹,无论从艺术形式、动物主题、陶质载体,还是时间序列、秦文化特色等方面,都反映出两者千丝万缕的联系,顺应着时代发展的潮流。
先秦时期将毛、臝、羽、鳞、介兽等动物题材分类并举,秦波折形虎身纹的各种因素和类型亦见于秦文化其它动物纹装饰中,如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出土的贴面凤鸟纹,瓦当獾纹、凤鸟纹;陕西秦咸阳建筑遗址出土空心砖上的龙纹、采集的鱼形陶玩具等。这不仅反映出社会整体艺术风尚演变的阶段性和一致性,也符合先秦时期纹饰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传统或者说发展趋势,即将动物纹简省、变形或部分撷取出来,改造为更加简洁、独立、渐趋抽象的几何图形纹样,如目纹、鳞纹、波带纹、云雷纹、三角纹、菱格纹等皆有其动物造型渊源,这些纹样既可用于动物原型构图,亦可作为独立填充单元重组,因此应用场景也更为广泛。而将抽象的动物纹样与人元素组合的器物形式和思想可追溯至先秦时期造型艺术中的人兽母题传统,这一传统将人与动物合为一体,用一种或多种动物元素将人身体的某些部位兽化,往往形成器物上的标志性图案,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及社会文化内涵。
秦“折曲型”虎身纹的符号化发展应用不外于此,作为秦文化虎身纹中极为独特和典型的元素,“折曲型”纹样的分化独立表明其与动物主题和虎母题的内在联系得以强化。而秦俑兼具器与人的双重属性,其塑造的纹样图案、服饰纹章无不取其象征之意,彰表着人物身份也承载了器的功能。当两者结合,高级军吏俑甲衣上缀饰V形纹,宛若虎皮裹身,将人首虎身的形与神完美融合,体现出“折曲型”虎身纹随着秦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动物造型的局部装饰转变为传递历史文化意义的符号化纹样标识。
三 V形纹的社会文化内涵
只有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积极寻求转型,不断重塑自身的文化面貌,承前启后,秦文化才能够独树一帜、发展壮大,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应是“折曲型”V形纹演化的根源。高级军吏俑甲衣V形纹正是吸收了先秦时期及秦文化虎艺术主题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内涵,才得以呈现出新的面貌和追求。
在先秦社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中,虎是上层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元素,地位远高于其它野兽,如《周礼》记载只有王大射时才可用虎皮饰边的箭靶。
秦文化可归属于以鸟为图腾崇拜信仰的东夷文化之列,其族群可能与殷商时期君王的亲信近臣——虎侯有关,其崇拜对象依次为鸟、虎、豹、熊,虎鸟结合的纹饰造型无疑属嬴姓族群的文化因素。
虎具有战争和杀伐属性,是先秦时期政治军事力量的象征,也与秦国军事实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秦军锐士比六国更胜一筹,张仪曾描述秦兵皆“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甚至后世史家仍用“虎狼”喻秦国之强兵。体现秦国军事先进性的凭证制度上亦可窥一斑,秦惠文王时(前 337——前311)铸造的杜虎符,就是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战国虎符实物。
因为特殊的斑纹特征,虎还被赋予特别的神性,具有驱鬼避恶的象征意义。1980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国墓葬中出土一块正面绘有一虎系于树的木板,画中猛虎可能担负着镇守棺室、护卫亡者的使命。可见虎在秦丧葬文化观念中具有重要意义。
渊源于古老悠久的四象星宿体系,虎更被赋予敬天授时和拱卫中央的威仪。秦始皇帝陵本身就布“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这无疑是政治权力与传统观念的一种呼应。
目前对秦俑和俑坑性质的探讨仍未盖棺定论,但共同的观点都认为这是秦国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和组织之象征,与战功或武力相关。高级军吏俑是迄今所见在职权或爵级方面地位最高的兵俑,其显贵的政治地位,权威的军事身份和忠勇、守猛的军人品格等社会属性都与虎母题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相契合。高级军吏俑甲衣原有鸟纹(凤纹)元素,基本排除了V形纹是简省鸟纹的可能性;中级军吏俑甲衣上的豹纹,表明了虎、豹有别的身份等级之意,正所谓“大人虎变”“君子豹变”;而承载虎母题象征意义的服饰元素正是甲衣上的V形纹。
综上所述,高级军吏俑甲衣V形纹抽象的几何形态蕴含着生动的历史画面和传统,将其从先秦时期具象而典型的动物纹装饰中提炼成为独立纹样,进而作为秦俑甲衣上虎身纹和虎文化的符号标识,这是秦文化虎艺术主题、社会观念与服制高度结合的产物,是秦国重建帝王生前身后世界秩序的图像化表现,充分体现了秦文化继承、融合、创新的集大成特色。这或可为认识和探索秦俑服饰内涵拓展新的视野。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4年冬之卷(总第32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希恩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