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玉友刚开始接触玉雕时,目光往往先落在料子好坏、工艺粗细上。这很正常,但随着观赏经验增多,不少人会慢慢体会到,玉雕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表达。纵观玉雕艺术的发展,从早期追求形似的极致写实,到后来注重意境营造的写意风格,其表达方式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而“虚实结合”,恰恰是这个演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它让玉雕从追求“像什么”,走向了传递“有什么意味”的新境界。
从“做什么像什么”到“做一半,留一半”
传统的玉雕,讲究的是“做什么像什么”。比如创作一只老虎,就要有完整的虎头虎身虎尾,连毛发都要根根分明。写实非常考验功力。例如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张焕庆老师,就是当代写实玉雕的代表人物。我收藏他创作的一件碧玉乌篷船,从船上的麻绳到水浪的纹理,再到糖色的巧妙运用,都处理得极其逼真,几乎找不到一处虚化的地方。
这种写实当然有其价值,它体现了工艺的极致,也承载了传统的审美。但问题也随之显现:一方面很费料,特别是在籽料日益珍贵的当下,每一刀都是成本;另一方面,过于写实就会缺少“留白”,玉料本身特有的温润、厚重之美,反而被繁复的工艺所掩盖。
大概在2000年初,玉雕界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创作者开始尝试“做一半,留一半”的表现手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虚实结合”。这方面,杨曦大师应该是最早尝试的,他做钟馗,只做了头和扇子,身体的部分就虚在料子里,没有刻意雕出来。
这一转变,标志着玉雕艺术语言的革新。
虚实之间,找到工与料的平衡
虚实结合不是偷懒,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做减法”。这背后,体现的正是智慧的取舍。创作者将功力凝聚在最见精神的关键处,比如人物的开脸、手的姿态等“实”处务必精准传神;而将身体、背景等部分,则大胆“虚”化,融入玉料天然的形态之中。
这种处理方式带来了几个好处:
一是保留了玉料的大面,让观众能看到玉质本身的美。玉不是木头,不是石头,它有自己的生命感。大面积的弧面、光面,才能把玉的油性、细度、光泽表现出来。
二是突出了作者的意图。这样更能强化作品的视觉焦点,使观众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作品的核心意境上。例如杨曦大师的《无畏施尊者》,降龙罗汉的脸和手是实的,身体却融在料子里,观众反而更会去关注罗汉的神情、手的力道,而不是被衣纹、飘带这些细节分散注意力。
三是为观者创造了参与的空间。实处展现的是创作者的功力,虚处则留给观者去理解和想象。在观众与作品之间,由此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写意之境:观者参与的艺术共创
当“减法”做到极致,便通向了“写意”的广阔天地。写意不是简单的“做得少”,而是更高层次的“做得巧”。它更像是一种“造境”艺术——创作者营造一个意境,留出适当的空白,邀请观者来欣赏,来思考,来共同完成意义的构建。
例如,我前段时间收藏的三件苗烈作品:一件是戴斗笠的老者钓鱼,一件是抚琴的高士,还有一件是执扇的文人。观者很难也不必确指其具体身份——有人联想到嵇康,有人看见姜太公,也有人读出李白的影子。
更妙的是,这些作品的形态往往打破常规,采用倾斜的、破面的构图,在看似不稳定的动态中寻求平衡,这种视觉的张力,恰恰激发了审美的再创造。这正是写意作品的魅力所在:观众看见什么,它就是什么。
能否“入”境,是衡量写意作品能否打动观众的关键。当观众凝视作品时,脑海中浮现出熟悉的诗句、典故,或勾起某种个人情感,仿佛读懂了创作者未尽的言语,甚至为之注入独到的理解——这就是行内常说的“进去了”。
此时此刻,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者,而是与创作者共同完成了作品的最后篇章。这种精神层面的互动、情感层面的共鸣,正是写意作品最动人的特质,也是其在当代愈发受到青睐的深层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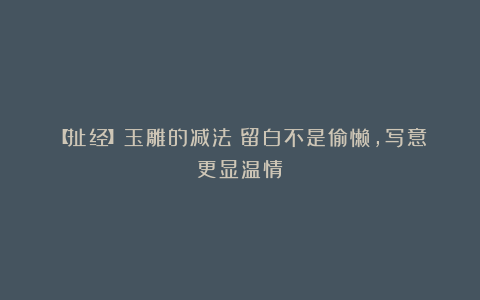
从传统的写实,到虚实结合,再到今天的写意,玉雕这二十年,走得很扎实,也很有意味。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艺术语言在不断丰富。
对我而言,不管是写实、写意,还是虚实结合,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些既有工艺功底,又有思想深度,还能与藏者“对话”的作品。
玉雕不是冷冰冰的石头,它有人情、有温度、有生命。而我们每一个爱玉、藏玉、做玉的人,都在参与这场没有终点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