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承千年古韵,融时代新思,于传承中焕彩,于创新里生辉,绘就了跨越时空的绮丽华章。
犍陀罗作为古印度十六国之一,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是白沙瓦,是犍陀罗的中心城市和贵霜帝国(汉朝时期的月氏人建立的,后来印度化)的夏季首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佛教中心,因此被称为“佛教圣地”。
从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入侵,到希腊人对犍陀罗130余年的统治,希腊化文化在这一地区影响比较深刻。从此犍陀罗地区就成了希腊雕刻与印度佛教融合的地带,因此犍陀罗是一个兼地理、历史和艺术内涵的概念,印度加希腊式佛像应运而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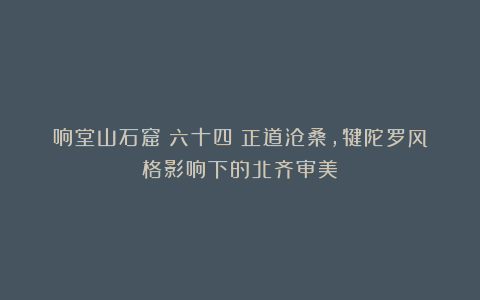
犍陀罗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始阶段,在公元1世纪左右,石板浮雕图像古朴且粗糙,人物肌体刻画平板化倾向显著,姿态与表情僵硬,来自中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第二个阶段繁荣阶段,大约在公元2-3世纪,石板浮雕与圆雕造像并行,图像美观且写实,人物形体结构合理,姿态优美自然,希腊、罗马雕塑技术得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一时期的佛、菩萨等圆雕像发达,佛传故事浮雕数量众多,佛传场面多,兼有少量本生、因缘故事浮雕。第三阶段是后续发展阶段,大约在公元4-5世纪,石板浮雕等继续流行,泥塑造像的图像流行开来,部分造像形式化倾向日益显著,呈现出在既有犍陀罗文化基础上的继续发展状态。
犍陀罗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西域、河西走廊,中原北方等地区的造像艺术。所有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国并非直接粗暴的嫁接在中国儒家、道家等文化之上,而是以某个切入点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然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生命力的组合,以此更远、更快的传播。
从东汉明帝梦见“小金人”开始,派遣官员前去西域迎回竺法兰、摄摩腾用白马驮经书运到洛阳,尤其是进入南北朝时期则开始大量地向东传播,从而促成了西域与汉文化地区佛教物质文化的高度繁荣。公元5世纪中叶北魏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河西走廊随之纳入帝国版图,西域门户被再度打通,使得犍陀罗文化因素能够畅通无阻地输入汉文化地区。公元5.6世纪之际随着北魏推行汉化改革,犍陀罗文化影响逐渐消退,但以往传入的犍陀罗文化因素还在部分地存续发展。高齐政权本来脱胎于北魏,在文化上,高氏家族则对汉文化态度与北魏不同,北魏推行汉化,而高齐贵族大多来自六镇藩属,反对汉化。鲜卑复古思想比较突出,于是重新对犍陀罗风格的造像开始了新一轮开凿。
响堂山石窟佛像的面容造型注重写实,端庄慈祥,身姿挺拔,嘴唇薄而线条分明,展现出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犍陀罗风格的写实手法。响堂山石窟中的雕刻作品运用丰富的线条来刻画佛像的面部表情、衣纹褶皱等细节,使得佛像更加生动逼真,与犍陀罗风格的雕刻技法注重线条的运用,异曲同工。
石窟中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各处运用深浅浮雕的形式雕刻着多种多样且极富变化的美化佛像和洞窟环境的图案纹样,如连珠纹、莲花纹、忍冬纹等图样,均来自印度、波斯、希腊等地方,在犍陀罗地区融合传达到的东方。大多数雕塑作品包含了大量的佛教故事题材,如佛陀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采用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故事题材,通过深浅浮雕、圆雕等技法来塑造物体的三维形态来展现佛教的教义和思想,使得佛像、菩萨等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整个石窟更加华丽庄严。
“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诞生在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的交流与对话之中。”响堂山石窟在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与西方艺术融合的特征,这种影响贯穿于造像的形制、服饰、体态之中,塑造了中国审美标准的“北齐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