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有生以来真没去过。
2025年“双十一”这天,我们一百多退休老人随团来到这个被称作平湖的县城,先后参观了平湖博物馆、东湖景区、李叔同纪念馆。东湖,这方被浙北平原温柔托举的湖泊,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更是平湖人用千年时光织就的文化锦缎——它裹着历史的针脚,浸着人文的染料,在李叔同的墨香里舒展成不朽的画卷。
平湖的故事,要从六千年前的一粒稻谷说起。当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在东湖西岸的汤山遗址播下第一株粳稻,这片土地便注定与文明结下不解之缘。春秋时属越,战国归楚,秦汉设县,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定名”平湖”,取”地居海滨,易守难攻,如湖之平静”之意。六百年的建县史里,平湖始终保持着江南小城的从容:莫氏庄园的雕花门楣还凝着清代的月光,南湾炮台的斑驳弹痕仍记着抗倭的烽烟,而西瓜灯文化节的流光溢彩,又将古老民俗酿成了当代的诗。
最能触摸平湖文脉的,是那些散落在城巷间的文化基因。”李叔同纪念馆”旁,至今留着他少年时读书的”小南海”书斋遗址;建国北路的莫氏故居前,百年香樟的浓荫里还飘着评弹的软糯唱词;而遍布乡村的钹子书艺人,用吴语唱着《田头山歌》《三埭头》,将农耕文明的智慧唱给天地听。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化碎片,实则构成了平湖的精神经纬——它不似大都市的喧嚣张扬,却像东湖的水草,在静默中把根须扎进每一寸土地。
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在东湖达到最和谐的境界。这座由汉代彭越浦、唐代东湖塘演变而来的湖泊,与绍兴的东湖截然不同,它本是人工与自然共同的作品:唐贞观年间筑塘围湖,宋元时疏浚河道,明清更添亭台楼榭。如今的东湖景区,三岛鼎立(案山、池海、鹦鹉洲),五桥卧波(案山桥、环碧桥、九曲桥等),湖中有岛,岛上有塔,塔影倒映处,恰是李叔同纪念馆的飞檐。春有樱花缀满曲径,夏有荷花铺成绿云,秋有桂雨落满长堤,冬有残雪染白报本塔,四季流转间,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早已浑然一体。每天,除了游人,馆外广场的白鸽或飞或站,悠闲自得。
若说平湖是一本书,李叔同便是其中最动人的章节。这位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艺术巨匠,1880年出生于天津,却在1901年至1905年间随母迁居平湖,度过了少年至青年的关键岁月。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写道:”我幼年时,母亲常带我到平湖的外婆家去,那地方的风景很好,我至今还记得。”这份对平湖的眷恋,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们循着他的足迹走进东湖:当年的”东湖书院”虽已不存,但湖西岸的”叔同路”仍保留着他少年时读书的痕迹。据说他常去附近的”小南海”书斋,窗临湖水,案置经史,清晨读经,傍晚习字,湖风穿堂而过,吹得案头的《说文解字》沙沙作响。这种”枕湖而学”的经历,或许埋下了他”悲欣交集”的人生底色——既得自然滋养,又受人文熏陶,方能既有艺术的绚烂,又有宗教的超脱。
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他青年时期的手札:”平湖山水清嘉,足以洗我尘襟。”墨迹未干的纸页间,能触摸到少年李叔同的心事:他在这里接触新学,接触戏曲,接触佛教典籍,这些多元文化的碰撞,最终在他身上发酵成艺术的醇酒与信仰的清露。更珍贵的是那幅《自画像》,画中青年目光如炬,衣袂飘举,背景隐约可见东湖的轮廓——这是他与故乡的精神合影,也是艺术与乡愁的永恒定格。
馆内最让人驻足的,是《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手稿复制件。这部律宗经典的研究著作,凝聚了弘一法师晚年的心血。笔锋从少年的锐利转为老年的圆融,墨色由浓转淡,恰似他从风流才子到苦行僧的人生轨迹。玻璃展柜外,东湖的波光透过窗棂洒进来,恍惚间,我们看见两个李叔同在此重叠:一个是倚栏看荷的少年,一个是执笔写经的高僧,中间流淌的,是平湖赋予他的文化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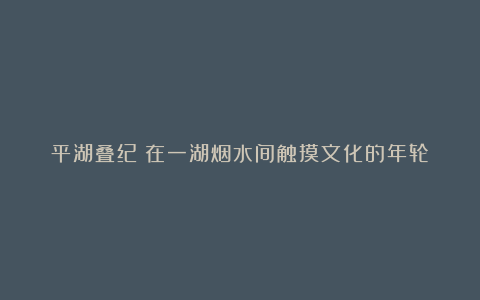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与当下共振。如今的平湖,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激活传统文化:莫氏庄园推出沉浸式昆曲演出,让游客在雕梁画栋间与古人对话;西瓜灯文化节融合数字技术,传统灯彩在AR投影中焕发新生;而李叔同纪念馆的”艺术启蒙课堂”,每年吸引数万孩子在这里触摸书法、篆刻、音乐的温度。可惜,我们到平湖,也就几个小时而已,如要真的沉浸式游览,来个两三天或三五天方可。
游船在东湖水面上缓缓而行,报本塔的塔影倒映在水中。忽然懂得,平湖的魅力从不在某个单一的符号,而在它的整体气象:是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交织,是自然的灵秀与人文的深邃共鸣,是李叔同笔下”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圆满。这座城用六千年的光阴证明:真正的文化,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中,愈发鲜明,愈发温暖。
离馆时,纪念馆的电子屏正播放着弘一法师的临终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这或许正是平湖文化的最佳注脚——它如东湖的水,清淡却绵长;如九峰的松,质朴而坚韧。当我们在这里触摸文化的年轮,其实是在与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共享同一份生命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