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侧面
“段建宇:渔樵”
YDP,伦敦
段建宇,《渔樵 No.20》 (局部) ,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油画棒,180 ×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我们每个人都被光照着,被屏幕包裹着,但那并不妨碍我们思考、生活、相爱。庸常不是虚无的,而是具体的。它包括身体的疲惫、快餐的油光、信息的噪音,也包括那些让人忍不住微笑的小细节——比如一条塑料袋在风中飘动。”
采访、撰文 / 孟宪晖
编辑 / Art-Ba-Ba办公室
图片致谢YDP、艺术家及维他命艺术空间
当我得知段建宇的个展“渔樵”将在伦敦YDP (Yan Du Projects) 呈现时,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画面,是约十年前的“杀、杀、杀马特”系列来到“朋克故乡”会有怎样的碰撞——那些被视为“土”“怪”“不合时宜”的混合审美,闯入一个自诩拥有反叛传统的城市,会激活怎样的化学反应?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很难再将跨国的展览看待成简单的文化互访,关于如何定义和理解“先锋”、如何以自身的复杂经验进入更广泛语境中叙事显然更值得探讨。
作为一位已经在长时段实践中完成自我更新的艺术家,段建宇以“渔樵”这一极具中国思想史与文人画传统记忆的符号,重新书写当代艺术家如何在现实内部生活、观察与思考。她以新作回望中国绘画史、民间造型色彩、八十年代装饰美学与国际艺术语境,也将自身从河南到广州的迁徙经验、在作家家庭中成长的语言感受,以及对图像、文本与身体的长期实验,一并纳入画面。在伦敦这个被不断叙述为“摇滚之都”“朋克现场”“艺术中心”的城市,段建宇所带来的不是姿态性的“反叛者”形象,她提供了一种更幽微又不失深刻的思考方式:在庸常生活与历史传统中如何持续提问。因而若要理解“渔樵”,就意味着要重新阅读段建宇前后十余年的创作脉络:从“杀马特与混合美学”,到“视觉修辞”“民间色彩”“身体与物象”“误读与再创造”……这些线索在“渔樵”中不断交织重汇,构成了一个可被细读的思想世界。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渔樵”意象:
“我很早就对’渔樵’这个题材产生兴趣。不是因为它在文人画史中的悠久传统,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看似平凡却能包容复杂思想的存在方式。我画的’渔樵’不是逃避者,而是见证者。他们既看山,也看屏幕;他们既在山水间,也在现实里。”
在中国悠久的渔猎文化中,“渔樵”的意象使用早已超越了原本的职业定位,随时代不断延展与拓宽,在诗文中尤其常被赋予“隐逸”的意味,仅《全唐诗》中晚唐诗人笔下“渔樵”就出现过四十余次。“北宋五子”之一邵雍(1011-1077)所著《渔樵问对》(不晚于1107年),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通过渔夫与樵夫二人的对话,探讨了涉及宇宙、社会、历史、人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将道家超越而出世的精神追求同儒家的积极入世结合起来。
而段建宇所感兴趣的恰是“渔樵”在尘世之中的状态——既出世又入世,既清醒又庸常。她将这个传统意象转回到当下生活之中,将这一题材视为一个支点,得以在古代与当下间移动。艺术家熟悉“渔樵问答”在思想史中的位置,也注意到赵汀阳、张文江等学者关于“渔樵”式对话的重新阐释——哲学在山水之间以口语展开,思想与日常并置,未曾远离人间。对她来说,这种介于“出世想象”与“入世劳作”之间的形象,更接近今天的现实个体。传统文人画中被净化过的象征角色,重新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可能是外卖员、打工者、办公室职员,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在日常劳作与自我怀疑之间徘徊的人。
段建宇,《渔樵 No.5》,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150 x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在一系列以“渔樵”为题的作品中,段建宇让渔夫不再披蓑衣,而是穿上由鲤鱼编织成的衣服,那是介于人类与鱼类之间的“第二皮肤”,带着戏剧化的夸张,也暗示身份的游移和现实的黏连。就像唐传奇和武侠电影中的侠客所具备的矛盾气质:既超脱又具体,既带有道德理想,又被现实磨损。“渔樵”的复杂不仅体现于主体人物身上,周遭的景物也不再是空灵的山水,而是混合了喷漆、塑料、陶瓷的场景——像梦,也像城市的碎片。艺术家希望这些形象能带出一种“被置换的古典”,一种跨越时间的滑稽。
段建宇,《渔樵 No.4》,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铅笔,200 x 14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如果说在中国绘画的语境里,“渔樵”是文人自我想象的延伸,是在动荡中寻找安顿的一种方式。在段建宇看来,当下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然不同了。“我们不是在乱世逃避,而是在秩序中被迫游移。我们没有山可以隐居,只能在信息的洪流中寻找片刻清明。”她所画的“渔樵”成为见证者,一如每天在屏幕前发呆的我们,都在劳作,也都在某种意义上“隐居”。他们不被浪漫化为抽身事外的哲人,而是继续留在事中,带着清醒与疲惫共同存在。由此建立起一种介乎历史叙事与个人经验之间的中间姿态:既不宣称宏大立场,也不退缩为纯粹的自我抒情,而是在绘画内部维持一种警觉的观看。对艺术家而言,这种“见证”的姿态是对历史的温柔怀疑。
当代与传统:
“我并不是在复原古代山水,而是试图寻找’传统在今天还能被看见的方式’”。
古代山水画讲究“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段建宇深知这一代人早已失去了那种空间经验。我们看到山水,多是通过屏幕,通过手机壁纸、广告背景、社交媒体图像。于是,艺术家的“渔樵”世界与中国山水传统发生正面碰撞,她在画中加入了“被隔着观看”的方式,试图更接近今天的视觉经验——风景往往先以图像的形式被消费,然后才成为“自然”。
在《渔樵No.1》中,她将画面上部处理成类似当代窗框与反光玻璃的区域,下部是平铺的水面,用喷漆和色块形成一种截断的空间关系。并置取代了线性透视,使观众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被观看的风景”——山水已内嵌于媒介之中。在《渔樵No.2》中,人物与山石呈现出类似舞台的调度,山像幕布般铺陈,人物带着违背“隐逸”初衷的形式出场,如演员般说话、辩论、沉默,就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扮演的角色,而这种“表演性”又揭示了观看行为本身。
段建宇,《渔樵 No.1》,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铅笔,140 x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渔樵 No.2》,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140 x 16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她借用马远、夏圭那种“一角见全境”的构图智慧;以八大山人作品中经典的上翻眼睛,给盘中之鱼增添出一份似睡非睡、漠然、冷视着世界的态度;又在“盘中鹤”中,将八十年代酒店菜雕的白鹤与虚化山形叠加,使传统山水的象征逻辑移入餐桌与装饰美学之中。“我觉得它们比山更像山,比景更像梦。它们的’人工’恰恰是今天最真实的自然。”如艺术家所言,山不再是纯自然,而与人工雕饰、集体记忆纠缠在一起。而传统更是开放的语言系统,只有在被挪用、打断、误用时才真正活着,段建宇希望观众在看这些画时,不辨“古”与“今”,而是去感受那种时间叠加的模糊感。绘画于她而言也不是再现过去,而是重新组织观看的方式。古典无需成为“纯粹的美”,当代也不必只剩“概念的冷”。段建宇在两者间往复,就像渔樵在山水与现实之间穿梭。
段建宇,《渔樵 No.3》及局部,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150 x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民间色彩:
“在我的画里,所谓’庸俗’的颜色其实是’生活的颜色’。我不在画布上追求那种优雅的灰或克制的中间调,我喜欢让颜色直接撞击——粉红对绿色、橙对蓝。这些颜色之间的冲突,正像人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活的力量。”
段建宇对色彩的兴趣从来都不是学院训练带来的,而是一种生活经验,来自具体时代与地域经验:河南集市上鲜艳到刺眼的颜色——塑料盆的红、挂历上的金,庙会糖人的粉,直接到没有转折的余地。而后广州的色彩又是另一番景象,潮湿、反光、流动,热带的绿、天桥广告牌的橘黄,它们在空气中渗开,也让段建宇的色彩观念在南北的交错中形成。这一经验与大卫·霍克尼从约克郡搬到加州后的经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学院里被认为“俗气的”颜色总是出现在段建宇的画中,她喜欢“过于鲜艳”,因为那最接近生活,而生活本就俗气。荧光的、塑料般的绿色,由喷漆和丙烯叠成了不自然的河流;像糖霜一样的山呈现出粉色,代表着庸常、甜腻的、过度的情绪。她希望画中的粉色既让人不适,又让人感到温柔——它是城市广告、婚庆布景、酒店墙纸的颜色,是人们共同的视觉记忆。她将八十年代“学习美”的努力——雕花菜盘、蕾丝窗帘、金箔日历——视作一种让生活看起来更体面的真诚的制造。这种民间装饰感,在她的作品中与山水和人物叠合,构成了既具记忆感又极其当代的色彩结构。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她认同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对于客观世界的不信任与冷静观察,倾向以“植物”或“矿物”的视角看待人和色彩:颜色不只是情绪附属,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生活噪音保留下来的证据。年画、纸马、泥塑等民间美术汇总的色彩在她的绘画中成为一种立场:拒绝被整齐的审美等级驯服,让画面在粗糙、明亮、近乎笨拙的色块交锋中,呈现出对现实最坦率的回应。
视觉修辞:
“绘画的修辞,其实就是在问:你怎么看?你为什么这样看?当观众意识到自己在’读’画面,而不是’看’画面时,绘画才真正开始。”
段建宇常以“写作”来比拟绘画。在写作中,词语和句子有自己的逻辑,作家需要在句法之间制造张力;在绘画中,笔触、形象与空白就是句法。它们不是描述现实的工具,而是组织感受的语法。她的画从来不是一幅幅“叙事”的图像,更像是一种修辞练习。她喜欢形象互相纠缠,让逻辑被打断,让语言在画布上自己说话。
在《渔樵No.8》中,变形的桌面与斜置的羊腿打破正常透视,圆点构成不稳定的桌面轮廓,使宴席场景被暂停般失衡。这样的“错误”是有意的修辞,它迫使观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引导去看一场视觉叙述,而非凭空接受“真实”。正如艺术家所言:“好的绘画不是讲故事的绘画,而是’句子式的绘画’。它通过停顿、转折、重复、比喻,让观看本身成为体验。”因而她也曾在《读者文摘》系列作品中,借用老杂志中“心灵鸡汤+风景插图”的版式,将河流与重复线条处理成如流水又似印刷机的重影,在重复中制造韵律,在韵律中产生模糊。
段建宇,《渔樵 No.8》,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180 x 25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修辞对段建宇而言也是态度。它意味着绕行,而不是直接抵达。她喜欢让意义被延迟,让观众在猜测、犹豫中体验图像的厚度。《渔樵》系列中,人物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看似偶然,实则各具节奏。树枝的走向、山形的弧度、衣纹的皱褶——它们像句子中的从句,彼此牵连,却又各自独立。当画中被加入不协调的元素——比如餐盘、酒店装饰、奇异的动物,也是艺术家在制造一种修辞性的碰撞。它们不是为了“讲道理”,而是让语言系统自我扩张。这种视觉修辞的训练,也让她学会了如何处理复杂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复杂社会情绪与经验被导入结构之中:并非回避沉重议题,而是拒绝以单义的“说明书”取代图像的多义性。绘画在这里成为修辞的现场,情绪在延迟中显形,结构成为抵抗扁平化理解的方法。她相信任何强烈的感受,都必须经过语言的过滤,才能变成艺术。
段建宇,《渔樵 No.20》,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油画棒,180 ×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文学与绘画:
“绘画让我延续了文学的逻辑:用视觉去写句子,用节奏去写情感。那种写作的痕迹,已经深深地留在了画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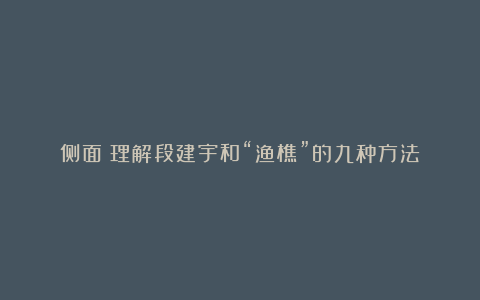
出身于作家家庭,使段建宇从小浸润在语言的环境中,文学杂志是她童年的背景音。即使当时还不懂文学是什么,她只觉得“写作的人”有一种奇怪的气质:他们可以用句子代替行动,用想象去延长现实。而这,大概是她后来画画的起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两千年初,在广州的生活,让她接触到陈侗的书店与阅读社群,在那里,她读到冯建华、图森 (Jean-Philippe Toussaint) 、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奥利维耶·罗兰 (Olivier Rolin) 、艾什诺斯 (Annie Ernaux) 等作家的作品,也从中获得对语言节奏与结构的敏锐感。
“语言本身就是生活的结构”这一说法,成为她日后处理图像的潜在方法论。段建宇将写作中的“急迫与忍耐”理解为绘画中笔触的冲动与修改的持续,把句读转换为色块的呼吸与形象的停顿。在人物造型上,她刻意保留某种“非人”的冷静:看似笨拙、安静,却拥有植物或石头般的存在感。
这一切,使她在“渔樵”与早年的《杀,杀,杀马特》《春江花月夜》等作品中,倾向采用片段化、跳切式的画面组织,而不过度依赖线性叙事。文学经验并未让她转向说明性的图解,相反,它让她更坚决地相信绘画可以成为另一种写作——通过视觉逻辑生成意义,以语气而非口号维系作品的持续可读性。好画面里也应该有气——那是一种内在的流动,一种思想在色彩之间呼吸的方式。
段建宇,《渔樵 No.6》,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油性笔,150 x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城市与庸常:
“’庸常’是我现在越来越常用的词。它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我所依赖的现实温度。”
随着观众逐步深入展厅,愈能发现段建宇如何把“渔樵”从山林带入城市,将传统中的隐者,与广告牌、快餐桶、连锁品牌和童年动画形象并置。“黑猫警长”身着制服的角色形象坐在快餐广告与红桶前,原本代表正义的童年符号被推入高饱和度商业环境,在塑料的光亮映照下显得略微疲惫和尴尬。她通过这种并置,让“英雄”与“打工人”的身份折叠,既带有温柔的幽默,也保留了对现实结构的清醒感知。今天的“英雄”——仍然坚守某种秩序,但同时被商品体系和娱乐逻辑包围。在另一幅画面中,红白相间的KFC桶、广州荔湾的“铜钱”大厦,以及异形化了的上海东方明珠作为“地标性建筑”戏剧性地矗立在一片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建筑中,“铜钱”大厦像太阳,也像佛光——俗气与庄重的并置令她感到真实:庸常与神圣从来就没有严格界限,它们在今天的生活里互相渗透。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段建宇,《渔樵 No.13》,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120 x 18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渔樵 No.18》,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铅笔、油性笔,150 x 15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城市风景于段建宇而言从来不是高楼或灯光,而是重复。“每天走过同一条街,看见同样的广告、听到同样的外卖铃声,那种机械感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流水线厂房——人被节奏吞噬,也被节奏保护。”她在绘画中也会刻意重复某些形象,正是其试图捕捉“重复时间”的证明。多年前艺术家从河南来到广州,最初只是因为它“温暖”。后来却发现,温暖并不只来自气候,更多来自人们对生活的松弛,也是这座城市教会了她如何理解庸常,可以在菜市场听到哲学讨论,也可以在美术馆外面吃碗云吞面。这种“不紧张”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感悟,是艺术不一定要通过崇高来抵达,而可以从庸常里出发。
就像曾经在“空姐”“杀马特”中把握到的时代变革,段建宇在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中,仍能敏锐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被光照着,被屏幕包裹着,但那并不妨碍我们思考、生活、相爱。庸常不是虚无的,而是具体的。它包括身体的疲惫、快餐的油光、信息的噪音,也包括那些让人忍不住微笑的小细节——比如一条塑料袋在风中飘动。”她眼中艺术的任务正式让“无意义的细节”重新被看见,恰如赵汀阳说“渔樵的哲学是生活的哲学。”因而她的作品延续“渔樵”作为观察者的角色:他们不再逃离,而是行走于城市塑料河流、电子山水之间,寻找微小但真实的诗意。
段建宇,《渔樵 No.17》,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油性笔、铅笔,160 x 14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身体与物象:
“我经常画动物——羊、牛、鸡、鱼。它们对我来说不只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人类自身的隐喻。它们身上有人的姿态、欲望与困惑,比人更直接、更无防备。动物不会掩饰,而这种赤裸的生存方式,恰恰是我在绘画中最想触碰的’真’。”
段建宇常说自己对“物”的感情很复杂。在她的画里,物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们像人一样有欲望、有表情,是我们与世界的接触面。它们见证了生活的平庸,也保存了生活的诗意。而羊、牛、鸡、鱼等动物也不只是自然生物,而是人类的镜像。它们承载着人的姿态、欲望与命运,甚至比人更诚实。
“渔樵”中,老羊与小羊对话的场景出现了两次,那种对峙的姿态被她视为代际关系的隐喻:沉默的注视、不完全重合的立场,以及仍在持续的关联。老羊的厚重与小羊的纤细,指向经验与天真、秩序与欲望的并行,而非彼此覆盖。她将这种代际“误会”理解为一种隐蔽却真实的传承机制,也自然关联到自己与父辈、与学生、与时代的关系。
段建宇,《渔樵 No.1》(上)及《渔樵 No.8》(下)局部
图片致谢艺术家与维他命艺术空间
动物于她而言的另一层意义是让身体的表达更直接。身体不是被描绘的对象,而是“思考的方式”。在户外写生时,段建宇近距离观察到羊群呈现“既重复又警觉的”状态:羊低头吃草的动作几乎机械,但当她靠近时,它们又会集体抬头,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盯着她。那种被同时凝视的感觉令人不安,也让她意识到“羊不是被画的对象,而是看回来的存在”。艺术家提到那一刻对自己很重要,因为“从那以后,我开始把动物当作有思想的身体,而不只是风景里的点缀”。《渔樵No.7》中羊群挤压的身体与集体质询般的姿态,使羊从温顺的意象转化为凝视者。而《渔樵No.10》中牛的形象则被当作“天然画布”,在其身上展开图案与符号,使之既是动物,又是语言载体,被朋友戏称为“穿花衣的哲学家”。鸡与 Crocs洞洞鞋的对视作品,更将生命与消费的关系推向荒诞:当带有炸鸡图案的鞋子面对活鸡,工业与有机、被吃的与被设为图案的角色互相回望,显露出现代视觉文化中常被忽略的残酷与滑稽。那种“互相注视”的关系,是所有作品都想探讨的主题:我们所消费的,也在消费我们。
段建宇,《渔樵 No.7 之一》,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油画棒,180 × 25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渔樵 No.9》,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75 x 1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渔樵 No.10》,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铅笔、油画棒,140 x 20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渔樵 No.11》,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油性笔,180 x 12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身体的逻辑和物的逻辑在这场展览中互相纠缠:身体让物获得情感,物让身体保持距离。这之间的循环,就是她理解的“绘画的伦理”。形象并未第一要务,其中呈现的呼吸更为关切——一种介于生与物之间的节奏,一种被生活反复摩擦后仍然闪光的生命力。在陶瓷创作中,这种身体感尤其明显。以“身体经验”为条件。女性形体陶瓷雕塑以夸张、原始、近乎图腾的姿态出现,釉色的流动强调重力与温度,使这些形象既关乎性别,也关乎信仰与生命能量。“陶瓷剑”系列则以软化、弯折、带裂纹的剑形,回应传统武器意象,在“以心为刃”的理解下,剑不再是攻击工具,而是内在判断与精神韧性的象征。
在这些关于动物与器物的创作中,身体与物的界限被持续打散:物带有人格,身体具有物性。她强调绘画与雕塑应当保留温度、汗、水渍与缺陷,拒绝密封的完美效果,因为真正“活着”的画面,恰恰来自这类不被抹平的痕迹。由此,“身体”逐渐向“语言”过渡,成为通往“误读与再创造”的内在通道。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段建宇,《渔樵 No.19》,2023年
布面油画、丙烯、油性笔、铅笔、喷漆,130 x 17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误读与再创造:
“误读让语言保持流动。我相信,只有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正确理解’,艺术才真正开始。”
段建宇认为绘画史本身就是一部误读史。每一代人都在重新理解前一代的图像。这种“错位的传承”让传统不再神圣,反而可触摸,也成为新的创作起点。关良、齐白石、林风眠、潘玉良……多位早期留洋的艺术家都曾带着对西方艺术的错位理解完成属于自己的创作,亦造就了现代中国绘画的语言诞生。
她的实践中,同样存在对马远的“水”、齐白石笔意、民间年画和寺庙彩塑的有意偏离:当这些图像被安置在“渔樵”“杀、杀、杀马特”“春江花月夜”等新的叙事框架下,它们脱离原本权威语境,重新成为开放的符号。在“渔樵”里,山水的“留白”更接近屏幕光源,气韵生动转化为光线生动;“盘中鹤”中,文人画的高逸理想与酒店菜雕的装饰风格并置,真假之间,美术史以外的视觉经验,反而带来了更为强烈的现实感。
段建宇,《渔樵 No.12》,2024年
布面油画、丙烯、喷漆、油性笔、铅笔,160 x 140 cm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段建宇以“误读”对抗僵硬的解释体系,保持与主流叙事的距离,使绘画始终处于可以被重新观看的位置,即“有了距离才能重新看清”。《时尚教宗(肖像)》(2024)中,宗教、时尚、科技符号混杂一体,形成不断流动的视觉语法。艺术家并不追求风格,那只是语言的副产品。重要的不是被归纳为哪一类艺术家,而是维持作品可继续被误解、被讨论的状态,她希望自己的画也能保持“不需要被读懂,只需要被感受”的自由。
杀马特与混合美学:
“从’杀、杀、杀马特’到’渔樵’,我并没有改变太多,只是学会了更慢地愤怒,更温柔地批评。”
“杀、杀、杀马特” 系列是理解“渔樵”的前史。那一时期,段建宇面对的是更直接的社会冲突与舆论图像——上访者、城乡碰撞、身份漂移、互联网亚文化的兴起。她拒绝以纪实或控诉的姿态处理这些题材,因为那容易把他者痛苦转化为可消费的形像。于是,她转向选择用一种审美化的方式去消解愤怒形式,彼时艺术家在思考:绘画是否有可能重新面对“社会题材”?是否可以在伦理上保持距离,又在情感上保留真诚?
她将“杀马特”作为隐喻,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被折叠后”的混合美学:马列维奇 (Kazimir Malevich) 的几何结构、非洲面具的造型、乡村装饰、花布、塑料制品,被共同纳入画面。叛逆的外表之下,其根源实则为对中心文化的模仿与扭曲。这些元素并置并不追求统一,而是呈现现实本身的多源与不稳定。通过这种方式,段建宇在绘画中处理“愤怒如何被组织”的问题:直接愤怒往往短暂,而经由形式折射的情绪可以留下更持久的痕迹。“杀马特”的实验让她学会与题材保持必要距离,不抽离现实,也不被情绪淹没。
“段建宇:渔樵”展览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至12月20日,YDP,伦敦
摄影:Wenxuan Wang
图片致谢YDP
回望这一阶段,她更愿意将之视为自画像,而非社会纪实:一个在混乱世界中尝试建立语言秩序的画家。后来“渔樵”的出现,是在同一问题上采取的另一种姿态:从高噪音转为低声,从尖锐走向内向,却延续了对现实的敏感与对图像语言的要求。“杀、杀、杀马特”的能量在“渔樵”中沉淀为更长线的、耐心的思考。
“很多时候,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写作。”
“渔樵”系列之所以重要,因其让艺术家重新理解了“观看”。她不再追求画面的“意义”,而是追求它的“温度”。那些看似平静的山水、渔夫、木柴,都是时间的隐喻,在画布上缓慢地生长。有人说,段建宇的绘画越来越安静,她却知道,那安静中有很多噪音,她不再用愤怒去回应世界,而是用结构去承受它。让复杂的情绪藏在细节里——藏在色彩的震颤里、藏在形象的停顿里。
“这就是绘画的伦理:用美去抵抗混乱,用形式去保存脆弱。”段建宇觉得自己一直在两种书写中往返——文字与图像。近年来,她愈加觉得绘画的节奏是一种比写作更慢,但更接近身体的思考方式,如果说写作教会她清晰地表达,绘画则让她理解了如何保留不确定。就像渔樵那样——他们不离开,也不依附;他们只是生活,在山水之间,在庸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