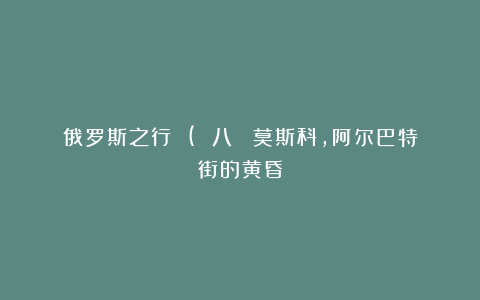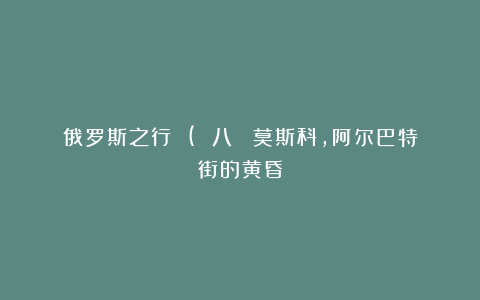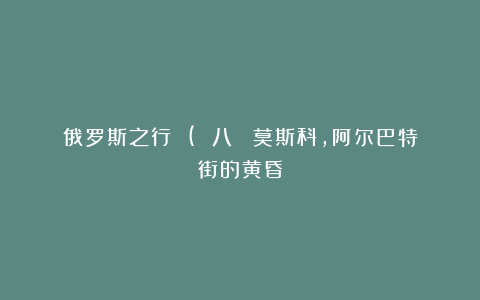|
阿尔巴特街,从57号开始,我们从俄罗斯外交部大厦转一个弯,就来到这里。
爱谷莉给我们2小时自由活动。临走,她再三关照,小心钱包被盗,当心镜头被卸。哪有这么可怕,一群来自大上海来的游客,还会惧怕俄罗斯的小偷?
黄昏的阿尔巴特街,阳光西斜,天空瓦蓝。路边圆形玻璃灯罩的街灯,将大街装点得典雅古朴。在方砖铺成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工艺商店古色古香,我捏着相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像个偷时光的小贼。
这条街不过八百米长,十米宽,却塞进了五百年的喧闹与叹息。据说阿尔巴特这个名字原是阿拉伯语“紧邻”之意,也有说是俄国人学舌“板车”的土话。
反正当年阿拉伯商人推着板车在此卸货,怕也想不到今日满街的套娃与摇滚涂鸦。
街角的书摊,一些人在低头翻阅。活像博物馆里搬出来的物件,我所在的城市早已绝迹,现在撞见,像踩着了童年掉在地上的糖块。不赶紧“咔嚓”一下存进相机,怕是回头梦里都寻不见这样的热乎。
路中摆着各式小摊,最瞩目的是画铺。油画、版画、速描,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揽到生意的画匠,聚精会神于画板上面,片刻之间,人物形象惟妙惟肖被跃然纸上。
几步之外,一个中年男人正跪在地上涂抹油彩,映版下面出现一座神秘的教堂。
这场景倒延续着老传统,从托尔斯泰时代起,阿尔巴特街便是落魄画家的避难所。如今他们照样支起画架招揽路客,十美元便能换幅速写肖像。
我凑近白发画者,他的笔下,碳素,粉墨运用自若,画布上,姑娘的眸子比真人还亮,想来列宾的学徒也得靠这手艺糊口。
初秋落日的余晖,映着地上的斜影,街边艺人,或歌唱,或舞蹈,或吹箫,或拨弄琴弦,完全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
吉他声混着叮叮咚咚的琴音飘过来,斜眼一瞧,那人捧着簧风琴,吹得全神贯注。十九世纪贵族沙龙的时髦乐器,而今在街头也能欣赏,琴盒里除了卢布还有美元和人民币。
转过普希金故居的蓝房子,撞见一场好戏。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为娜塔莉亚在圣彼得堡郊外与丹特士决斗。丹特士开枪击中普希金腹部,诗人两天后身亡。马路上的这一幕,女人是娜塔莉亚?瘫坐在旁的是丹特士,是在演决斗后的瞬间?我心里没有答案。
那幢蓝方子可是诗人成婚的蜜罐,1831年他挽着俄国第一美人娜塔莉亚搬进二楼,写信向朋友宣告,我结婚了。虽然三个月后就匆匆搬离。
如今故居对面立着他们的新婚铜像,诗人卷发飞扬,新娘裙裾如云,凝固在走向教堂的瞬间。
套娃店的橱窗,普金正冲着奥巴马挤眉弄眼。店主热情对我说:悄悄,叶利钦套戈尔巴乔夫,能装五层。
这些画着政要的圆肚木偶,倒是俄国人的面对历史的幽默注脚。
隔墙“宝石商店”的涂鸦墙更绝,满墙狂野线条中浮现出维克多.措伊的侧脸,苏联摇滚教父在此永生,青年们年年来献上啤酒。
瓦赫坦戈夫戏剧院前(建于1921年),两位士兵在图兰朵公主的金像前合影,也被我抢先按下快门。
街舞少年拿大顶时露出半截腰身,塑料布上的涂鸦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缩进街角的汽车咖啡巴,邻桌银发老太正往列巴上抹酸奶油,面包盘子大,才卖十五卢布。
夕阳映照下的建筑闪着金光,圆玻璃罩子像骑士头盔,忠实地守护者方砖路。
托尔斯泰,赫尔岑、莱蒙托夫、果戈里都曾在这里居住。至于住在阿尔巴特街的那座房子,现在已无人知晓。
恍惚看见十九世纪贵族马车驶过,车帘或许坐着去剧院看戏的托尔斯泰;
三十年代雷巴科夫笔下《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正为命运奔走;
苏联青年偷听西方电台的杂音,掺进今日商贩的吆喝声里…..
阿尔巴特51号,雷巴科夫在此居住(1919-1933)
新阿尔巴特街的玻璃幕墙在远处闪光,奢侈店冷气十足,顾客寥寥。而老街上烤面包的焦香,琴弦的震颤,颜料的味道,在暮色里蒸腾成一片暖雾。
俄罗斯人骨子里嫌弃商业化,周末商店早早关门,全城车流涌向郊外小木屋,他们在这条石巷子寄存灵魂,好在别处继续生活。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更长,相机里已经塞满几百张照片。
有醉汉摇着空瓶子哼呵阿库扎瓦的民谣,那吟诗人曾在此流浪,他在老街43号长大,双亲殒命于大清洗,自己背着“人民敌人之子”的名号上战场拼命。此刻他的青铜像立在街角,苦难与荣光终被铸成街头风景,供游人歇脚时随手一拍。
阿尔巴特街的妙处,大约就在500年的悲欢全拌进黄昏的鸡尾酒里。人们举杯啜饮时,尝不出哪滴是普希金的喜泪,哪滴是阿库扎瓦的苦酒,只觉得满喉温热,刚好配这人间的喧闹。
《阿尔巴特之歌》作者,苏联作曲家,诗人阿库扎瓦(1924-1997)在老街43号长大。布尔什维克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被枪决,母亲被流放。阿尔巴特之歌,被称为城市知识分子的民谣。诗歌如下:
纵然爱上四万条别样的街道,但你的深情留下的创伤无法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