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爨(cuan)氏家族,是一段“突然遗失”的历史片段,仿佛所有“一夜之间”消失的文明。
其实,翻开历史案卷,有清晰的脉络可寻。
爨氏起源
从中原灶膛到滇南火塘
东汉末年,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因中原动荡而豪强并起
。
诸葛亮的南征大军正穿越牂牁江。
队伍里有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腰间悬着枚青铜印,印纽雕着奔马,印文是汉隶凿刻的”军司马”——他就是爨氏先祖爨习。
“爨”源于姬姓,出自周王朝时期官吏爨官,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爨官,为西周时期在宫廷内为王室成员制膳之士中的灶官,就是俗称的火头倌,专职掌管炊火。
这枚印信并非寻常军职象征,而是爨氏家族在中原王朝与南中部族间走出的第一步棋。
据《华阳国志》记载,爨习本是建宁郡(今曲靖)大姓,东汉末年已拥兵自重。
225年诸葛亮南征时,他审时度势率部归附,献上的”见面礼”是滇地特有的”毒箭淬铁法”。
这种箭镞用哀牢山铁矿铸造,蘸取蛇毒后能穿透三层藤甲,诸葛亮大喜,当即任命爨习为”军司马”,隶属马忠麾下。
诸葛亮班师后,爨习的军司马印派上了更微妙的用场。
他拿着这枚汉廷信物回到建宁郡,在部族议事会上”出示印信,宣示汉恩”,成功说服各部首领接受蜀汉管辖。
《三国志》注引《南中志》记载,爨习凭借军司马的身份,将自己的族人安插进各郡县担任”督邮””功曹”。
这些职位虽低,却掌控着地方文书与监察权,为爨氏日后垄断南中政权埋下伏笔。所谓,“举贤不出氏族”。
最关键的转变发生在蜀汉延熙年间。
225年,诸葛亮为巩固蜀汉后方,率军南征,七擒孟获后推行“和抚”政策,启用当地大姓参与治理。
爨习的儿子爨弘继承了父亲的军司马印,却不满足于军职。
他带着印信远赴成都,以”南中赋税足额上缴”为筹码,为自己谋得”建宁太守”的文职。
爨氏由此跻身南中统治阶层。
这一事件标志着爨氏从地方豪族向政治势力的转变,其依附蜀汉的策略为家族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诸葛亮南征后设立“庲降都督”管辖南中,同时推行“夷汉分治”:
汉族大姓掌控郡县政权,土著部族保留世袭首领。
爨氏凭借中原文化背景与军事支持,逐渐在建宁、朱提(今昭通)等地扩张势力,与孟氏、霍氏等大姓形成制衡。
至三国后期,霍氏因与孟氏内斗衰落,爨氏趁机吸纳其部众,成为南中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西晋末年,巴蜀流民李特起义(301年),战火波及宁州(南中改置)。
西晋王朝无暇南顾。
爨氏首领爨琛趁机联合其他大姓,驱逐晋朝官吏,自领“宁州刺史”,形成事实上的割据政权。
此时中原正逢“五胡乱华”,东晋朝廷对南中仅存名义管辖。
爨氏通过“奉晋正朔”的名义,实则独立统治,史称“开门节度,闭门天子”。
爨氏在统治期间推行“汉夷合流”政策:
一方面,以《爨龙颜碑》为代表,标明家族为“班超后裔”,借助中原名门以增强正统性。
另一方面,吸收滇地土著文化,创造融合汉隶与古滇符号的“爨文”。
铸造兼具汉式纹饰与滇地风格的青铜器。
这种文化策略使其既获得中原士族的认同,又笼络了当地部族。
至南北朝时期,爨氏统治范围已覆盖今云南大部及贵州西部,进入鼎盛期。
隋朝统一后,试图恢复对南中的控制。
597年,隋文帝派史万岁率军入滇,爨氏首领爨翫因“恃远不宾”被击败。
隋朝设立南宁州总管府。
但爨翫不久复叛,隋朝因忙于对突厥作战,最终放弃直接管辖,爨氏再次割据。
此事件暴露了爨氏与中原王朝的矛盾——
既想保持独立,又无力完全对抗中央,为日后衰落埋下隐患。
唐朝,太宗时期,对南中推行羁縻政策。
任命爨氏首领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允许其世袭统治。
但爨氏内部因利益分化逐渐分裂为东、西两爨:
东爨(乌蛮,今彝族先民)以曲州(今昭通)为中心。
西爨(白蛮,今白族先民)以昆州(今昆明)为核心,双方常因争夺盐井、土地爆发冲突。
唐朝为制衡爨氏,暗中支持洱海地区的南诏政权,加速了爨氏的危机。
唐玄宗时期,南诏首领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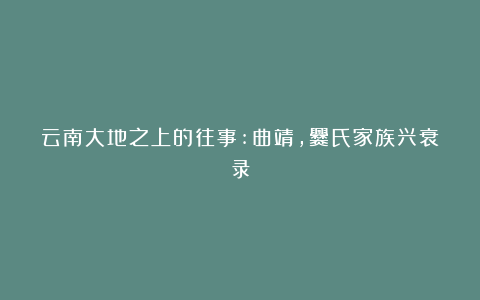
748年,南诏为扩张势力,以“调解爨氏内乱”为名,联合吐蕃进攻西爨核心——味县(今曲靖)。
据《蛮书》记载,南诏军队“俘掠爨氏宗族及部众二十余万,迁徙至永昌(今保山)”。
曾经繁华的味县沦为废墟。
此后,东爨残余势力虽短暂归附唐朝。
但在南诏与吐蕃的夹击下彻底崩溃,爨氏统治历经数百年后宣告终结。
爨氏的崛起,始于汉末三国的边疆权力真空与中原王朝的“以夷制夷”策略。
其鼎盛,得益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对汉夷文化的融合与割据政权的建构。
其衰落,则源于隋唐中央王朝重振边疆控制的企图,以及南诏在区域霸权竞争中的崛起。
从诸葛亮南征到南诏灭爨,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塑造了爨氏家族的命运。
更勾勒出中国西南边疆从“豪族割据”向“民族政权”过渡的复杂历程。
正如爨文化遗存中汉式碑刻与滇地青铜的并存,爨氏的兴衰本身便是一部中原与边疆、民族与文化碰撞融合的活历史。
二十万流民
从味县到永昌的血泪路
城破三日后,南诏军队开始强制迁徙爨人。
二十余万男女老幼被驱赶着走出城门。
他们回望时,味县的民居正在燃烧,黑烟中隐约可见爨氏祖祠的飞檐——
那座曾刻满青铜铭文的建筑,此刻像个被戳破的蜂巢,梁柱间不断坠落着燃烧的木楔。
迁徙的队伍沿着澜沧江古道西行。
盛夏的毒瘴在山谷里弥漫。
老人跟不上队伍,被南诏兵用长矛戳着前行。
孩童们哭着要喝母乳,母亲们只能从浑浊的江水里捧水解渴。
走到哀牢山时,疫病开始蔓延。 每天都有数十具尸体被抛在路边。
秃鹫在队伍上空盘旋,翅膀投下的阴影像一块块移动的墓碑。
一个背着爨文典籍的老学究,趁夜将竹简埋在山岩下,他指甲抠进泥土时,触到一块带字的陶片——
那是百年前爨人烧制的瓦当,上面的云雷纹还清晰如昨。
走到永昌(今保山)时,二十万爨人已死去近半。
南诏兵将他们圈禁在澜沧江畔的山谷里,四周筑起木栅,派”蛮兵”日夜看守。
头爨地为南沼占领以后,爨地的所谓爨人也发生了变化。
一部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由于被强迫迁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区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白族。
留在当地山区保留本民族文化较多的“乌蛮”,则保有了自己的部落组织,逐步成为后来的彝族。
到了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当时的爨人,大多数便是指今天的彝族了,而提到的所谓的爨文,也即是彝文了。
爨氏的后裔后来可能改姓寸了,因为爨和寸本就同声同韵。
在云南鹤庆地区找到了明朝时期立的一块碑,叫《寸升碑》。
这块碑上面叙述了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入南诏大理以后保持有贵族身份,后改为寸。
这块碑说明爨氏家族西迁后其分布并不局限于大理地区,而是很广的。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后人改姓为寸了,到了明代还留有记载。
十年后,一个云游的唐僧路过(曲靖)味县故地。
他在日记里写道:”城郭丘墟,狐兔窜于殿宇,荆棘没于街巷。”
曾经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口,如今只有断碑半截埋在荒草中,碑上”爨使君之墓”的字样被风雨侵蚀,只剩”火”字底的四点还像未熄的余烬。
城南的爨氏庄园已成狐穴,当年工匠铸造铜鼓的作坊里,锈迹斑斑的陶范散落在青苔间。
最令人心惊的是味县县衙的残墙,那里有幅被烟熏火燎的壁画,画中爨氏贵族宴饮的场景已模糊不清,唯有角落一个捧着酒樽的侍女面孔尚存,她的眼神空洞望向城外,仿佛还在等待再也回不来的马帮。
在这时期由西爨迁去的。
一是澜沧江边,就在今巍山(蒙化)、景东等处住居着的彝族支系,自称腊罗拔或密撒拔,现有二十多万人口,相传住居在这区域的年代已很早。
又一是金沙江北即今会理、盐边等处。
迁徙的山谷里,他们把中原的桑蚕种埋进红土,却用滇人的腰机织布,织出的布匹上,汉式云纹与爨氏龙纹缠绕成新的图案,
爨氏家族的直接统治虽已终结,他们的文化基因却渗入云岭各族。
在大理国的《张胜温画卷》里,有个巫师戴着爨氏青铜面具跳神;
丽江纳西族的东巴经中,某些字符与爨文如出一辙;
甚至今天云南方言里的”火塘””马帮”等词汇,发音仍带着爨人古汉语的尾韵。
在古爨人的后代撒尼部落人中,世代相传着一个凄美感人的故事,
即流传于云南石林地区彝族支系撒尼人当中的口头神话传说。
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男青年阿黑和女青年阿诗玛之间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
“阿诗玛”,汉义就是“蛇女”。
而蛇女则是古爨人深切崇拜的图腾。
最倔强的遗存是那两块爨碑: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
当岁月磨平无数王朝的印记,它们仍立在曲靖的田野,向过往的风讲述着那个青铜家族的故事。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诸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云南的山山水水#云南历史和地理#